第三节 阿拉伯语本体规划中的几大挑战
阿拉伯语的本体规划伴随着阿拉伯民族意识的觉醒,同样也深深地浸透了西方近代思想的影响。本体规划的进展,客观地折射了阿拉伯社会在传统与现代、传承与变革、守望与期许之间的探索与抉择、迷茫与困惑、争论与斗争,反映在具体案例上,曾经遇到过几次比较大的挑战。
一、文字拉丁化大辩论
一战后,随着奥斯曼帝国在1922年的解体,在原帝国境内的各地,在传统的阿拉伯国家的周边,纷纷崛起了以土耳其共和国总统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1881—1938)为代表的一些政治人物和领袖。这些民族主义者所秉持的治国理念,主流是亲西方的,他们所进行的革命或改革,都打上了深深的西方烙印。在知识文化领域,这些领袖的改革明确指向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废除阿拉伯字母、废除标准阿拉伯语、废除面纱、废除阿拉伯教法、废除穆斯林的宗教义务、废除伊斯兰伦理与道德,等等。这些政治、宗教和语言方面的改革,对正在开展阿拉伯语复兴运动的阿拉伯国家产生了一定的外部影响。
此时的阿拉伯世界内部,也存在一批亲西方学者,这些具有西方文化背景的学者,通过自己的著作和文学作品,向大众传输着亲西方的理念,希望通过他们的努力,使国家和民族摆脱“落后”。这些学者,以塔哈·侯赛因(1889—1973)、卡西姆·艾敏(1863—1908)等为代表。
塔哈·侯赛因是埃及著名作家、政治家,被誉为“阿拉伯文学之柱”。塔哈以向埃及和阿拉伯社会介绍西方思想著称,并宣传“埃及民族主义”,他一生个性和倾向都极其鲜明,但也饱受争议。他在自己的《埃及的文化前景》一书中曾有对理想中的埃及的畅想:
“我们上流社会的物质生活是纯粹欧洲风格的,而在别的阶层则有或多或少的区别,这关键取决于个人或团体以及他们获取资源的能力,这么说的意思是,他们物质生活的最高理想也就是欧洲人物质生活的最高理想。”
“我们的精神生活,无论其表象和形式有多少区别,是纯粹欧洲风格的。我们的政治制度是欧洲的,我们毫无保留地从欧洲将它引进过来。如果说我们有所欠缺的话,那就是我们在引进欧洲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形式的时候还是稍微慢了一些。”
“我们的教育制度从上个世纪以来就是按照欧洲的模式建立起来的,这是毫无疑议和毫无争论的。我们的孩子在完美无瑕的欧洲模式下建立的小学、中学和大学学习。”[10]
在书中最后,塔哈·侯赛因指出:
“所有这一切都证明:在这个时代,我们期待与欧洲建立一天更比一天紧密的联系,直到有一天,我们成为它的一部分,无论是语言上,还是精神上,还是形式上……”[11]
这种观点也集中代表了当时知识分子中的一大部分人的观点,那就是“救亡图存”,就是要在所有方面变得和强者一样。在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这种思潮也极其鲜明。这种和传统文明彻底决裂,全面拥抱西方文明的论调在那个时代大行其道确有其一定合理性,但放到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来审视,未免显得片面和偏激。
塔哈·侯赛因在法国取得了博士学位,还娶了一位法国姑娘苏珊为妻。这样的背景或许让人觉得他的亲西方论点并不过分,但是如果在了解到他还曾担任过开罗阿拉伯语言学会会长和阿拉伯语言学会联合会会长、埃及作家协会主席、阿拉伯国家联盟文化专员,甚至还曾担任过埃及教育部长的话,那么这种论点未免让大众感到忧虑。幸运的是,在具体的实践上,塔哈不仅是作为一名熟谙西方文化的西化学者鼓吹大力引进西方先进思想,更是作为一名彪炳于世的阿拉伯大文豪创作出了光耀千秋的阿拉伯文学作品。透过他的《日子》、《鹧鸪鸟的叫声》等小说,我们看到了他那西化表象下却隐藏着一颗炽热的“埃及心”——或许这样的评价对他才公平。
卡西姆·艾敏是埃及著名作家、社会活动家,妇女解放运动的倡导者。卡西姆·艾敏曾求学法国,一生主张社会改良,参与过埃及独立运动,但世人较少了解。他还是一位亲西方的,主张全盘西化的代表人物。他在代表作《新女性》一书中这样写道:
“这些我们致力于寻求解决之道的弊病,其实是没有什么良药的,除非我们教育我们的孩子们学习西方的文明,知晓它们的起源、分支和遗存。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真理的光明照亮我们的眼睛,就像太阳驱散阴霾。我们将会理解西方文明的价值,我们将会坚信如果不是建立在现代科技的基础上,任何改革将会一事无成。人类生存的状态,不管其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情况如何不同,都会屈从于技术的力量。因此,我们可以发现,文明国家,不管其人种、语言和国民及宗教有多少区别,不仅在政府组成、行政管理、司法体系、家庭结构、教育方式、语言表达、书面用语等方面都惊人地相似,在生活习惯方面,如穿戴、问候、饮食等方面也日益趋同。这种情况使我们更喜欢举欧洲的例子,我们推崇他们的生活方式,我们会更关注欧洲妇女(的生活方式)。”[12]
以上这些政治领袖和思想家的政治实践和启蒙呼吁,所秉持的信条无疑是救国家于危难、拯民族于水火,希望通过引进西方科技和制度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实现国强民富的目标。但是如果只看到旧制度的僵化和落后,无视长期历史文化传统的稳定性和惯性,将其“妖魔化”,全面打倒和否定,并一味崇拜西方制度和技术的威力,无视其片面性、局限性和负面性,甚至将其“神化”并全盘进行吸收,显然是存在重大认识误区的。因为如果全盘西化得以从理论到实践全面铺开,就意味着阿拉伯民族和自己的文化传统、历史渊源和社会习惯完全割裂,意味着彻底的“脱胎换骨”:脱下长袍,摘下面纱,穿上西装,讲起洋文,变成西方世界的一员。
由于在西方先进科技面前的弱势心理,阿拉伯知识界和政治界在一定时期普遍没有建立起对自己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的自信,在面临选择的时候,他们往往倾向于否定自己,而没有拿一把真正客观公正的标尺去甄别西方文明中的精华和糟粕。这种文化上的不自信和不自觉对复兴阿拉伯文化、复兴阿拉伯语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弥漫在阿拉伯知识界和文化界的亲西方思潮,对阿拉伯语的复兴和规范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阿拉伯的有识之士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们从历史的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未来:伊斯兰征服时期,阿拉伯民族开拓了广阔的疆域,征服了周边的罗马和波斯等先进文明,他们拼命吸收和学习这些先进文明成果,但结果是他们并没有变成罗马人和波斯人;阿拉伯人保留了自己的宗教信仰、文化传统和语言文字,反倒使文明程度高的罗马人和波斯人改变了语言和信仰,成为阿拉伯帝国的一部分。所以,对西方技术的引进并不意味着文化上的改变,这一点慢慢成为共识,即将科技和文化进行区别对待,在大力引进西方自然科学技术成果的同时,保留东方既有的道德价值和传统文化,以避免“文化异化”。
但是西化的浪潮还是在各种合力的作用下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产生了一些影响,最典型的例子是土耳其语的拉丁化。
(一)土耳其语拉丁化取得成功
被称为“土耳其国父”的穆斯塔法·凯末儿·阿塔图尔克(1881—1938)于1922年推翻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创立现代民族国家——土耳其。他是一位亲西方的政治领袖,致力于国家全面西化,采取了去伊斯兰化、去阿拉伯化的政策,力图去除土耳其的历史与文化根源。
凯末儿推动实行的土耳其语的拉丁化就是一个标志性的政策、他的政策路径清晰可辨:消灭了阿拉伯字母,就等于是阻绝了阿拉伯语,普通人今后将不能诵读《古兰经》,也无法阅读古籍,将与土耳其的历史文化自然隔绝。这就像将一个婴儿的脐带剪断,与母体再无联系。
土耳其裔的阿拉伯大学者沙基布·阿斯兰(1869—1946)在他的《伊斯兰世界的现状》一书中这样说:
“安卡拉共和国的总统先生穆斯塔法·凯末儿想要做的,就是一步一步使土耳其人从伊斯兰文化传统中脱离,使他们远离阿拉伯语,将引导土耳其政府远离宗教,就像西方国家那样,基督教远离政治。土耳其被称为‘第三条道路’的政党是其忠实追随者,因为这个党的所有人看起来都像是凯末儿领导的士兵。他去除了政府机构中一切具有伊斯兰色彩的东西,不加区别。他取消了伊斯兰法庭,然后又禁止从事伊斯兰教法工作。他取消了‘伊斯兰长老会’这个部级机构,把它降格为一个内政部的处理宗教事务的司局级机关。他在宪法中取消了‘伊斯兰教是土耳其的国教’这款条文。他还取消了举办宰牲节和开斋节的仪式,说土耳其政府不承认这两个节日。但是由于受到强大阻力,土耳其政府不得收回成命,不得不庆祝这两个节日,凯末儿也要出面祝礼。
至于采用拉丁字母书写土耳其文,除了存在大量的反对声音外,当局给公众的冠冕堂皇的理由是:有利于减轻幼儿学习的难度、缩短学会阅读的期限等,其真实目的在于使土耳其民族远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逐步使人们丧失阅读《古兰经》的能力,更为重要的是,使欧洲相信土耳其已经彻底西洋化,已经成功地加入了欧洲大家庭。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标,凯末尔还命令土耳其人戴上了帽子,以此表现其融入欧洲的程度。抛弃阿拉伯字母给土耳其的科技、文艺、经济和贸易生活带来了重大打击是,几乎所有人都不会用拉丁字母书写,仅有极少的人会使用。人们之间的书信减少了,报纸和书籍的读者减少了。一份以前拥有上万读者的报纸现在仅剩下了500人。
书写的困难也导致了政府机构办事效率的下降。数以百万计的书籍被束之高阁,不计其数的家庭为此破败。在艺术领域,很多拉丁字母被引进代替原来的阿拉伯文字母,但是在很多场合并不能正确表达原意,所以某种程度上讲,土耳其语已经与其本源相异,变得更像一门新的语言。由于拉丁字母是分离的,如果说它是易于读写的话,那么它在纸张上占据的空间更大些,比用阿拉伯字母进行书写耗时更长,阿拉伯书写方法就像是速记一样(耗时更短)。
尽管书写危机在土耳其愈演愈烈,但是一意孤行的统治者仍然推动这个民族走向拉丁字母,这源于他对洋化的不懈追求。
那些不了解实际情况的人会这样认为:土耳其人非常高兴和满意取消了伊斯兰法庭、取缔了私塾和学校的经堂教育、强制妇女揭去面纱、教育方面推行男女同校、提倡男女青年一起跳舞、戴礼帽、使用拉丁字母书写,以及其他凯末儿政府致力于近代化的一些措施。他们说,如果土耳其人不满意,肯定会造反,推翻他们的政府,把他们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但是只有那些深入观察土耳其的人才会理解土耳其人民正在遭受的灾难和不幸,理解他们为何能够在如此艰难的时势中依然沉静,即使这种改变违背了他们的传统习惯和道德价值。为什么他们选择屈从而不是选择革命和起义?因为他们只是不想让国内外的敌人再次荼毒土耳其而已。
至于伊斯兰教,时至今日,这种去宗教化的政策仍然没有在土耳其奏效。土耳其民众仍然笃信伊斯兰教,从伊斯坦布尔和其他地方的现象就可以看出端倪。伊斯兰教不惧怕洋化运动,即使当局在报纸上大肆宣传。伊斯兰教丝毫没感到威胁,除非现时的统治延续很长时期,新生的没有宗教教育的一代成长起来。”[13]
一战和二战之间这股西化的浪潮,催生了土耳其语的去阿拉伯化运动。由于奥斯曼土耳其长期居于伊斯兰教的中心地位,近代土耳其的文字改革、土耳其语的拉丁化对阿拉伯地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对正处复兴运动关键时期的阿拉伯语产生了负向影响。
(二)埃及和伊朗拉丁化实验遭受失败
在土耳其废除阿拉伯字母书写的时期,在伊斯兰世界,同样有一些国家进行了类似的尝试,但均遭到了失败。伊朗著名的里萨·巴列维国王曾经开展过这项工程。他组织了一批文学家尝试用拉丁字母取代阿拉伯字母进行波斯文的书写,最终还是失败了。
第一个正式提出用拉丁字母拼写阿拉伯语的是法国东方学家、传教士路易斯·马西农(Louis Massignon)(1883—1962)。他长期供职于法国殖民部,并在北非和埃及开展传教活动。他的这一观点通过西方传教机构培养的毕业生在摩洛哥、埃及、叙利亚和黎巴嫩得以传播,有一定的影响。其中有一些阿拉伯知识分子参与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卡西姆·艾敏(1863—1908)、萨拉曼·穆萨(1887—1958)、阿卜杜·阿齐兹·法赫米(1870—1951)等。
贝鲁特美国大学历史与闪米特语言教授艾尼斯·法立哈(1903—1993)是黎巴嫩较早主张采用拉丁字母的。他声称自己这一主张主要是基于简化读写,他还反对将阿拉伯语作为当今一代的语言,因为阿拉伯语的语法是从《古兰经》和古代诗歌里提炼出来的:
“事实并非是一直流传下来的说法那样:实际使用的语言是先前时代研究语言的来源,因为提炼它的语法和确立它的规则的语料首先是贾希里亚时期的诗歌,然后是《古兰经》,什么时候诗歌语言和文学语言、宗教语言成了反映人们生活和劳作的镜子了?”
“我们现在的官方立场是:我们在讲一门濒危的和孑遗的语言,我们应该用这种语言表达我们所有的情感和我们的内心,而当这种语言被罩上了一层神圣的外衣时,在某一时空点上停滞在了发展的轨道上,当它被很多规则限制住之后,它便在那个时空点上停止了发展进程。”[14]
法立哈找出一条折衷的方法处理宗教语言和生活语言的关系:
“《古兰经》将像很多宗教经典一样仍然保有它神圣而崇高的地位,尽管人们实际使用的语言和宗教经典语言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但这些宗教经典仍然保留了它语言上的优雅和崇高。比如说,17世纪的英王钦定版《圣经》除却是一部经典的《圣经》译本外,还被认为是英语世界里一部优美的文学巨作。这部英译《圣经》在语言上的影响沉淀在同时代的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里。直到今天,在伦敦著名的环球剧院,只上演17世纪莎士比亚的经典戏剧,剧中人物说当时的语言、吟咏那个时代的诗歌、采用古老的表达方式……同样的情况还有,天主教堂把《圣经》的拉丁语译本作为教堂正式的宗教用语,只有拉丁语才能体现神圣;东正教堂则不同,他们采用希腊文作为宗教语言;马龙派教堂则使用叙利亚语;埃塞俄比亚东正教堂则使用吉兹语(一种古代闪语)作为宗教用语。”[15]
法立哈对待阿拉伯语的态度非常明确而坚决,将其严格界定在宗教领域,社会生活则采用方言土语,并用拉丁字母进行拼写。
呼吁采用拉丁字母进行书写的改良者的一种理论建构是:“阿拉伯语是导致阿拉伯社会落后的原因,只有采用拉丁字母才能给阿拉伯民族带来科技和文化。”在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萨拉迈·穆萨和阿卜杜·阿齐兹·法赫米。
埃及作家萨拉迈·穆萨(1887—1958)是20世纪埃及最重要的民族主义思想家、改良家,他对待阿拉伯语的态度令人印象极其深刻:
“我们是在骆驼的时代从蒙昧的贝都因人的手里继承到阿拉伯语的,难道奢望我们能在飞鸟的时代还用它来交流吗?”
……
“我们很少发现有呼吁(对阿拉伯语)进行大胆改革的人,除了那些不在乎别人说他们愚昧和无知的有见地的人。比如说像主张取消阿拉伯语的卡西姆·艾敏和艾哈迈德·艾敏(1887—1954),还有像主张采用拉丁文书写的阿卜杜·阿齐兹·法赫米。事实上,采用拉丁字母的建议是通向未来的一个跳跃。如果我们这样做了,我们就能将埃及发展到土耳其的境况!这种书写方法能关上过去的大门,但同时会为这个民族开启未来的大门。……总之,我们能够这样讲,采用拉丁文书写能使我们从当下跃升到未来,但是那些因阿拉伯字母留存而得益的因素及传统会对这种跃升感到满意吗?”[16]
穆萨呼吁清除一切阿拉伯语的影响,为土语登场扫清障碍。但是它忽视了这样一个客观事实:阿拉伯各个地区的土语是不尽相同的,甚至是各国内部的各地区土语也是区别甚大的。
穆萨把阿拉伯社会的种种落后现象归因于阿拉伯语,称它为“哑巴语言”,他认为是阿拉伯语阻碍了阿拉伯和伊斯兰社会实现社会公平,也是一些社会异常现象的根源。他在自己的《现代修辞与阿拉伯语》一书的《序》中写道:
“埃及语言方面的落后是导致社会落后的最重要的原因……当我们的语言尊重当代文化词汇的时候,它也就尊重了当代生活的民族……对任何民族来说,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它的语言,因为它是这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并保存了其社会价值和思维习惯的遗产。”[17]
穆萨认为语言是一个民族复兴的基础,一个民族的复兴不可能建立在一门僵化的、没有发展的语言之上。阿拉伯文化之所以落后,原因就在于阿拉伯语的停滞与僵化,无法适应当代社会生活的需要,无法承载民族复兴的重任。穆萨在自己的著作中也反复提到拉丁语在欧洲国家的兴衰,来反证将宗教语言和生活语言相分离的必要和必然。
“这门语言不能满足当代知识分子的需求,因为它无法应用于思想,无法提高它,因为它无力传输能改变未来的各种科学知识……这种(社会)进步体现在,我们生活在这样一种社会:真理基于客观数据而不是宗教信仰。鉴于这样一种原因,我们的语言应该是科学的,我们的文化应该是全球的,我们的书写应该是拉丁的……”[18]
同样是地区大国,同样是伊斯兰国家,语言文字拉丁化的结果是,土耳其推行成功了,伊朗和埃及却失败了。在国家近代化的过程中,这种取舍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力量在主导呢?
从表面的原因来看,可以从社会力量对比、政治领袖的决断力、国际格局的变动等“硬条件”进行分析,但从深层次来挖掘,必须从历史、文化、民族和宗教等“软因素”来考虑。
埃及作为阿拉伯文化大国,开罗又是阿拉伯文化中心,伊斯兰教和阿拉伯语的影响根深蒂固,西方文化可以动其表面,无法触其根本,可以逞一时之强,无法占长期优势。埃及与西方文明接触较早,沾染已久,明辨西方文明利弊,最关键的是,阿拉伯文化复兴在此时正如火如荼地展开,阿拉伯精英知识分子正擎起复兴阿拉伯文化的大旗,怎么可能开历史倒车,把文化复兴的载体——阿拉伯语给抛弃呢?所以,尽管社会存在激烈争论,但是主流的思潮是“西学为用,阿学为体”;借助西方先进科技文化实现阿拉伯复兴是共识,全盘西化,融入欧洲只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一代一代埃及文学家和学者,以自身实践勇于面对这场西化浪潮,在理论界和创作界发出强有力的声音,证明改良后的阿拉伯语完全可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各种需求,完全可以表达人们的各类情感;不能也无法用拉丁字母取代阿拉伯字母,这样会割裂阿拉伯民族的历史,削弱阿拉伯文化的根基,最终导致阿拉伯民族近代化的失败。
伊朗作为伊斯兰教什叶派大国,宗教文化气氛浓厚,历史上波斯思想全面影响到了阿拉伯学术,很多波斯诗人、文学家、政治家的名字镌刻在阿拉伯帝国的历史上。除了语言上相对有些独立以外,在相当多的文化领域,波斯文化已经融入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波斯本身的伊斯兰化和阿拉伯化程度很深,这一点对近代伊朗有着深远的影响。所以,如果伊朗的去阿拉伯化运动取得进展,波斯语用拉丁文进行书写,伊朗将游离于伊斯兰之外,它将无从发挥伊斯兰世界什叶派领袖的影响,在地区和国际的地位将发生动摇。鉴于伊朗和阿拉伯的历史、文化和宗教渊源,波斯文的拉丁化是不可能推行成功的。历史最终也证明了这一点。
土耳其则不一样,一是突厥民族和阿拉伯民族的历史关系和波斯民族和阿拉伯民族的关系大不相同。同样是面对历史上阿拉伯民族的强势征服,波斯民族的态度是主动融入,学习阿拉伯语,学习阿拉伯文化,利用自身文明程度较高的特点,迅速占据阿拉伯文化的高地,以波斯的文学艺术、典章制度和文化品位去影响阿拉伯民族,最终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上留下灿烂的印记。突厥民族则由于自身文明程度较低,始终无法或不肯融入阿拉伯文化,也从不努力去学习阿拉伯语和阿拉伯文化,所以自始至终不为阿拉伯民族所认可,并没有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上留下可圈可点的印记。土耳其只是借助自身勇武,为阿拉伯人东征西讨,建功立业,乃至最终坐大,开创不世武功,建立奥斯曼大帝国。文化基因的差别,决定了突厥民族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深层次的认同不够,去阿拉伯化碰到的阻力没有伊朗大,而凯末尔自身巨大的政治魅力和坚忍无比的决断力,誓要斩断土耳其和阿拉伯伊斯兰的宗教文化联系,彻底走上“世俗化”、“欧化”的道路,最终导致土耳其语拉丁化。
二、以方言取代标准语的倾向
全面西化的浪潮不仅志在文教领域推行拉丁化改革,还意图在日常生活领域全面“去伊斯兰化”。标准阿拉伯语被认为是“《古兰经》的语言”,所以成为西化者的矛头所指。在这一时期,社会泛起一股强大的思潮,意图用各地方言土语作为官方语言取代标准阿拉伯语,在报纸杂志、文学作品、广播节目、演讲会谈等场合全面推行土语,将标准语的适用范围严重压缩,甚至将其重新逼回到清真寺,仅在宗教场合使用。
这种理论和将阿拉伯语拉丁化有一定区别。后者是要将阿拉伯字母彻底取代,而前者并无意割裂阿拉伯语和《古兰经》、《圣训》、伊斯兰教法和阿拉伯文化起源等的传承关系,它的最大目的在于严格限定标准阿拉伯语在特定范围内使用。
亲西方的学者将现代人们无法自由表达他们思想的问题归咎于标准阿拉伯语,诟病它晦涩难懂,无法适应现代生活。但是用土语取代了标准语,就能解决这些问题了吗?阿拉伯人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中得出结论:在阿拉伯人的精神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学生活中,标准阿拉伯语的地位和作用不可取代。经过近代化改造,古典阿拉伯语已经发展为能适应现代生活的标准阿拉伯语,引进了大量能反映现代生活的新词,衍生出一些新的用法,已经完全能表达人们全部的情感和思想。对标准阿拉伯语的诟病并不是语言本身的问题,而是人们没有很好地掌握它。如果各地区都是用自己的方言和土语作为官方语言,那么就会造成现代人们和古代传统的割裂,人们不再能读懂古代大诗人的伟大诗篇,不再能欣赏古代散文的优美和隽永,不再能理解沉淀在古典语言里的很多文学故事和神话传说,阿拉伯传统的文化特质和道德价值将面临巨大的断代危机,阿拉伯文化将被彻底“异化”。
在这一阶段,有一些学术团体和部分学者开展了对方言土语的学术研究,为其取代阿拉伯语标准语做了一些准备。其中以某些阿拉伯语言学会、部分大学教授、一些主要的科学和文学杂志为主要代表,其中就有艾哈迈德·哈桑·扎耶特(1885—1968)。他是著名的《使命》和《小说》这两本文学杂志的创始人。
以土语取代标准语后面更深层次的动机是西方殖民主义的宏大战略意图,即通过将阿拉伯语“历史化”、“过去化”而将阿拉伯伊斯兰历史“断代化”,将伊斯兰征服后的阿拉伯各地区的历史等同于先前所经历的古代历史一样进行断代,将阿拉伯地区的民族属性、宗教属性、文化属性人为抹杀,为彻底西化、基督教化这块土地作思想上、舆论上和文化上的准备。
提倡以土语取代阿拉伯语是分步骤、分阶段实施的,同时也是阿拉伯世界内外合力进行的。走在这一行动最前列的是西方的东方学者,这些东方学者一开始都是以“学术研究”的面目出现,都宣称自己尊重阿拉伯的独立和发展。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是德国东方学家威廉·斯佩特(Wilhelm Spitta)(1853—1883),他在19世纪末担任埃及书局的董事长。斯佩特1880年出版了一本书《埃及阿拉伯方言语法》,在书中,他煽动埃及种族主义言论,为埃及人现在使用阿拉伯语感到悲哀:
“最后,我鼓起勇气说出我的希望,这种念头从本书写作开始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这种希望关乎埃及本身以及它的人民,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所有长期在讲阿拉伯语的国家里生活的人都能感受到,对一个成年人来说,他在很多方面都受到由于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的脱节而造成的影响,用古典阿拉伯语书写是无法产生真正的现代文学的,因为只有为数不多的受教育阶层才掌握这种语言。”
“那么为什么不去改变这种令人沮丧的状况呢?原因很简单,主要是人们担心如果完全抛弃《古兰经》的语言,那就意味着侵犯了宗教的神圣。结果是,这种宗教仪式用语仍然活跃在所有场合。”[19]
斯佩特的真正用意是让阿拉伯语远离生活的舞台,而局限于宗教场合,下一步就是将伊斯兰教局限于清真寺。这种理论是符合殖民者需要的,他们甚至认为,阿拉伯语作为《古兰经》的语言,应该和拉丁语、古希腊语和古叙利亚语一样,只属于那些牧师、神父和祭司在进行宗教仪式时使用,一般人们不需要懂。斯佩特预告了阿拉伯语的“死亡”,如同历史上拉丁语的死亡一样。但是事实情况是,东西方巨大的历史文化差异使得发生在西方的一幕并没有在东方重演。
在威廉·斯佩特之后继任埃及书局董事长的埃及东方学家卡尔·沃勒斯(Karl Voller)(1857—1909)也持相同的主张,丢弃阿拉伯标准语,用土语进行书写。他写了一本书《现代阿拉伯方言》,不但主张取消标准语,更是主张土语用拉丁文进行书写。
英国的东方学者也发表过类似的学术观点,比如英国占领埃及后来担任开罗地方法官的塞尔顿·沃尔默(Selden Willmore, 1856—1931)在1901年出版了一本书《埃及的地方阿拉伯语》,提出用埃及土语替代标准语作为文学语言,要为其制定语法规则,并呼吁采用拉丁字母。
英国东方学者威廉·威尔考克斯(William Willcocks)(1852—1932)在1893年曾担任埃及《艾资哈尔》杂志的主编,他对待标准语的观点更为激进。他曾在这本文学杂志上发表过论文《为什么直到现在埃及人都没有产生创造的力量?》。他把埃及缺少发明创造的动力的原因归咎于使用标准阿拉伯语进行书写,主张废除标准语,用土语进行书写,但是他并没有充足的证据说明标准语是造成落后的原因,而土语是进步的力量。这不禁使人疑问:难道土语真的是推动阿拉伯社会进步的灵丹妙药,真的能去除阿拉伯人头脑中根深蒂固的部落意识等落后观念?
1925年,威尔考克斯将《圣经·新约》翻译成埃及土语,接着以英文发表了一篇论文《叙利亚、埃及、北非和马耳他现在讲迦太基语,而不是阿拉伯语!》他在文中宣称,在沙姆、埃及和马格里布地区以及马耳他所讲的方言土语本身就是伊斯兰征服前所讲的迦南语,或腓尼基语,或迦太基语,当它完成和标准阿拉伯语的连接后,受到很多标准语的影响,而标准语是一种不含任何高贵意义的空洞的语言:
“我们很轻易地就可以发现,在这些国家,它们的语言受到阿拉伯标准语的麻醉般的影响:对同等程度的听众,他们甚至都听不出这些靡靡之音的哪怕一个词。无论是对于无法阅读的人,还是接受教育的人,只要是使用阿拉伯标准语的,毫无例外地在头脑之中就已经杀死了所有发明创造的念头,因为这种语言只懂灌输,而无变通,这也使得这些国家的科学家无法产生原创的思想。”[20]
除了这些代表西方利益和学术观点的东方学者外,去标准语和土语化运动也得到了来自阿拉伯世界内部一些亲西方的学者和文学家的大力支持与推动。这场阿拉伯内部的关于阿拉伯语的“存废之争”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不能简单地以“爱国”或“卖国”给他们贴上标签,而应站在其时其地给予客观的评论。
鲁特菲·赛义德(1872—1963),埃及近代思想家、哲学家和启蒙运动先驱,是较早主张以埃及土语取代标准语的比较有影响的学者。当时,在埃及出现过一些实验的主张,主要涉及在各类市场开展对阿拉伯语书写的规范和改革,其中最有争议的就是阿卜杜·阿齐兹·法赫米(1870—1951)所提出的土语方案,曾引起保护阿拉伯语人士的极力反对。
最早在埃及发生的这场呼吁使用土语的运动慢慢传到别的阿拉伯国家和地区,其中就有黎巴嫩。
一些黎巴嫩基督教学者对此极力推崇,比如赛义德·阿格力(1911— )、艾尼斯·法利哈(1903—1993)和鲁瓦斯·阿瓦德(1915—1990)等。在1973年6月,在黎巴嫩巴尔马纳召开了外国机构筹备的学术会议。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消除标准拉伯语的影响、重视土语的应用。主要到会的是耶稣会修士,当时艾资哈尔清真寺的大阿訇阿卜杜·哈利姆(1910—1978)拒绝出席。
当时埃及也有一些学者主张在标准语和土语之间选择一种“中间语言”,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有陶菲格·哈基姆(1898—1987)和艾敏·胡力(1899—1966)等。塔哈·侯赛因(1889—1973)则主张对阿拉伯语采取“发展语言”策略,即替换阿拉伯语语法、或者对它进行改造,简化阿拉伯语词法和句法。但是这些主张在实际操作层面都很难实行,因为《古兰经》对阿拉伯语语法进行了严格的限定,仅是一些微小的改动就可能牵涉到全面的改革。
三、如何看待阿拉伯地区曾经存在过的古代文明
西方殖民主义出于战略上的考虑,对于伊斯兰教和阿拉伯民族采取了全方位和深层次的文化和思想渗透,极力打压可能促成阿拉伯民族主义和阿拉伯统一的思想和行动,对标准阿拉伯语更是实施“全方位围剿”——除了在思想理论界掀起“使用拉丁文”的浪潮以及大力主张各国采用土语取代标准语之外,还从另外一个角度对标准阿拉伯语实施“釜底抽薪”式的打击,即通过西方的东方学者和阿拉伯西化学者对曾经在阿拉伯地区存在过的古代文明实施发掘和研究,借而说明阿拉伯人并不是这块土地的唯一主人,历史上曾经兴起过很多发达的文明,他们并不讲阿拉伯语,也不信伊斯兰教,但他们也是这块土地上现在生活的人们的祖先。其最终目的是破坏阿拉伯人的民族身份认同,延缓或迟滞阿拉伯民族主义观念的蔓延,扶植地方主义、国家主义等分离观念,呼应以各地方言取代标准语的浪潮,打击阿拉伯团结和统一的努力,最终实现对阿拉伯地区长期“分而治之”的战略图谋。
法国社会学家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1841—1931)曾经说过:
“那些不屑于古波斯文明、古希腊文明和古罗马文明以及他们的语言,并沿袭了阿拉伯人语言、宗教和文明的埃及人将会发现,即使像埃及这样浸淫伊斯兰教已久的国家,尽管埃及人和阿拉伯征服者之间的子女繁衍甚多,经过两代或三代之后出现了新的人种,但埃及人还是有许多优越性,这基于它相对较少的阿拉伯血统的原因。埃及庞大的农民阶层仍然保有他们的宗教和语言,是时候该把他们的祖先及其生活图景还给他们的子孙了。”[21]
受复兴古代文明的影响,埃及有些学者呼吁回归法老文明及其生活方式,黎巴嫩也有学者呼吁回归腓尼基文明。这部分黎巴嫩学者坚称黎巴嫩人是在阿拉伯人之前居住在地中海东岸的腓尼基人的后代,他们在历史上不是阿拉伯人,而是腓尼基人子孙和基督教十字军王国后代的混血。在伊拉克,也有一些声音要求回归巴比伦文明和苏美尔文明,他们认为现在的伊拉克人是这些古老文明的后代,应该珍视这些文明的遗产,并继承他们的遗志。
总体来看,这些思潮和呼吁无一例外遭到了失败,其失败的原因,正如曾极力鼓吹回归法老文明的穆罕默德·哈桑尼·海卡尔(1923— )说的:
“法老时代的历史已经被时光无情的翻过,文明已经获得了新生,伊斯兰是唯一一颗能开花结果的种子,在这种文明中,生机勃发,孕育希望。”[22]
另一位曾主张复兴古代文明的学者艾哈迈德·哈桑·扎亚特(1885—1968)也不无沉痛地总结这段心路历程:
“这就是现在的埃及,建立在1300多年阿拉伯伊斯兰历史上的埃及。历史已经抹去了之前的印记,就像太阳抹去了无边的黑暗一样……君不见,埃及历经沧桑还残留些什么?除了被无情鞭打的残肢断臂,除了蒙冤受害的莽莽大众,除了《亡灵书》里时隐时现的孤魂野鬼,除了那些镌刻在石头上的谦恭的领袖,除了那些使人们远离现世的神话传说?埃及除了皈依于伊斯兰之外无法自立,它活力的源泉、力量的依存、文明的基础都来自于阿拉伯的召唤;埋有木乃伊的墓穴多已经空荡,石壁上依稀可见逝者的些许生平,如何才能抖落这些历史的尘埃,让我们以现代人的姿态重新认识古迹的宏伟和尼罗河的伟大?但是请永远要记取:你们所吹嘘的木乃伊身上的那种精神其实是‘阿姆鲁’(埃及的征服者,574—663)的精神,你们用以传述埃及光荣的语言是‘木达尔人’(北部阿拉伯人的祖先)的语言,你们借以弹奏出尼罗河韵律的竖琴是‘乌穆鲁·盖斯’(阿拉伯古代大诗人,阿拉伯诗歌的开创者)的竖琴。”[23]
这场由西方政界主导,学术界推动的旨在干扰和歪曲阿拉伯人民族身份认同的运动并没有取得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成功,反倒印证了历史和文化的不可逆性,反倒激发了阿拉伯知识界和大众的文化自豪感。
四、英法殖民语言对阿拉伯语的渗透和遏制
英法殖民主义是西方思潮的背后推手,他们通过接收留学生、派遣各类顾问、合作研究和勘察、建立西式学校等各种途径将西方思想输入到阿拉伯各国,首先影响知识阶层,进而影响大众阶层,最终达到输出西方文化和价值观、西化阿拉伯民族,进而实现自己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战略目标。为了做到对西方文化的认同,必须破坏阿拉伯民众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认同,这样才能让“新一代”和“旧时代”说再见,拥抱西方文化,成为西方势力在阿拉伯地区的代理人。
分化、瓦解阿拉伯民族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传承的最便捷途径就是对阿拉伯语下手,颠覆标准阿拉伯语的神圣地位,以外语或当地方言为通用语言,人为切断阿拉伯各国间的历史文化和语言联系,制造“国别认同”大于“民族认同”,造成事实上阿拉伯地区“分而治之”的局面,挑起他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阻碍阿拉伯民族的统一,进而遏制阿拉伯民族的复兴和崛起。
建立学校是英法在阿拉伯地区实施语言分化战略的重要步骤,而且效果远好于刺刀和大炮。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劳埃德勋爵(1925—1929年在任)1926年在亚历山大的维多利亚学院所做的演讲中对这一目标毫不掩饰:“我们应该尽其所能加强英国人民和埃及人民相互理解的渠道,这种相互理解曾是建立维多利亚学院的克罗默伯爵[24]的初衷。没有比建立学校、教授不同国籍的年轻人更好的途径了。这些年轻人(指学生)过不了多久就会赞同英国的观点,这是由于老师和学生们之间紧密的交往关系所致的。”
西方殖民统治致力于削弱阿拉伯语的地位,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是通过引进西方思想,引进西式教育,将殖民语言凌驾于阿拉伯语之上;另一方面鼓励和提倡方言、土语的研究和推广,彻底动摇标准阿拉伯语的地位和影响。除了这两方面的夹击之外,西方殖民者还大力推进阿拉伯地区的考古学和民俗学的发展,对这片土地上曾经繁盛过的法老文明、巴比伦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等展开研究。表面上是宣扬正常的学术和科研活动,其背后更深层次的动机也包括通过此类学术活动,配合殖民者开展宣传,破坏阿拉伯民众对于伊斯兰教和阿拉伯语的认同,用历史上的多元性特征来佐证当今殖民统治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以求取殖民统治的正当化和长期化。
西方殖民者在阿拉伯地区长期的统治,在语言领域留下很多痕迹,至今仍难以消除,比如说:
(1)很多企业名称冠以外文
比如说,车商 写成
写成 ,教育机构将自己命名为
,教育机构将自己命名为 ,而不是
,而不是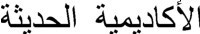 ,就连洗衣店也来赶时髦:
,就连洗衣店也来赶时髦: ,而不是标准语:
,而不是标准语:
 。类似的例子还有:电气工具店叫
。类似的例子还有:电气工具店叫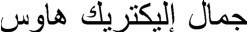 ,玩具店叫Royal Club,音像店叫
,玩具店叫Royal Club,音像店叫 ,眼部护理产品店叫Blue Eyes,设计公司叫
,眼部护理产品店叫Blue Eyes,设计公司叫 ,制冷企业叫
,制冷企业叫
 ,钱庄叫
,钱庄叫 ,古玩店叫
,古玩店叫 ,连阿拉伯人也不知道在
,连阿拉伯人也不知道在 后加一个后缀
后加一个后缀 ,到底表示什么意思。
,到底表示什么意思。
这样一些例子说明,外文已经严重侵蚀了阿拉伯语的纯洁性,亟待净化。
(2)日常用语夹杂外文
可以明显地感觉到,阿拉伯人的日常对话中会夹杂一些英文词汇,比如说:Ok,Hi,Bye Bye,Good Morning等,这样反倒显得“有文化”。尽管阿拉伯语有对应词,但是年轻人宁可用外文。
(3)电视和广播中充满外文
随着商业化的浪潮,电视等媒体追求收视率,外文电影和电视剧占据了屏幕,夹杂着外文的影响,威胁到阿拉伯语的纯洁性。
(4)西方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通过西方服饰、饮食、流行文化入侵阿拉伯文化
现在阿拉伯国家的街头遍布西式快餐店、年轻人热衷西式服饰如牛仔裤等、人们也比较向往西方式的“梦想”:住更大的房子、开更豪华的汽车、崇尚个人奋斗。西方生活方式的元素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潜移默化地改变着阿拉伯人的思维模式,影响着阿拉伯人的价值观,也使得阿拉伯语在词汇、表达方式等方面发生迁移,逐渐向西方“话语模式”靠拢。
注解:
[1] 苏·赖特著,陈新仁译,《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从民族主义到全球化》,第52页,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2] 阿卜杜拉·卡迪尔·马格里布开罗阿拉伯语学会学报《阿拉伯语》杂志,第36页,1935年刊.
[3] 曼苏尔·法赫米,开罗阿拉伯语学会学报《阿拉伯语》杂志,第18页,1957年刊.
[4] http://www.arabization.org.ma/objectifs.aspx
[5] http://www.arabization.org.ma/lexicaleettermindogiquedetravail.aspx
[6] 历次研讨会举办的时间、地点和主题请参见附录二。
[7] 历届翻译大会举办的时间、地点和主题请参见附录二。
[8] 即UDC(Universal Decimal Classification),又称为通用十进制分类法,国际通用的多文种综合性文献分类法,原由比利时人P.M.G.奥特莱和H.M.拉封丹在《杜威十进分类法》第6版的基础上编成,1899年起陆续以分册形式出版法文本(第一册为《物理科学卡片目录手册》),1905年汇编成《世界书目手册》,1927年的法文增订版改名《国际十进分类法》,后由国际文献联合会(FID)统一主持对它的修订工作。
[9] 可扩展标记语言,标准通用标记语言的子集,一种用于标记电子文件使其具有结构性的标记语言。
它可以用来标记数据、定义数据类型,是一种允许用户对自己的标记语言进行定义的源语言。它非常适合万维网传输,提供统一的方法来描述和交换独立于应用程序或供应商的结构化数据。
[10] 法赫德·哈利勒·扎耶德:《处于西化和犹太化之间的阿拉伯语》,第126页,雅法知识出版社和玛卡纳出版社,2006年版.
[11] 法赫德·哈利勒·扎耶德:《处于西化和犹太化之间的阿拉伯语》,第127页,雅法知识出版社和玛卡纳出版社,2006年版.
[12] 法赫德·哈利勒·扎耶德:《处于西化和犹太化之间的阿拉伯语》,第130页,雅法知识出版社和玛卡纳出版社,2006年版.
[13] 法赫德·哈利勒·扎耶德:《处于西化和犹太化之间的阿拉伯语》,第139—140页,雅法知识出版社和玛卡纳出版社,2006年版.
[14] 法赫德·哈利勒·扎耶德:《处于西化和犹太化之间的阿拉伯语》,第211页,雅法知识出版社和玛卡纳出版社,2006年版.
[15] 法赫德·哈利勒·扎耶德:《处于西化和犹太化之间的阿拉伯语》,第212页,雅法知识出版社和玛卡纳出版社,2006年版.
[16] 法赫德·哈利勒·扎耶德:《处于西化和犹太化之间的阿拉伯语》,第213页,雅法知识出版社和玛卡纳出版社,2006年版.
[17] 同上,第214页.
[18] 法赫德·哈利勒·扎耶德:《处于西化和犹太化之间的阿拉伯语》,第214页,雅法知识出版社和玛卡纳出版社,2006年版.
[19] 法赫德·哈利勒·扎耶德:《处于西化和犹太化之间的阿拉伯语》,第207页,雅法知识出版社和玛卡纳出版社,2006年版.
[20] 法赫德·哈利勒·扎耶德:《处于西化和犹太化之间的阿拉伯语》,第209页,雅法知识出版社和玛卡纳出版社,2006年版.
[21] 法赫德·哈利勒·扎耶德:《处于西化和犹太化之间的阿拉伯语》,第216页,雅法知识出版社和玛卡纳出版社,2006年版.
[22] 同上,第217页.
[23] 法赫德·哈利勒·扎耶德:《处于西化和犹太化之间的阿拉伯语》,第217页,雅法知识出版社和玛卡纳出版社,2006年版.
[24] 克罗默伯爵Evelyn Baring, 1st Earlof Cromer(1841年2月26日—1917年1月29日)原名艾弗林·巴林,英国行政官员和外交家,代表大英帝国管治埃及24年(1883—1907)之久,对埃及发展成为现代化国家有深刻影响。
 写成
写成 ,教育机构将自己命名为
,教育机构将自己命名为 ,而不是
,而不是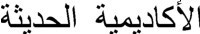 ,就连洗衣店也来赶时髦:
,就连洗衣店也来赶时髦: ,而不是标准语:
,而不是标准语:
 。类似的例子还有:电气工具店叫
。类似的例子还有:电气工具店叫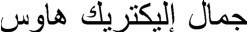 ,玩具店叫Royal Club,音像店叫
,玩具店叫Royal Club,音像店叫 ,眼部护理产品店叫Blue Eyes,设计公司叫
,眼部护理产品店叫Blue Eyes,设计公司叫 ,制冷企业叫
,制冷企业叫
 ,钱庄叫
,钱庄叫 ,古玩店叫
,古玩店叫 ,连阿拉伯人也不知道在
,连阿拉伯人也不知道在 后加一个后缀
后加一个后缀 ,到底表示什么意思。
,到底表示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