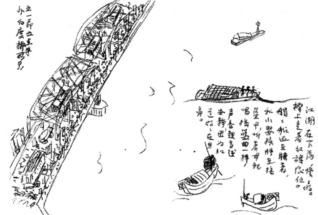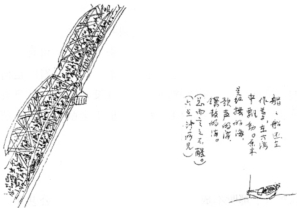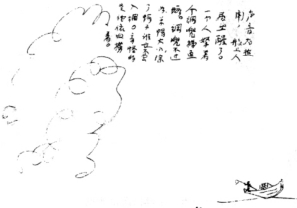-
1.1自序
-
1.2目录
-
1.3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从“关系”中理解“我”、文学、思想和文化实践
-
1.3.1一、有来路,才有自我
-
1.3.2二、人,没有装到新文学的框子里面
-
1.3.3三、文学里面有天地,比人的世界大
-
1.3.4四、守“常”察“变”,寻“本根”持“白心”
-
1.3.5五、选择、位置:偏之又偏,实得其正
-
1.3.6六、题目下面的题目
-
1.4“联接历史沟通人我”而长久活在历史中——门外谈沈从文的杂文物研究
-
1.4.1一、远因和选择
-
1.4.2二、杂文物和普通人,历史的长河和“抽象的抒情”
-
1.4.3三、物质文化史研究的观念和方法
-
1.4.4四、留给后代的礼物
-
1.5中国当代文学中沈从文传统的回响——《活着》《秦腔》《天香》和这个传统的不同部分的对话
-
1.5.1一、沈从文传统在当代
-
1.5.2二、活着,命运,历史,以及如何叙述
-
1.5.3三、个人的实感经验,乡土衰败的趋势,没有写出来的部分
-
1.5.4四、物的通观,文学和历史的通感,“抽象的抒情”
-
1.5.5五、回响:小叩小鸣,大叩大鸣
-
1.6“剪辑”成诗:沈从文的这些时刻
-
1.6.1翠翠,在杜鹃声中想起我
-
1.6.2绿百合
-
1.6.3豆彩碗
-
1.6.4迁移
-
1.6.5本书各文出处
-
1.6.6总 序
1
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