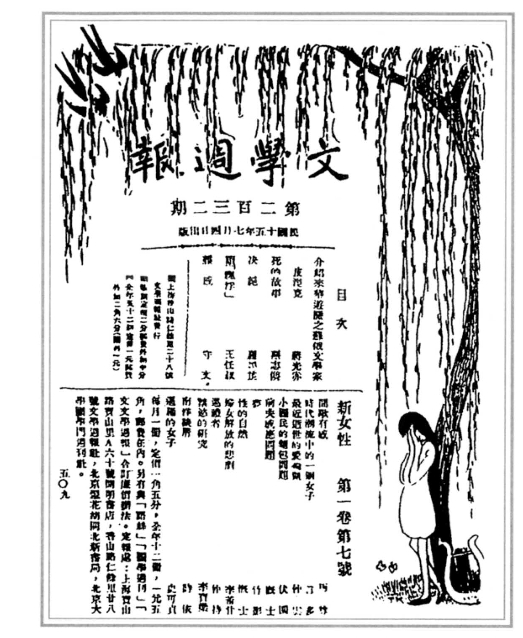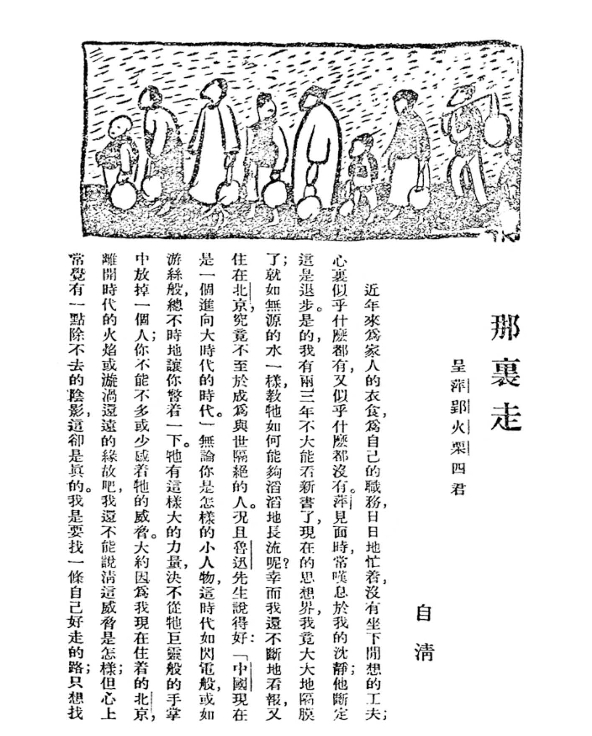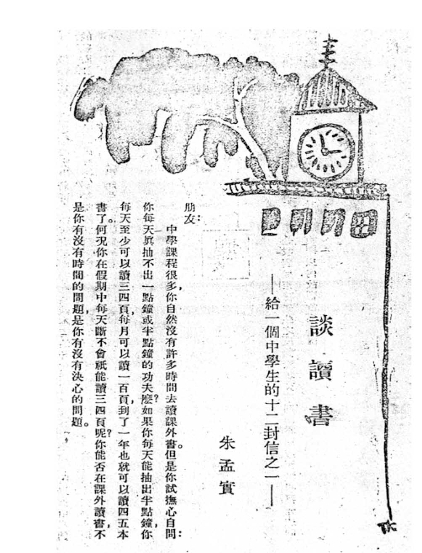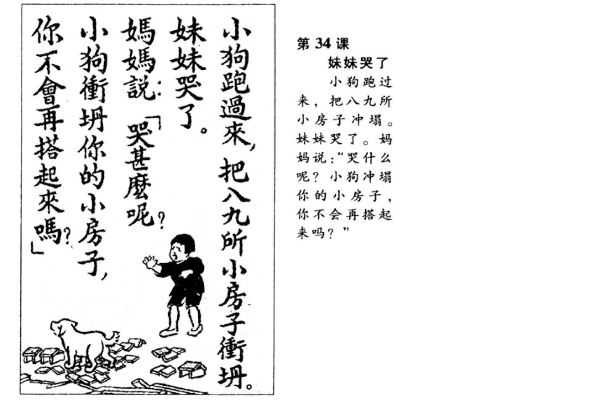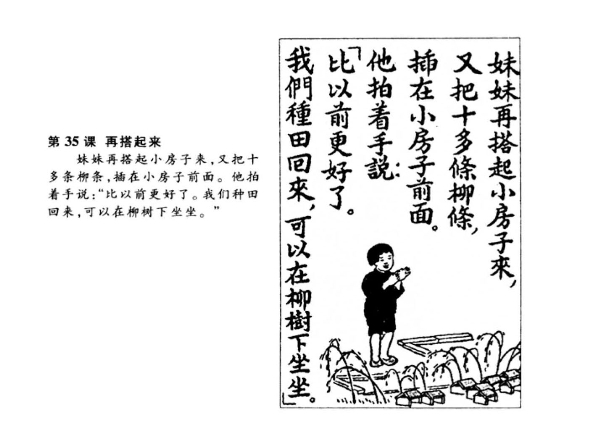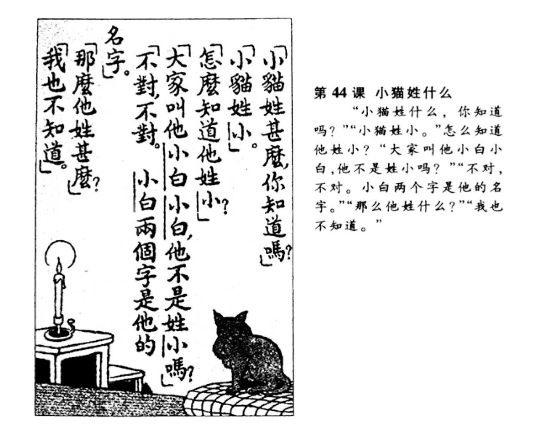-
1.1前 言
-
1.2目录
-
1.3小中见大 弦外余音——《子恺漫画》艺术探析
-
1.4《子恺漫画》溯源试答——答友人问
-
1.5中国现代木刻版画的先行者李叔同和丰子恺——记现代木刻版画的发现
-
1.6丰子恺套色木刻试析
-
1.7访朱光潜先生——关于《子恺漫画》的两次谈话
-
1.8丰子恺先生两张珍贵的封面设计
-
1.9谁是《中国青年》向丰子恺的约稿人?
-
1.10漫画名称的始用和普及
-
1.11《子恺漫画》初版时的佳话
-
1.12访叶圣陶先生——关于《子恺漫画》的两次谈话
-
1.13朱自清与丰子恺
-
1.14“纳须弥于芥子”——从《杨柳》看丰子恺散文的主要特色
-
1.15称名也小取类也大——《车厢社会》浅析
-
1.16追踪抗日战争“传单轰炸”的真相
-
1.17《百万传单乃百万重磅炸弹之种子》的历史意义
-
1.18中国近代美术的先驱者李叔同
-
1.19弘一大师广告艺术画发现始末
-
1.20李叔同的另外两个“最早”
-
1.21陈师曾简笔画的发现
-
1.22陈师曾的另外两幅简笔画
-
1.23文艺之“左”“根深蒂固”二例
-
1.24关于拓展丰子恺研究领域的思考
-
1.25忆子恺老师——纪念丰子恺先生逝世四周年
-
1.26学习丰老
-
1.27编后记
-
1.28参考文献
1
走近丰子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