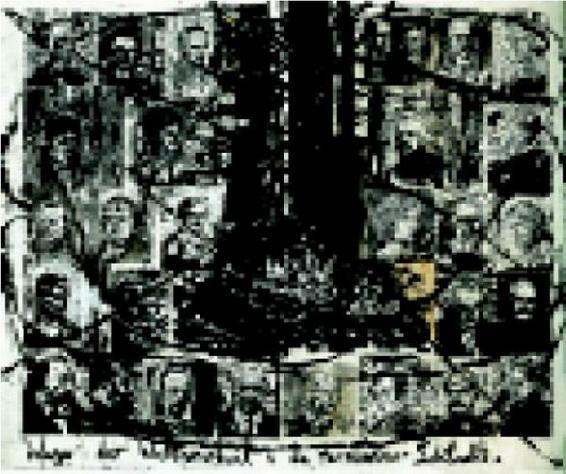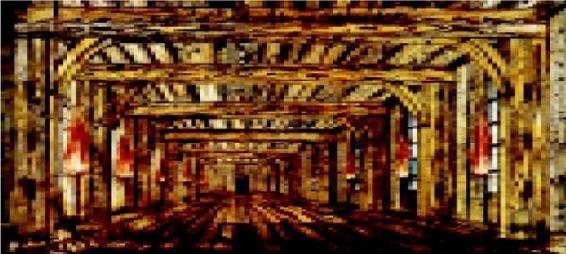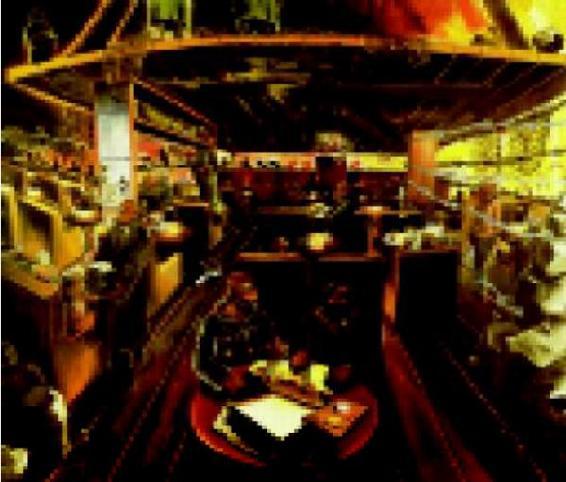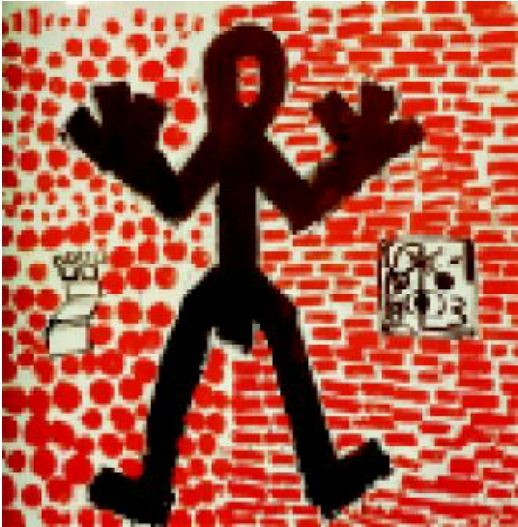-
1.1前言
-
1.2形而上画派 一个人的两个视觉
-
1.2.1■ 德·契里柯(Giorgio de Chirico,1888-1978)
-
1.2.2■ 卡罗·卡拉(Carlo Carra,1881-1966)
-
1.2.3■ 乔尔乔·莫兰迪(Giorgio Morandi,1890-1964)
-
1.3表现主义 抽象与移情
-
1.3.1■ 作为一种艺术思潮的“表现主义”
-
1.3.2■ 表现主义的重要先驱艺术家
-
1.3.3■ 四个早期德国表现主义艺术家
-
1.3.4■ 桥社的伟大友谊
-
1.3.5■ 表现主义的成熟阶段——青骑士社
-
1.3.6■ 新客观社
-
1.3.7■ 表现主义的评价
-
1.4抽象主义 “自在之画”
-
1.4.1■ 什么是抽象艺术
-
1.4.2■ 与抽象主义艺术擦肩而过
-
1.4.3■ 俄国对抽象主义艺术的贡献
-
1.4.4■ 康定斯基与蒙德里安
-
1.4.5■ 风格派的命运
-
1.4.6■ 抽象主义艺术的发展
-
1.5达达主义 一场游戏一场梦
-
1.5.1■ 苏黎世达达(1916-1919) 约翰(汉斯)· 阿尔普(Jean Hans Arp)
-
1.5.2■ 纽约达达(1915-1920)法兰西斯·皮卡比亚(Francis Picabia)马歇尔·杜尚(...
-
1.5.3■ 德国达达(1918-1923) 乔治·格罗兹(George Grosz) 约翰·哈特菲尔德(Jo...
-
1.5.4■ 巴黎达达(1919-1922)
-
1.6超现实主义 无意识写作
-
1.6.1■ 马克斯·恩斯特(Max Ernst,1891—1976)
-
1.6.2■ 霍安·米罗 (Joan Miro,1893—1983)
-
1.6.3■ 勒内·马格利特(Rene Magritte,1898-1967)
-
1.6.4■ 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i,1904—1989)
-
1.7波普艺术 机械复制时代的涂鸦
-
1.7.1■ 达达主义:现成品成为艺术
-
1.7.2■ 波普艺术的基本发展概况
-
1.7.3■ 波普艺术的主要特征
-
1.7.4■ 美国的波普艺术运动以及代表人物
-
1.7.5■ 英国的波普艺术以及代表人物
-
1.7.6■ 欧洲大陆的波普艺术:新现实主义
-
1.7.7■ 新波普艺术以及代表人物
-
1.8照相写实主义 “逼真”与“真实”
-
1.8.1■ 照相写实主义基本概况
-
1.8.2■ 与之相关的欧洲写实主义溯源
-
1.8.3■ 美国的写实主义溯源
-
1.8.4■ 照相写实主义绘画特征以及代表人物
-
1.8.5■ 照相写实主义的雕塑
-
1.9新具象艺术 使人们面对其命运的形象
-
1.9.1■ 一个相对宽泛的“新具象艺术”概念
-
1.9.2■ 20世纪上半叶各艺术流派中的具象背景
-
1.9.3■ 存在主义与具象表现绘画
-
1.9.4■ 对抽象主义的反动——波普艺术中的具象
-
1.9.5■ 照相写实主义与美国新具象艺术家
-
1.9.6■ 巴塞利茨和基弗—战后德国的具象绘画
-
1.9.7■ 弗洛伊德与英国具象绘画
-
1.9.8■ 后现代主义与美国新具象艺术
-
1.10大事记
-
1.11参考书目
-
1.12后记
1
视觉革命:观看 的现代艺术史(视觉不断的革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