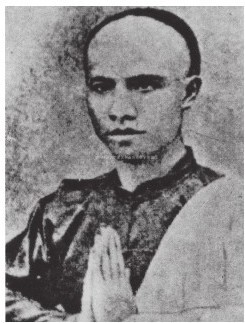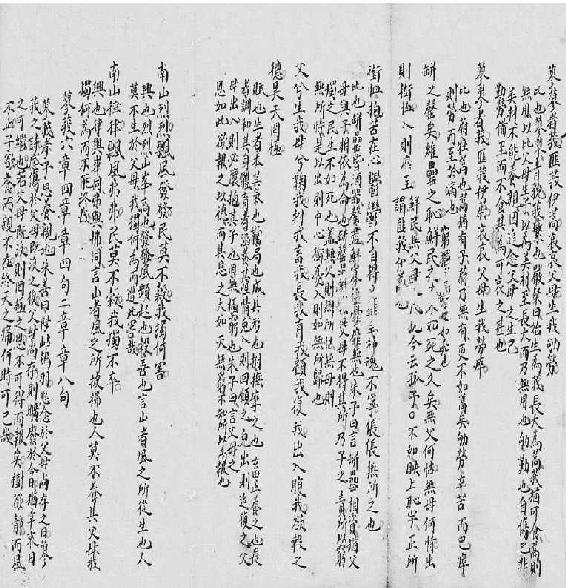谭嗣同:剑胆琴心法华相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遂相与一抱而别。初七八九三日,君复与侠士谋救皇上,事卒不成。初十日遂被逮。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数辈苦劝君东游,君不听。再四强之,君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梁启超《谭嗣同传》
“亘古不磨,片石苍茫立天地;一峦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涛。”这是谭嗣同墓前的一副楹联,也是对谭氏一生的最好诠释。想苍茫辽阔的天地之间,风云变幻,草木枯荣,无一不变易,唯有一块顽石亘古不变,以不灭之相、坚贞之形而傲然独立,此非日月之精耶!想岁月流转的时光大河之中,人如犬逐,道如石沉,罕有不崩颓,唯有一柱孤峰壁立千仞,以伟岸之魂、雄烈之魄而垂示万载,此非中流砥柱耶。谭嗣同之胆魄、识见、气度在维新诸人中堪称最佳者,其与梁启超相互砥砺,与康有为亦师亦友。执维新之牛耳的康有为曾评价他:“挟高士之才,负万夫之勇,学奥博而文雄奇,思深远而仁质厚,以天下为己任,以救中国为事,气猛志锐。”康氏晚岁虽成保皇之老朽,然此评则中肯至矣。
19世纪末传入的照相技术为我们留下了一些珍贵的照片,令吾辈能够一睹英雄的风采。谭嗣同存照不多,其中一幅全身照为笔者之最爱,他兀然而立,左手叉腰,右手轻提衣襟,一袭白袍敞开襟怀,英气逼人。他的脸上闪烁着皓月般的光芒,深邃的眸子忧郁而悲悯,令人想到华严法相。他本就是一个胸怀菩提心的人,期许使天下万民裕安,故而不惜舍身成仁。晚清中国风雨飘摇,内则百姓贫困不堪,饥寒交迫;外则列强相侵,烽火不断。胸怀救国之志的维新党人推行变法,一方面想改变统治者,一方面想唤醒普通民众,使这个国家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但是变法触及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利益,他们用屠刀将这次变革扼杀了。作为变法骨干,谭嗣同本可不死,但是他抱流血之志、必死之心,以“舍身饲虎”的精神成为惨烈的殉难者。
谭嗣同像
谭嗣同(公元1865年-1898年),字复生,号壮飞,又号华相众生、东海褰冥氏、廖天一阁主等,湖南浏阳人,是戊戌变法的骨干人物、戊戌六君子之一。谭氏家族自明代移居浏阳,其中多人因战功被封侯,是浏阳的望族,但是到了谭嗣同的祖父谭学琴时,家道已经中落。谭学琴少时家贫,未读过多少书,但为人机警聪颖、忠厚大度,因此被引为县衙的官差。他生活俭朴,积攒了一些钱,其家也算是小康。谭雪琴个人生活十分节俭,但对有困难的人却从不吝啬。亲戚族人向他借钱,他总是想尽办法予以满足。史载,谭家抽屉里装满了借据,多得塞都塞不下。谭雪琴病重,临终时嘱托子孙以读书为业,并吩咐家人将所有借据付之一炬,而不是作为遗产让儿子继承。这位老人的大度与豪迈可见一斑。
谭学琴去世时,其子谭继洵,也是就是谭嗣同的父亲才六岁,因一家人生活本就拮据,加上谭雪琴不要人家还钱,这个家庭就更加贫困了。谭继洵的哥哥谭继升颇有其父之风,一面苦苦支撑家庭,一面积极支持弟弟读书。谭继洵不负父兄之望,读书非常勤奋。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他考中举人;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考中进士;次年参加殿试,被咸丰帝钦点为户部主事(正六品),从此踏上仕途。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已经升任户部员外郎(正四品)的谭继洵家再添人丁,徐氏夫人在其北京宅内诞下一个男婴,他就是谭嗣同。这是个从小就桀骜不驯的孩子,既有其父亲刻苦读书、有志于学的一面,也有祖父豪迈大度、慷慨仁爱的遗风。十岁时,他与哥哥谭嗣襄拜大学者欧阳中鹄为师。欧阳氏是一个推崇实学的人,正是在欧阳氏的影响下,谭嗣同对王夫之的思想产生了兴趣,进而受到其思想的洗礼。王夫之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循天下之公”,王夫之曾猛烈批判历代的统治者,认为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而非君主一人的天下。这种思想闪烁着民主主义的光辉。谭嗣同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开始对当时的中国社会进行思考。他曾赞誉这位灵魂的导师:“万物招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
谭嗣同读书涉猎极为广博。他认为读书应以经世济民为要,因而对八股文深恶痛绝,在学制艺(即八股文)之学时,曾在课本上写下“岂有此理”四个大字。他仰慕古来之剑侠,对他们扶贫济弱、除暴安良的行为极为赞赏。十二岁时与京师大侠王正谊(即大刀王五)结交,向其学习剑术,还向外号通臂猿的胡七学习刀术。他待人平和,与出身江湖的王五、胡七平辈论交,绝无官家公子哥儿的傲气,因而深得王五等人的敬重与喜欢。
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被加二品官衔,任命为甘肃巩秦阶道(治所在今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道台,定于次年赴任。当年冬天,他随同父亲第一次回浏阳原籍。浏阳老宅“大夫第”保留着谭继洵昔年读书时的原貌,院内树木成荫,书房内书卷横陈。在原籍期间,谭嗣同日间读书,夜间习剑,并与浏阳人唐才常结为密友,是时谭嗣同十三岁,唐才常十一岁。谭嗣同曾作两联,其一曰:“惟将侠气流天地,别有狂名自古今。”其二曰:“除夕月无光,点一盏灯,替乾坤生色;今朝雷未动,击三通鼓,代天地扬威。”
正所谓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谭氏之辞,真有遗世而独步、睥睨天下之襟怀,真非常人也。谭唐二人思想相近,都胸怀救民报国之心,后世将二人合称为“浏阳双杰”,即缘于此。
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夏天,谭嗣同随赴任的父亲踏上西北之旅。当时西北大旱,数千里寸草不生,草木俱枯,饿殍遍野。盛夏时节暑气逼人,加上自然灾害,致使瘟疫蔓延,道路两侧的沟壑内尽是人尸,越往北灾情越严重,死者不绝于道,宛若人间地狱。谭嗣同父子一行数十人,同样未能逃脱厄运,途中两个幕僚病死,跟随的挑夫车夫有的病倒,有的逃跑,去之大半。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也病倒了,不得不在陕州停留。十四岁的谭嗣同因身体强健,居然安然无恙,但是父亲骤然病倒,令他方寸大乱。幸亏幕僚刘云田十分忠谨,沿途事无巨细悉数打理,鞍前马后亲奉汤药。
有一次,天黑地僻,谭继洵病情加重,只有十里之外有药铺,从者或不知路,或无胆量夜行,刘云田只得举着火把策马而去。夜极黑,火把只能照到前面一小片,他忽觉马蹄下踩到异物,急忙拿火把照看,原来踩到人尸,顿时大惊失色,纵马狂奔,一口气跑出数里地。或许是踩到人尸的恐惧,他居然将火把坠落于地,顿时陷入一片黑暗之中。无奈之下,刘云田只好下马,手脚并用探路往前走,伸手所及处多次摸到人尸。买药回来后,用灯一照,鞋袜俱被血水濡染,这是从尸堆里滚爬而出的结果。谭嗣同目睹这种惨状,以及灾害疾疫横行之下百姓的苦难,感同身受。在刘云田的细心照料下,谭继洵逐渐恢复健康,谭嗣同也与刘氏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此次西北之行,使谭嗣同对王夫之的思想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使他对君主专制下的中国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谭嗣同奉父命回到浏阳,此后三年均受教于“大围先生”凃启先(浏阳人,字舜臣)。涂氏的学术思想是“明体达用”,与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一脉相承。不过,涂氏所授之科目仍然未脱出儒家经典的范畴。叛逆的谭嗣同虽学习勤奋,但是对所学之经义却颇多不屑。他后来曾说:“虽受读瓣姜(欧阳中鹄)大围(涂启先)之门,终暴弃于童蒙无知之日。”可见,他少年时内心对经学一直很反感。当然,他年长后对欧阳中鹄和涂启先的学术之精又有了新的认识,故而对少年时未专心做学问而自责。在浏阳就学期间,他和唐才常、刘善涵、贝允昕多有往来,接触到一些自然科学,比如数学、地理学、物理学、化学等学科的知识,视野更加开阔。
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谭继洵对儿子的学业终究还是不太放心,因此命儿子赴甘肃,到其官衙内读书,以便亲自督导。大西北的自然环境十分恶劣,民风尤为剽悍,谭嗣同深受感染,常常策马行猎。光绪十年,谭嗣同离家出游,游历了直隶(今河北)、甘肃、新疆、陕西、河南、湖北、江西、江苏、安徽、浙江、山东、山西……大河上下,长城内外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尤其是在大西北,他曾多次纵马出行。在写给友人刘善涵的信中曾说:“飞土逐肉,掉鞅从禽。目营浩罕所屯,志驰伊吾以北。穹天泱漭,矢音敕勒之川;斗酒纵横,抵掌游侠之传。戊己校尉,椎牛相迎;河西少年,擎拳识面。”充满了对边塞生活的自豪之情。
谭嗣同将游历之所见,写进了诗词中,其中写西部的作品尤为精彩。他在《望海潮》一诗中说:“曾经沧海,又来沙漠,四千里外关河。骨相空谈,肠轮自转,回头十八年过。春梦醒来波,对春帆细雨,独自吟哦。唯有瓶花数枝,相伴不须多。寒江才脱渔蓑,剩风尘面貌,自看如何。铿不因人,形还问影,岂缘酒后颜酡。拔剑欲高歌。有几根侠骨,禁得揉搓?忽说此人是我,睁眼细瞧科。”
谭嗣同手札
好一个“有几根侠骨,禁得揉搓?”便是这首词,也足以流传千古矣,又何必杀身成仁。大西北的旷古苍凉深深影响了谭嗣同,于此笔者颇有“戚戚焉”之感。盖笔者对此苍茫山河亦壮之,况为吾故乡耳。这个时候的谭嗣同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坚韧与胆略。他在《与沈小沂书》中说:“嗣同弱娴技击,身手尚便,长弄弧矢,尤乐驰骋。往客河西,尝於隆冬朔雪,挟一骑兵,间道疾驰,凡七昼夜,行千六百里。岩谷阻深,都无人迹,载饥载渴,斧冰作糜。比达,髀肉狼藉,濡染裈裆。此同辈所目骇神战,而嗣同殊不觉。”纵马大漠七昼夜,长驱一千六百余里,以至于大腿内侧血肉模糊,其同伴无不骇然,而他却不以为意。
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战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次年5月2日,康有为联合在京参加考试的举子们上书清政府,呼吁“拒和变法”,从而拉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1898年谭嗣同与唐才常在湖南长沙创立南学会,并创办了《湘报》,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改革的学说,以“新政人才”而知名。同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谭嗣同被推荐给光绪帝,得到了光绪帝的召见,并和林旭、刘光第、杨锐一起被授予四品卿衔,参与新政。光绪帝变法之心极为强烈,曾下诏说:“汝等所欲变者,俱可随意奏来,我必依从。即我有过失,汝等当面责我,我必速改。”但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力量十分强大,变法在不触动守旧派的前提下尚能维持,一旦触及守旧派的利益,便遭到他们的强烈抵制。
唐才常像
谭嗣同在推行新政时已感受到来自多方面的阻挠,而顽固派对维新志士尤其切齿痛恨。当时传言慈禧太后要借秋季赴天津阅兵之时废掉光绪帝,维新人士们预感不妙,但却相顾无策。与袁世凯仅有数面之缘的康有为认为,只有袁氏可以帮他们。9月18日,谭嗣同夜访住在法华寺的袁世凯,要袁氏带兵进入北京除掉顽固派势力。老袁虚与委蛇,始终推诿,后见谭嗣同面有怒色,恐其怀有利器,便假意答应先回天津除掉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然后率兵入京。但袁世凯回到天津后,立即将此事密报荣禄,出卖了维新志士。袁世凯出卖维新志士与否,因史料记录漏洞颇多,故而很多人持怀疑态度,笔者于此存疑。
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缇骑四出,逮捕维新派人士。康有为、梁启超等事先获得消息,俱躲入外国大使馆。友人劝谭嗣同也躲避一下,以图卷土重来,谭嗣同却拒绝了这一建议。他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他将自己的书信、文稿交给梁启超保管,决定以身殉道,唤醒国人。当时,日本使馆方面提出为谭嗣同提供庇护,谭嗣同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毅然回绝了庇护的建议。
9月24日凌晨,谭嗣同端坐在灯下,他估计清政府的缇骑天亮前就会来。为了不连累家人,他模仿父亲的笔迹伪造了七封父亲的信,每封信的内容都是父亲对他的申饬。后来,谭嗣同被捕,连同其居所内所有书信均被查获,提刑官员将搜集的书信上报给慈禧太后,慈禧太后认为谭继洵并非不教子,而是谭嗣同并非孝子,故而未予连坐,只是让谭继洵回归故里了事。
9月28日,清政府将谭嗣同、杨深秀、刘光第、林旭、杨锐、康广仁等六人押赴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当他们的囚车穿过街衢时,市民们愤怒地向他们抛烂菜叶、吐口水。深夜读史,当读到这一不为人注意的细节时,我忽然感到非常悲哀。我常以为,英雄殉难,民众应该表现出愤慨,但事实却是周星驰电影里扔烂菜帮子的那一幕。我们的民族多的是麻木的看客,多的是乡愿,多的是“打酱油者”,罕有勇于站出来担当者或表达愤慨者。偶有几个勇于承担的脊梁,却被看客们吐满了口水。
谭嗣同在其著作《仁学》中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唯大盗利用乡愿,唯乡愿工媚大盗。”他的死仍然未能唤醒这个乡愿的民族,当他被大盗屠杀时,他看到的是乡愿们的围观。历史从来不惮以恶意来呈现人的卑劣,尤其是群体性的卑劣。明朝末年袁崇焕在宁远积极抗清,但因清军绕过宁远,从内蒙古一线绕道进攻北京,赶来勤王的袁崇焕被崇祯帝下狱,处决时市民们争相购买他的肉,更有人冲上去撕咬他,他绝不会想到他曾保护的这些人会如此痛恨他。有私仇否?没有。那是为何?
李敖先生在《北京法源寺》中有精辟的论述,他说:“个人只有和群体的大多数一起浮沉,才能免于被残忍对待。个人太优秀了、太特立独行了,就容易遭到群体的迫害。群体是最残忍的,个人比较好。群体比个人不是更好就是更坏,群体比个人极端得多。所以,优秀的个人如果优秀得过分,就要准备付出惨痛的代价给群体,作为‘冒犯费’。所以,许多优秀的个人为群体做事,必须事先就得抱有最后还得被群体出卖的危险。”什么是群体性的极端?起哄式的狂热就是群体性极端,鲁迅先生的小说《药》里面那些观看杀人并为之起哄的人就是群体性极端,他们是“看客”的代名词。到了21世纪的今天,我们真的摆脱了看客的身份吗?不尽然。打酱油者也,俯卧撑者也,躲猫猫者也……深夜读史,每读至谭嗣同遇难之时看客们的表现,就感到后背一阵阵发凉。
鲁迅先生曾经将黑暗的时代比喻为铁屋子,他企图用呐喊来唤醒沉睡的、将要被闷死的人们。可惜,那些从黑甜梦乡中醒来的人却未见得领情,反而会责怪他惊醒了自己的梦。市民吐口水的行为,很好地说明了这一切。
谭嗣同故居,位于北京市宣武区北半截胡同41号,现在已成为民宅。
谭嗣同遇难时,观者如潮,他大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然后从容就戮,年仅三十三岁。谭嗣同对佛学悟之甚深,他不但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更有一种视万物如一的精神,他所倡导之爱,不仅及于人,更及于一切生命。他的爱是人间的大爱,他有佛一样的心肠,正所谓佛本多情,他才能为了唤醒众生而决绝地死。笔者早年读李敖先生的《北京法源寺》,曾与内子专程在京城寻访法源寺,至宣武门外教子胡同犹未见,问道于路人,于斯言谭嗣同,皆茫然不知。幸问一老者,方知在胡同南端东侧。步入寺中,古木参天,梵音声声入耳,我闭目肃立,试图感受谭嗣同在寺中盘桓的心境。是时,钟声大作,余悲而之于赋诗:为君豪壮知湖南,弹指刹那百余年。抚剑扬眉思壮飞,仰天大呼忆复生。侠骨丹心今不见,江山更新悲从前。欲换乾坤肯惜血,佛国莲花释一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