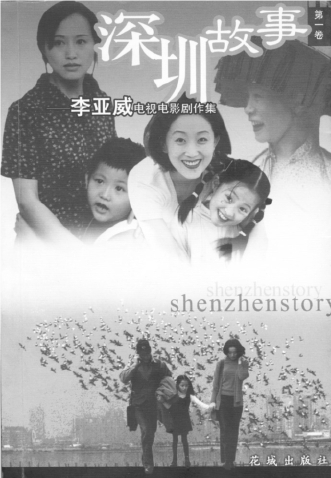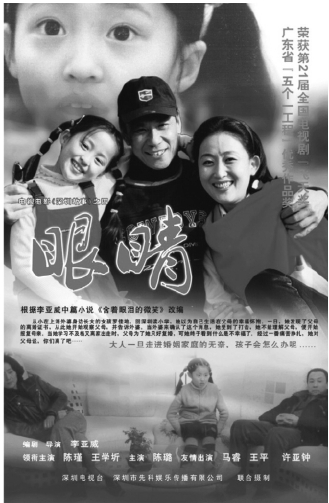胶着于现实的艺术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的鹏城——这个在举世瞩目的“深圳速度”中奇迹般崛起的新兴城市,已经傲然地向世人展示并证明了自己的存在与价值,当巍峨炫目的地王大厦,高冷地耸峙在繁华喧闹的深南大道之上时(这座深圳的地标式建筑建成于一九九六年),人们在对其“四十五度角”仰望的过程中,也产生了多少“华丽的伤感”和惶惑——在这座“六亲不认”的城市里,每一个人都必须用“实力”来证明自己的存在。
当时的深圳,以象征着“梧桐树”的亚洲第一高楼地王大厦为标志,吸引了无数的“孔雀东南飞”。然而,当那些翩翩而来的“孔雀”们“绕树三匝”,试图择枝而栖之时,心中顿然醒悟:这里不是论资排辈的地方,以往的荣耀已如过眼云烟,一切必须从头开始。
李亚威当年面对的正是这样一种情形,虽然来到深圳之前,她有着“显赫”的背景和不俗的业绩——论资历:她是新中国电影发祥地长春电影制片厂的艺术处处长。论业绩:她创作的剧本曾经获得国际电影节的奖项,她本人也已经执导过电视剧《酿酒人》《穿红马甲的女人》及三十多首MTV的影像作品。但So what,那又如何?过去的成功并不能证明你现在的价值,是骡子是马,还得“再”拉出来“遛遛”。
李亚威这样诉说过她当年的感受:
“从长影来深圳后的第一年,我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这里的人们,不认你过去是谁。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这是我的第一个感受,你过去是什么不重要;第二个感受,就是你得做出东西来,如果你什么也没做出来,别人就认为其实你也不过如此;第三给我的冲击,是这里的节奏特别快,我原来在长影的时候,节奏也不慢,艺术处每年跟着二十一部影片转,我因为是处长,比其他同志忙一些。可到了深圳,不一样了,城市的各个角落,人们的神情,让你感觉到有点紧张,不知把心放哪。所以,一九九五年,我开始走入创作阶段,我先走进了幼儿园,当时左翎的妈妈在深圳的幼儿园当园长,左翎在上海拍片的余暇,来深看我,我就顺理成章,得天独厚地开始了我伸进城市的第一个角落——幼儿园。我还不止去了一所,去了四五所。那种新城市里的幼儿园及园长们的观念,让我兴奋不已。
“我到深圳写的第一个电影,我的印象很深。一九九五年春节到了,我看到了整个城市就像一座空城一样,下了雨颜色很浅,楼是那种感觉很‘歪’的感觉,不知道是楼变了,还是我眼睛看(着)的感觉,那种感觉让我感到所有这座城市的人都回到自己心爱的家乡,这座城,在那(一刻)很孤独,给我触动很大,我就开始写故事。《深圳故事》诞生了。”
李亚威是一个顽强地追逐理想的人,放着好好的长影厂处长不当,南下深圳既不是冲着当官,也不是冲着发财,而是冲着她的艺术理想而来的。只是当她的艺术理想盘旋、俯冲并试图降临于现实的大地之时,李亚威还是明显地感觉到,现实的“大地”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平整、顺溜,而是布满了凹凸和粗砺,要想“温柔地”走入那个理想中的“良夜”,绝非易事!这让她意识到:必须及时调整自己的角度和姿势,让理想与现实之间有一个相对“缓冲”的结合。
“我以为我到这里会把我自己一系列的故事,或者在长影不能完成的那些创作任务,一股脑在这片土地上写出来。可是来了以后,一切都不是这样了,我攒起来的那些故事,我都不要了,因为这个地方的火热生活,完全跟我过去不一样。那些攒起来的故事是高高在上的,不接地气的,我的《女特警》啊,《上海滩》啊,这只是在商业最盛行的时候(才有可能)。但是来到这儿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活生生的现实,使得你不得不向它低头,你每天跟朋友在一起创作、工作,甚至于每一天,你回到家中,你冲凉,都要冲好多遍,所以时势造英雄一点都不错,后来我所有的想法都变了。我在一九九五年,完全融入了这个城市,到了一九九六年,我开始进行创作。开头写的都是小说,到一九九六年下半年,我就开始(把它)变成剧本。”
此时的李亚威,既开始张开双臂拥抱特区火热的现实生活,同时又执着沉迷于她的艺术创作,现实与艺术犬牙交错,难分彼此;生活与创作相互碰撞,火花飞溅,艺术在生活中“进行”,生活在艺术中延宕。
“来到深圳,对北方来的人要扒掉几层皮;一是脸皮,遇事不要不好意思,直来直去;二是天气的燥热,身体不适不断掉皮,长出新皮,迎接一种脱胎换骨的过程。
“我当时住在黄木岗一室一厅的周转房。是当时市文联给我的最方便的地点。晚上很热,来到深圳最怕的就是蟑螂,还有爬墙虎,晚上一开灯,就是一个爬墙虎,或者大蟑螂,很吓人。除了蟑螂还有老鼠,晚上(经常)跟老鼠搏斗。当时的环境,我是一边(在)创作的过程中,一边就有一些老鼠伴随着,或者有一些蟑螂。但是那个时期(的生活)是原汁原味的,我感到我的生活是落地的,无论是写故事,还是什么,都是别的朋友来讲他们的朋友的故事。比如说《红跑车》,就是一个朋友说(给我听)的,她哭得天昏地暗。我根据他们讲的(故事),开始创作《深圳故事》。那时候,我天天跟自己搏斗。一个懒惰的我和一个要做事的我,天天围着我打架。我的灵魂在涅槃……
“一九九四到一九九六年,扑面而来的生活像一阵阵清风,不断地冲击着我的内心。除了工作以外,我便开始感受当时那些生活,有很多是我听到的。一些是悲惨的,他们混不下去就离开了,有的著名画家来了不久,画了不少,卖不出去,就又离开了。听见比较揪心的,很多天睡不着觉。听到喜悦的也睡不着觉,当你听到一个故事的时候,就想深入写下去,比如:我居然为了写一个幼儿园,前后用了一年半时间。我采访了十个幼儿园的园长,不断到幼儿园去采访,去看那些孩子。当这个时候,我就好像有了一个新的生命,我每一次望着他们的时候,甚至坐在那里看见他们生活的时候,会觉得我还是一个创作者。”
《深圳故事》系列作品呈现并见证了李亚威这一时期的艺术胶着于现实的过程。
最初的《深圳故事》系列作品中的四个剧本,全部改编于李亚威自己创作的小说,而且都与她在特区的生活直接或间接地关联着,牵扯着。
《红跑车》改编于小说《夏日恋情》。一九九六年夏,李亚威的一个朋友,在她的红跑车里,跟李亚威诉说了她爱上一个有妇之夫,充当了第三者,让李亚威深有触动。她便以此故事为原点,创作了小说《夏日恋情》,将生活在“特区”中的女人撕心裂肺的痛苦,自己与自己厮杀搏斗的情景刻画得淋漓尽致。小说完成后被章列兵先生看中,在其建议与支持下,李亚威于一九九七年将小说改编成剧本,并于同一年拍摄成电视电影,《深圳故事》系列的第一部作品并由此诞生。
拍摄于一九九八年的《妈妈飘着长头发》,改编于李亚威的小说《谎言》。这部小说,源自李亚威本人的亲身经历。对于深圳这样一个“移民城市”来说,来自不同地域的人们带着自己的梦想来到这里拼搏,同时也就伴随着由此产生的各种生存压力、惶惑和陌生感。一九九五年的夏天,李亚威遇到了一个误把她认为是自己妈妈的小女孩,她被女孩的天真和无助所打动。小说《谎言》的创作,正是出于一次偶遇的触发。小说改成剧本后,因其别致的视角和扎实的情节,引来了刘洁、佟凡、阎青妤等演员的无条件加盟,奚美娟还来做了艺术指导。
《妈妈飘着长头发》海报
《红跑车》海报
《升》是《深圳故事》中与李亚威的“现实生活”最有“距离”感,虚构成分最多的一部作品。一九九七年,李亚威对深圳周边客家人的“大围屋”产生了浓烈的兴趣,她接连去了龙岗、梅州等传统客家人居住和生活的区域体验生活,并根据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创作了小说《捡的》。著名演员奚美娟看了小说之后,很喜欢其中的“楚二娘”这个人物,便鼓励李亚威将其改编成影视作品,还允诺出演剧中的“楚二娘”。《深圳故事》开拍之后,奚美娟一直担任着剧组的艺术指导,在奚美娟的鼓励与支持下,李亚威很快将小说改编成剧本,并于一九九九年拍摄完成了《升》。
二○○三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的《深圳故事——李亚威电视电影剧作集》封面
荣获了第二十一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二等奖的《眼睛》,同样改编于李亚威的小说。这部创作于一九九八年的中篇小说《含着眼泪的微笑》,在审稿阶段,就被业内人士认为“更适合拍电影”,于是李亚威便以最快的速度,在原小说的基础上,创作了《眼睛》的剧本,由于等待主演陈瑾、王学圻的档期,二○○○年一月才将其搬上了荧屏。
从《深圳故事》前四部作品的取材、改编和创作的过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艺术与现实那种水乳交融般的互渗和胶着,但事实上,这种艺术胶着于现实的情形,还不仅仅表现在创作之中,另外,还体现在拍摄、制作的各个环节。
作为一个电影导演,李亚威与别人不同的地方在于,从她的执导生涯开始,她就不是一个“纯粹”的导演。用李亚威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多数时候,是“一条龙”式的运作,即她自己既是编剧,又是舞美,既当导演,又是制片,有时还兼着作曲,集“创、编、导、拍、制”于一身。这种“一条龙”式的运作方式,镌刻着浓烈的深圳特色和那个时代的印记。
《升》海报
《眼睛》海报
李亚威曾这样描述她当年的生活:
“当时《深圳故事》我先是把我的小说给投资方看,投资方觉得有意思,我就改成剧本,他就出资了。出资的时候,我就用这个本子先找到一个制片人,因为我是做电影的,我先找到一个制片人,给我做下手,我就开始选演员,选外景,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就开始按照我的本子进行运作。我的资金是非常少,还有一部分是(来自)赞助,应该说我在做这个过程中,全部都是用我最坚强的毅力和我的人脉关系来做成的。因为那个时候做,又要把资金给人家卖(赚)回来,又要得到奖项,然后又要在奖项的基础上,能够给人家发行得很好,所以压力很大。在那个时期里,每一次做这个事情,我都是非常非常累地去做,一年做一次,都大病一场,但是我(还是)很想探索这样一条路。我不是拿不到钱,我不愿意给人家(造成)损失,万一卖不回来,就砸了,所以每一次资金都很少,当时人家也说,你就要点钱,何必这么紧张呢?
“我在做《深圳故事》的时候,没有一个(片子)是超过三十万元的。一拍片的时候,我家里整个就变成了道具仓库,那时候,我妈妈还活着,组里人都管妈妈叫‘剧务老妈’!
“妈一来就帮我拿(东西)道具,一会儿给大家做饭。”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李亚威对记者回忆起当年她遇到的一次“动荡”:
“拍《眼睛》的时候,演员已经上了飞机,结果投资的老板忽然撤资了,我一夜之间几乎头发全白了。然后,我把房产证压了上去,片子接着拍。人要守信义,我不能让组里人一下飞机就失望啊!但,在这个动荡当中我是非常受刺激的。”
在《深圳故事》的创作和拍摄的过程中,李亚威固然一方面承受着来自现实生活的种种压力和挑战,但同时也感受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温暖和支持,在这些温暖和支持中,让李亚威尤其感念的人之一,就是当年广东电视台分管电视剧的副台长张木桂。在《深圳故事——李亚威电视电影剧作集》一书中,张木桂曾这样回忆和评价《深圳故事》:
“一九九七年秋天,我尚在广东电视台分管电视剧、文艺节目的副台长任上。电视剧制作部门送来了一部名为《深圳故事》的系列剧八集故事大纲和两集已写成的儿童剧文学剧本《妈妈飘着长头发》。”
在看了大纲和剧本之后,作为一名资深并有着相当鉴赏力和判断力的影视从业者,张木桂“内心十分兴奋。作为一个从事电视剧编辑的人来说,我极少看到如此超凡脱俗,创作态度如此严谨的单元剧,大体上可以认定为每部戏都是一部电视电影。”
那么,《深圳故事》究竟是靠什么,打动了这位当年广东电视行业资深的“大佬”级人物的呢?张木桂认为:
“贯穿《深圳故事》的是它独特的人文关怀主题。人文关怀是一个哲学命题,是从人学的基本点来把握文艺精神的价值取向……李亚威在她的《深圳故事》中,以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提醒人们在艺术创作中要注意防止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缺失”;“李亚威的作品总让人觉得有法国、意大利电影的韵味”;“在李亚威的镜头下,没有惊心动魄的故事,没有让人心悸的悬念,她只是以她所学的小提琴那样,娓娓地向观众倾诉人生的体验,既率真又含蓄;不红而娇,淡极始艳,在淡淡的故事情节和隽永的意境中,与观众一起去感悟人生,解读生命”。
或许也正因为如此,张木桂在连李亚威是男是女都搞不清的情况下,就为《深圳故事》的创作和拍摄大开绿灯。李亚威说,《深圳故事》每拍完一部,送审到张木桂那里,“他都会给我一个评语,然后几乎每一部他都很欣喜”。
当然,《深圳故事》的成功背后,我们还可以看到深圳相关部门的领导和李亚威一起并肩走过的同事及章列兵、奚美娟们的身影。
如果我们不了解《深圳故事》是在怎样的一个情形之下创作、运行的“实况”,我们就很难触摸它想呈现的生活内核和它之所以展现出来的精神面貌——每一点来自生活的鲜活感受,都会触发艺术创作的冲动;每一次创作冲动的背后,总是负荷着现实的各种羁绊,致使想象的翅膀常常只能在现实的“低空”盘旋,艺术空间的“降维”,也许就成了不可避免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