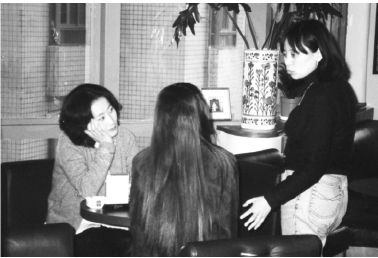五
这事要说清楚,还得从更早的时候说起。
拍摄《火之舞》对于李亚威来说,其艰辛、困顿、磨难、窘迫和拼搏,在她的从业生涯中,是前所未有的。
作为一位影视导演,李亚威与别人不同的地方在于:从她的执导生涯开始,她就不是一个“纯粹”的导演,用李亚威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多数时候,是“一条龙”式的运作,即她自己既是编剧,又做舞美,既当导演,又是制片人,有时还兼着作曲,集“创、编、导、拍、制”于一身。这种“一条龙”式的运作方式,一个好处是能锻炼人,能让她对影视创作的各个环节,方方面面都了然于胸,但缺点也很明显:精力分散,耗时耗力,为了一点资金或者琐事,李亚威都不得不亲力亲为,还可能要四处求爷爷告奶奶,很多时间和精力无谓地消耗在创作之外的事情上。
“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这是宋代大诗人陆游八十四岁时写给儿子陆遹的一首诗中的两句,意思是若想写出好的诗章,仅在诗的本身上下功夫是不够的,还必须把眼光和实践拓宽到诗之外的域界,积累知识,修身养性,格物致知。但现今中国社会中,“诗外”的功夫,却往往指的不是这些,而是指人际关系的搭建,外部资源的整合与自我的营销推介,长袖善舞有时是“诗外”功夫的最好注脚,所谓“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而这些,又都不是李亚威擅长和喜欢的。
“在我拍片子的过程中,从来就没有一部是资金现成,剧本现成,条件具备,只等着我去拍就行了的片子。我往往边创作剧本,边筹集资金,边组建团队,十分操劳。”李亚威说。
也许从小受到的教育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李亚威在她的人生经历中,已经习惯了在克服困难中前行,在不断地挑战自我的极限中实现超越。如若不然,当初她放着好端端的长影艺术处处长不当,毅然只身来到深圳重新创业,就无法有更好的解释。
应该说李亚威原本可以一直过着她优雅闲适,洒脱浪漫的艺术人生。从七岁半开始,李亚威就在父母的倡导下学习音乐,应该说,这个在今天看来极具“战略眼光”的决定,为李亚威之后的人生航道,架设了第一个航标,也为李亚威的人生梦想,抹上了最初的绚烂底色。要知道,这种人生航向的设定,与当时那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有着很大的偏差,甚至还有着很大的政治风险。
李亚威从孩童时代开始,就对音乐表现出了与同龄人不一样的兴趣和领悟力。七八岁的时候,偶然一次机会听到了法国作曲家马思涅的《沉思》,她竟泪流满面。可就在她开始学琴不久,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便席卷神州大地,她父亲也因为“走资派”的身份,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在那个荒谬的年代,音乐、艺术,作为“封、资、修”的“毒草”,已经被革命风暴扫进了时代的垃圾堆,而此时已经成了社会的“边缘人”的李亚威父母,在那样的条件下,心中依然倔强地守望着人类文明的价值底线,坚信民族文明的伊甸园不会就这么永远地荒芜下去,艺术的花朵最终还会绽放在这个国家的文化舞台上。尽管在当时的条件下,看不出学琴有什么“发展前途”,弄不好还会带来一定的政治风险,但她的父母还是坚持不懈地督促女儿在音乐的天地中发奋地攀援。
在《深圳故事·李亚威电影电视剧作集》一书的后记中,李亚威曾这样记述她童年的往事:
“我童年的时候,母亲在我六岁生日里,给我买了一把秦琴,那是二十五元一把的秦琴,母亲要节省一个月的工资,才能买这把我喜爱的弹拨乐器。事过多年,我的小提琴在音乐学院毕业了,母亲还在擦那把落上了尘土的秦琴。母亲说,人是不能忘记自己的起步的。
……
从小对音乐有着某种特殊的领悟和天赋的李亚威,在父亲的督促和母亲的支持鼓励下,卓然独立于那个纷乱的年代,徜徉在自己的艺术天地之中。
正应了“机会永远是属于那些准备好了的人”那句话,十三岁那年,被艺术女神所青睐,在许多同龄人不得不忙着“战天斗地”,修理地球的时候,李亚威以一技之长幸运地被招入了辽宁铁岭地区文工团。六年后,她又考进沈阳音乐学院深造,毕业后分配到长影乐团任小提琴演奏员。
要知道在当时的那个时代,那可是引来无数艳羡目光的工作。可是天性不安分,并有着更高远的人生和艺术追求的她,却并不满足于捧上一个让人羡慕的“铁饭碗”,她在音乐之外,自己还学起了建筑、绘画,甚至还创作和发表了诗作。
在李亚威的人生长旅中,她曾一次又一次地“改换门庭”,变更身份,向着既朦胧又清晰的人生目标,一步一个脚印地迈进。先是长影《电影晚报》记者、信息主任,再是长影艺术处处长,再然后是深圳。
一九八二年在长春电影制片厂乐团的时候
沈阳音乐学院毕业后分配到长影乐团报到的前一天
一九九六年,在深圳为一个专题片拉了一段小提琴
在长影厂乐团任乐手期间,李亚威曾先后被选送到中央音乐学院和巴黎音乐学院师从布莱教授进修深造。随着对音乐了解的加深,她对自己的人生定位也出现了新的认识。就在她从巴黎深造回来不久,她忽然发现:音乐,特别是交响乐,也许并不太适合她自己和那个时代,而文学和写作还有电影,对于她也许有着更广阔的发挥空间。
一九八五年,在担任了六年的小提琴演奏员之后,李亚威开始了她人生的第一次“华丽转身”。她“跳槽”到长影的《电影晚报》,转行当了一名记者,开启了她的文字生涯。在此期间,她除了写下了大量的报道、纪实文学及诗歌外,还迷上了电影文学创作。
李亚威还清楚地记得当年去《电影晚报》考试的情景:
主编曹积三对她说:你写的小诗还可以,再写个本报讯吧!
李亚威问:啥叫本报讯?
曹积三:限你三天吧,写不出可别怪我了!
“我不吃不喝,我干妈张眉(长影乐团的女指挥)给我找出了一大摞有本报讯的报纸,我看了一天,写了两篇。曹主编看了就问:是你写的吗?我说:是的!就这样,我进到了《电影晚报》,从小提琴手变成一名记者,从拿小提琴弓变成了拿一支笔。从此彻底改行了!”
因为优异的工作业绩和出色的工作能力,李亚威不久就被提拔到长影信息室当主任,接着又到了长影艺术处工作,副处长、处长,一路干了上来。
才三十多岁,就当上了处长,在旁人看来,李亚威的前途“一片光明”,特别是在“官本位”还有着很大市场的中国,行政级别,往往意味着资源、待遇和享受。可李亚威不这么想。当然,这不一定就说明李亚威有着多么高的“觉悟”,更主要的,李亚威从心里,向往着一种更自由、辽阔的人生,她不想把自己的人生,过早地困囿于 一种“定数”之中。
作为从小在音乐的熏陶中成长起来的李亚威,对于人生和自我价值的实现,有着自己的独特理解和追求。虽然说这时的李亚威对自己下一步的人生目标,也许还并不太明晰,但不可否认的是,李亚威是一个怀揣着梦想的人,为了实现她的“梦”,李亚威一直在“时刻准备着”。
一九八七年,在北京
一九八九年在长春电影制片厂任艺术处处长的时候
作为李亚威的长辈,上海音乐学院作曲指挥系教授,曾在长春电影制片厂任常任指挥、副团长的张眉,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起第一次见到李亚威时的情景,是这样描述的:
“我认识李亚威的时候,她还是一个从沈阳音乐学院毕业不久,刚到长影乐团的小提琴演奏员。我第一次迈进她小小的寝室和琴房,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靠墙书柜中那一排排古今中外的名著,而她正在熟读德莱赛的作品。顿时,我对这个稚气未脱的拉小提琴的小姑娘刮目相看。当她已不满足小提琴弓子所表达的激情,急切地想喷出自己心中的火焰,决定放下琴弓,拿起笔杆,奔向一条前途未卜的、陌生的文学道路时,人人都惊叹了,为她捏一把汗,可是我知道,在她的胸膛里早就深深地埋着一颗种子,那就是文学和电影,这是她与生俱来、不可阻挡的一种情愫。”
张眉所说的李亚威生命中的那种“情愫”,也许更早的时候已经在她的生命中悄然衍生了。李亚威在她的一篇题为《记忆〈金蔷薇〉》的散文中写道:
“我从小跟父亲练小提琴,他为我抄谱,我就练;他不抄,我就背。在那美丽的童年时光,除了完成学校的作业,父亲要求我要用‘铁杵磨成针’的毅力练琴,读书对我成了一种奢侈。但我喜欢读书,为了不让父亲发觉,便偷偷地用小手电筒躲在被子里看我能接触到的书,每每读到好书,会涌动出一种说不出的快感……到长影乐团时,十几岁的我疯狂地阅读着德莱塞的《金融家》《史多葛》《珍妮姑娘》等作品,读书的时间甚至超过练琴的时间。”
七十年代的李亚威一家合影(中间是姐姐,右侧是弟弟)
或许正是张眉所描述的这样一种对文学和电影炽热的“情愫”,一把小小的提琴,一个人人艳羡的行政职务,已经难以容纳得下李亚威辽远高阔的人生梦想。当她还在长影当艺术处处长的时候,她就在工作之余,尝试着进行电影文学剧本的创作。
半路出家的她,这种“创作”于她是艰涩而磕绊的。多年的音乐生涯,只对五线谱熟知并能由此触发灵感的她,生平创作的第一个电影文学剧本,竟然是在五线谱上写就的。当她陆续在五线谱上创作出了《你不懂我的心》《独尊上海滩》等剧本之后,她创作的一部名为《喋血金兰》的剧本,被当时新疆天山电影制片厂看中,并被拍成了电影,旋即受到业内人士的好评,并一举夺得了当年山东国际电影节的荣誉奖。这让从小就有着高远的艺术追求的李亚威,对实现她的“电影梦”有了更多的想象和具体的追求。
一九九○年在长春电影制片厂时任艺术处处长的李亚威与时任厂长的闫敏军、张艺谋、郑洞天、金韬、刘建中等人合影
对于拍电影,李亚威还在长影工作的时候,就曾萌生过朦胧的好奇和冲动,但她早年的这段“追梦”的经历,李亚威甚少对外人提起。马年的正月初三,李亚威的好友赵总,请她和李怡及我去她家做客,在赵总家吃饭的时候,无意间李亚威说起了她早年的一些“往事”。
在李亚威还当着《电影晚报》记者的时候,为了学习拍电影,她曾特意申请到剧组里担任又苦又累的场记工作。为了更多地得到前辈老师们的指教,李亚威在剧组期间,甚至有意无意地跟长影的老导演苏里老先生“套近乎”。就这样,德高望重的苏导——这位曾经执导了《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平原游击队》《红孩子》《刘三姐》等,在中国当代电影史上享有重要地位的著名导演,专门给求知欲旺盛,勤勉好学的李亚威开小灶,手把手地教了她许多电影导演方面的知识和技巧。李亚威说,她日后在电影艺术上的许多造诣,都曾受益于当年苏里老先生的指教。
在长影的任职期间,李亚威还被她人生旅途上的另一个“伯乐”——高天红,有意地“推”到了导演的位置上,同时也强化了她的“电影梦”。李亚威说:“如果没有当时高天红导演的激励,我也许不会那么早进入导演的行列。”
对于这件事,高天红曾回忆道:
“于是,我通过一个机会,硬把她推上去,让她当自己剧本的导演了。李亚威除了编剧又走上了导演之路,这是她又一次上了人生奋斗的台阶。
“她的《酿酒人》《穿红马甲的女人》等一部比一部娴熟,一部比一部拍得老到。
“当导演是需要综合素质能力的,必须懂剧本、懂摄影、懂美术、懂音乐、懂表演、懂服装、懂道具……到了如今还要懂制片,懂为人,这些都是亚威具备的。”
正是有了长影时期的这段影视创作的实践和磨砺,李亚威心中早就萌发并成长着的那种“情愫”,此时已然充溢了她的身心,是到了放飞自己梦想的时候了。
当年李亚威辞去长影艺术处处长的职务,毅然南下深圳,绝非一时的心血来潮,这其中既有破釜沉舟的决绝,也有深谋远虑的愿景和实现理想的冲动。后来,当我问起她当初为什么放弃了长影那么好的事业平台南下深圳时,她是这么答复我的:
李:我刚开始来到深圳,应该说,因为是(市文联的)张俊彪主席,(对他其实)我也不熟,他要了我。为什么选择来呢,我觉得文联总是能够放松一些,使我当时很强烈的创作欲望得到释放。在一九九四年之前,我一直苦于没有时间去搞创作,那时候我正可着劲地写着《傍晚她敲开我的门》《喋血金兰》等电影剧本。那个时期我的创作欲望非常强,而且当时我不仅仅是创作剧本,还拍了三十六首MTV,为其中有一个叫《喀秋莎》的还跑到俄罗斯边境去拍。在一九九○年之前,我就已经开始做导演和编剧了,而且剧本编得还不错,像《喋血金兰》(导演孙沙)一拍出来,就获得了山东国际电影节的荣誉奖,因为当时它的收视率特别高。后来我越来越觉得应该有一个创作相对宽松环境,那种渴望,就像一颗不安分的种子要发芽一样,急需一个创作环境。
文:当初深圳文联给您安排的其实是组联处处长这样一个行政职务,这跟您搞创作会脱节,您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李:当时是这样的,因为我来的时候,并不知道组联处处长(具体)是干什么的,但是我知道有一点,任何工作也不会比在长影压力更大了,因为那个位置责任太大了。每年二十一部影片,不仅仅要拍摄,还要电影局通过。(那会儿)既要抓出作品,每天还有许多的行政工作,压得你喘不气来。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无法跟长影的工作比,所以不管是干什么,只要能离开,我当时一听说文联,(就想)文联的任何一个部门,都不会有长影那样大的压力和工作强度,所以没有什么想法就来了。
一九九○年,拍摄音乐电视《喀秋莎》与俄罗斯演员在一起给演员李艳秋说戏给演员陈瑾说戏
文:当时你也是揣着一个梦想来的。是什么样的梦想?
李:我当时来的时候,觉得到这个地方会轻松,我到这里会把自己的一系列的故事,或者在长影不能完成的那些创作任务,一股脑(地)在这片土地上写出来。
文:您当时所想到的“创作”,只是针对文字而言,还是有一种电影影视的创作概念呢?
李:我当时到深圳来,就是因为对影视感兴趣,因为(之前)我已经很成功地把《喋血金兰》搬上荧屏。到这之后,我一直追求的理想状态,就是希望有一个空间,能够承载我自己思想里面奔驰的东西,然后把这些剧本、小说弄出来。(最初)我对小说和剧本感兴趣,但是后来由于我写好了这个东西,必须有人去执行,(我就)去拍了,后来我成了导演。在长影的时候,我已经是导演了,但(在这儿)没有人会理解你,编剧、导演、制片人,甚至作词、作曲都(得)一个人兼。
一九九七年在拍摄《深圳故事》之一《妈妈飘着长头发》的现场(右一为美术师张坚)
《深圳故事》之四《眼睛》剧照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深圳,是一个英雄不问出处的地方,无论你是谁,也不管你之前有过多么显赫的“过去”,你都必须在这块“新大陆”上再次证明你自己的能力与实力。虽然对自己再次创业的困难的预估并不太充分,但李亚威还是很快放下身段,把自己作为一个闯特区的普通创业者,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从头做起。
写剧本,拍广告,拉赞助,搭班子。编剧、导演、美工、制片、发行,一个人“一条龙”式的动作方式,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筚路蓝缕,奋力前行。
“那时候,搭一个班底,要从长影、上影、珠影、潇影、北影、广影等几个电影厂里选出来,在深圳连一个推移动道的专业人员都找不到。” 李亚威说。
著名演员奚美娟曾这样描述此时的李亚威:
“很多人来到深圳,是追求和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有的人成功了,就站稳脚跟,有的人失败了,就匆匆而过。而亚威在追求改变生活的同时,却一直执着地追求着她的文化理想状态,她的作品,无论是拍出来的和即将拍摄的,构思都很巧妙,从一个
一九九九年在拍摄《深圳故事》之三《升》的现场(右一为著名演员奚美娟)
一九九九年在拍摄《深圳故事》之三《升》剧照
角度深入进去,紧紧地抓住人物的命运和现实状态的悲欢离合,有些怀有深刻思想主题的人物故事,分明表达了亚威要呼唤和张扬的一种深圳人的精神。”
经历了一番胼手胝足、卧薪尝胆的苦斗之后,李亚威在事业上终于完成了她由蛹化蝶的蜕变,由她创作并执导的系列电视电影《深圳故事》及其他一些影视作品、节目,让李亚威在深圳和全国的影视圈内声名鹊起,《深圳故事》甚至成了深圳的一张为人熟知的文化名片。奚美娟说她《深圳故事》系列的诞生,领先了中国电影的“状态性表演现象”。
从“一条龙”式的制作方式摸爬滚打锻炼出来的李亚威,既长了本事,又有了信心,也许她认为,经历过这么一种“十项全能”式的训练,影视圈内的“活儿”,再也没有什么能难得住她的了。这时的李亚威,有点像《红灯记》中即将赴宴斗鸠山前的李玉和,认为有了李奶奶的那“一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她全能对付,但拍摄《火之舞》的困难还是大大超出了她的预计。
二○○五年在拍摄《深圳故事》之六《你的钱匣子给了谁》的现场(右一为摄影指导于长江)
在拍摄《深圳故事》之六《你的钱匣子给了谁》的片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