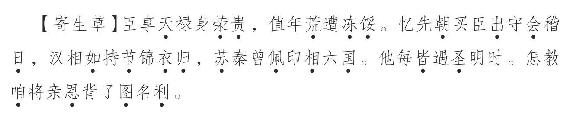嘉靖写本《琵琶记》校录后记
一
徐渭《南词叙录》中著录有宋代南戏《赵贞女蔡二郎》戏文一种,演出的是“伯喈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的故事,并说这个戏是出于“俚俗妄作”的,然而它却是“戏文之首”的代表作品。可惜的是,这本早期南戏的剧本,却没有片言只语保存下来。到了元代末年的时候,浙江东嘉人高则诚依据《赵贞女蔡二郎》这本“俚俗妄作”的早期南戏,进行了新的创作。他深深惋惜“伯喈之被谤”,要为东汉时期著名的文学家蔡伯喈重新塑造一种应该歌颂的艺术形象,他“用清丽之词,一洗作者之陋,于是村坊小伎,进与古法部相参”而成功地编著了《蔡伯喈琵琶记》。高则诚编著的这本《琵琶记》剧本,比较完整地传留下来了,被称为中国戏曲史上元末明初南戏复兴时期的“五大传奇”之一,明清两代直到今天的戏曲舞台上,都是不断地在演出这个剧目,可以称得上是一部不朽的名著。高则诚的《蔡伯喈琵琶记》,后人大多简称为《琵琶记》,或者叫作《蔡伯喈》。1958年从广东省揭阳县渔湖公社西寨村古墓中出土的嘉靖写本《琵琶记》,也是沿习古代南戏以剧中主角的名字为剧名的体例,题名为《蔡伯喈》。
广东揭阳古墓出土的写本《琵琶记》中,有一页正文的上端侧旁书写“嘉靖”二字,它表明是明代嘉靖年间的写本。嘉靖是明世宗朱厚熜的年号,共四十五年,相当于公元1522年至1566年。嘉靖写本《琵琶记》是迄今所保存下来的时代最早的一种戏曲艺人舞台演出本。它是潮州一带地方明代戏曲艺人十分爱护珍视的纪念品,它记载着他们的艺术活动,并且以此作为他们的陪葬物。这是一本罕见的明代戏曲舞台演出实况的历史见证!所以,它是一件珍贵的戏曲文物。由于古代留传下来的戏曲剧本,大多数是木刻印刷的版本,像这样的明代戏曲写本的实物是非常罕见的。虽然它在出土时已经残破了,但是,它却记录了不少当时演出这个戏的重要资料,对于研究戏曲史、文学史以及有关《琵琶记》的版本、文学、唱腔、表演各方面的发展演变,提供了大量的证据,所以它又是一件研究戏曲发展史的珍贵文献。
二
明清以来流传的《琵琶记》剧本是很多的。清代陆贻典曾经说过:“刻者无虑千百家”,但是版本却是多种多样的,“几于一本一稿”。清代的版本不去说它,单就明代的版本来说,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下列数种:
《新刊元本蔡伯喈琵琶记》二卷 清陆贻典钞校本
《新刊巾箱蔡伯喈琵琶记》二卷 明嘉靖苏州坊刻本
《李卓吾先生批评琵琶记》二卷 明虎林容与堂刻本
《新刻重订出象附释标注琵琶记》四卷 明金陵唐晟《绣刻演剧》本
《蔡中郎忠孝传》四卷 明刻本
《陈继儒评鼎镌琵琶记》二卷 明书林萧腾鸿刻《六合同春》本
《琵琶记》三卷 明黄氏尊生馆刻本
《琵琶记》四卷 明吴兴凌氏刻朱墨本
《元本出相南琵琶记》三卷 明刻本
《琵琶记》二卷 明毛氏汲古阁刻《六十种曲》本
《新刻魏仲雪批点琵琶记》二卷 明清间刻本
以上十一种版本,根据钱箕先生认定:“第一、二两种,都还保持着元人的真面目,……李卓吾评本以下九种,都经明人修改过。”钱先生以陆钞元本为底本,参照其他本,校注了《琵琶记》,于196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根据上述的这条线索,我也是采用陆贻典钞校的《新刊元本蔡伯喈琵琶记》(《古本戏曲丛刊》初集影印本,以下简称陆抄本)作为主要参考本,对嘉靖写本《琵琶记》进行整理校录工作的。我在整理校录这本残缺不全的明代写本的过程中,逐渐明确和发现这本嘉靖写本,作为版本来说,它与陆抄本基本一致,是同属“元本”范畴的一种珍本。因此,我认为这本嘉靖写本应是继陆抄“元本”和巾箱本之后的最新发现的第三种元本《琵琶记》,是值得学术界重视的一种珍本。为此,我拟定它的名称为嘉靖写本《琵琶记》。
嘉靖写本《琵琶记》在1958年出土时共有五本,页数不明。其中三本,出土后毁损无遗。广东省博物馆收藏保存至今的仅是其中的两个残本,经过裱褙以后,现在共计九十五页,每页两面,共计一百八十面。原写本页心高宽各约22.5公分,每面直书8行,每行书写15字左右不等,曲文字句旁多有艺人演唱时的点板符号。由于原本页面有的残破过甚,裱褙又有错页现象,这就需要首先着手进行整理复原的工作,我是采用与陆抄本对校的办法,逐字逐句地进行校录、补阙,最后整理成现在的样子。整理出来的结果是:
甲,嘉靖写本《琵琶记》总本上卷一本。原写本共五十四页,订为二十出,计有:
第一出 开场(缺) 第二出 祝寿
第三出 逼试 第四出 送别
第五出 训女 第六出 赶路
第七出 忆夫 第八出 考试
第九出 游街 第十出 吵闹
第十一出 招婿 第十二出 拒婚
第十三出 相怒 第十四出 辞朝
第十五出 请粮 第十六出 抢粮
第十七出 允婚 第十八出 结亲
第十九出 埋冤 第二十出 吃糠
乙,嘉靖写本《琵琶记》生本一本。原写本共三十八页,订为四十二出,计有:
第一出 开场(缺) 第二出 祝寿
第三出 逼试(缺) 第四出 送别
第五出 训女(缺) 第六出 赶路
第七出 忆夫(缺) 第八出 考试(缺)
第九出 游街 第十出 吵闹(缺)
第十一出 招婿(缺) 第十二出 拒婚
第十三出 相怒(缺) 第十四出 辞朝
第十五出 请粮(缺) 第十六出 抢粮(缺)
第十七出 允婚 第十八出 结亲
第十九出 埋冤(缺) 第二十出 吃糠(缺)
第二十一出 琴诉 第二十二出 侍病(缺)
第二十三出 思家(缺) 第二十四出 卖发(缺)
第二十五出 家书 第二十六出 葬亲(缺)
第二十七出 赏月(缺) 第二十八出 上路(缺)
第二十九出 盘夫 第三十出 谏父
第三十一出 行路(缺) 第三十二出 接眷
第三十三出 佛会 第三十四出 入府(缺)
第三十五出 题诗(缺) 第三十六出 相会
第三十七出 遇使(缺) 第三十八出 回乡
第三十九出 李旺(缺) 第四十出 庐墓
第四十一出 宣旨(缺) 第四十二出 旌表
丙,嘉靖写本《琵琶记》残片三页,计有残文五段。
宋元南戏剧本例不分折分出,亦不标目,如《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本,如陆钞本均依旧制,每折之末书写“并下”或“下”字表示而已。明人刻本多加出数和标目。嘉靖写本通篇亦遵宋元旧例,不作出数,亦不标目,仅在第四出的写本上发现有“第四出”三字。据均此,我在整理和校录这本残缺的写本的时候,为了检阅方便,加以出数以明段落,同时拟定两字的标目表示剧情的内容。既然这次校录工作是属于古籍整理的范畴,除了加添标点符号,以示句读语气和曲律规格以及字句不同之外,凡是写本中的原有错别字和异体字,一律照样录写,只作必要的校注,附于每出正文之后。
三
嘉靖写本《琵琶记》出土共五本,被毁损了三本,现存的两个残本共九十五页。经过校录整理发现计有总本一本,是上卷部分二十出;生本一本,是生脚单头演出本的全本,另外尚存残片三页。据此,可以看出其余毁损的三本,当是总本下卷一本,以及可能是旦脚单头演出本一本和末脚单头演出本一本。
清代陆贻典曾经对《琵琶记》作过一番校录工作,他的手书校录本,是根据钱遵王收藏的一本抄本和一本嘉靖戊申(1548)苏州重刻本进行校录的,他在校后记中说过,他这一本校录本是“信未经后人改窜者也”的“元本”。这是迄今学者们所公认的比较接近高则诚原著的一种本子,已经影印出版,编入《古本戏曲丛刊》初集,题名《元本蔡伯喈琵琶记》。然而,它毕竟是经过明代人修订过的本子,它的订正者,就是署名为“南溪斯干轩”的人。这种本子与戏曲演员们在舞台上实际演出的情况,当然存在着一定的距离。艺人们演出的《琵琶记》究竟又如何呢?在现存的各种地方戏中,那是多得很的,然而,迄今我们能见到的最早的艺人演出本,看来要算广东揭阳出土的明嘉靖年间无名氏艺人的写本了。
嘉靖写本既是明代艺人演出本,又是残破不全的写本。因此,有必要采用比较接近原著的陆抄“元本”来与这本写残本进行对校了。由于写本残缺剥落,进行补残看来是非常必要的。如何补法呢?严格限制在补残呢,还是要补全呢?看来只能进行补残而不能补全。因为补全,就必然成为另外一种新的版本了。那样做又还需要集中其他各种版本来进行汇校,而不是现在我采取的对校的办法了。汇校本也是需要的,但那是以后的事了。所以我决定用一种“打补丁”的办法来进行修补复原,比如曲文有残缺的字句,用陆抄本予以订补。在说白方面,因为演出实践有所取舍变更,特别是中国剧曲传统中具有的净丑脚色打诨的特点,在演出时不一定严格遵守剧本的限制,演出时是允许有所增减和变更的。所以,我所做的工作只是在非补不可的地方予以订补和校录,其他一般不加订补。特别是生脚演出本,既是生脚单头,则不将别的脚色的唱白予以增补,用以保存原貌,但在个别重要的地方,亦作了少量的补订和必要的校录工作。
四
嘉靖写本《琵琶记》虽然是明代人书写的艺人演出本,而且现存的又是残本,但是在这个本子中,却保存了“元本”许多重要的特色。如果说陆抄“元本”是“信未经后人改窜者也”的话,那么,这本嘉靖写本就是一部接近“元本”的写本。对于《琵琶记》的研究,它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中国的戏曲艺术在形式体例上的最显著的特色,是唱、念、做、打多种表现手段的综合。从戏曲艺术发展的历史情况来说,这种艺术表现手段的综合,在宋代的杂剧艺术中已经形成。但是在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和各个地区,侧重点又不是完全相同的。金、元时期的北方杂剧艺术,相对来说更偏重曲调曲词的演唱,对于念白即说白,往往作为唱词的补充手段;属于做(作)和打的插科和打诨这些艺术手段,更是处于可多可少的陪衬地位。现存的《元刊杂剧三十种》,是说明这种情况的最好的历史证据。宋、元时期的南戏艺术,更多地偏重于唱、念艺术手段的结合。同时在继承宋杂剧的插科打诨的艺术手段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是还处于戏曲艺术的陪衬地位,这点与金、元杂剧艺术是相同的。因此,宋、元时期的南戏艺术,更多地保留了唐宋以来普遍发达的民间说唱艺术的特色。我们从现存的《永乐大典戏文三种》的剧本和其他早期南戏剧本来看,都是如此地显示着说唱艺术所具有的浓厚的说、唱并重的特色。陆抄“元本”《琵琶记》具备了这种情形,嘉靖写本《琵琶记》也同样具备了这种特色。宋元南戏剧本不单单注意词调、曲调的唱文的安排和写作的讲究,而且十分着重说白韵文化的写作,它的说白部分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十分讲究的。比如开场戏,往往用一首或二首词调组成,由副末来介绍剧情大意和主要人物,但是它们是说白而不是唱词。如《永乐大典戏文三种》的《小孙屠》是用两阕【满庭芳】的词来进行说白的;《张协状元》是用词调【水调歌头】来进行说白的;《宦门子弟错立身》是用词调【鹧鸪天】来进行说白的。《琵琶记》也是用两首词调【水调歌头】、【沁园春】来进行说白的。在嘉靖写本《琵琶记》中同样如此遵循这种体例的。如第六出【浣溪纱】词:“生白:千里莺啼绿映红。末白:水村山郭酒旗风。丑白:行人如在画图中。合白:不暖不寒天气好,或来或往旅人逢,此时谁不叹西东。”又如第九出末上白:“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这首五言诗。其他不用韵文的说白,也是十分讲究的,如第九出中末和丑脚的那段很长的说白。在嘉靖写本中,不管是韵文和非韵文的说白,都体现了宋元时期南戏艺术保存的说唱并重的民间说唱艺术的特点。
其次,嘉靖写本《琵琶记》,它在剧本形式上完全与《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及陆抄“元本”相同,保存了古本戏文不分出数,从头到尾,连缀一贯的方式。尽管其中有“第四出”的标示,那是仅有的一处例外,全本体例仍是沿习古本戏文的。
重要的是嘉靖写本《琵琶记》的曲文与《九宫正始》所引“元谱”和陆抄“元本”相同。但在一些重要的字句和名目上有所订正,更显得“原始”,更有接近高则诚原本的迹象。在曲牌名称上,往往用宋代词牌的原名,而不用明代的曲牌名称。比如“宝鼎现”这个词牌,调见宋康与之《顺庵乐府》,在《康熙词谱》三十八及万氏《词律》二十中均载此词。嘉靖写本第二出亦作“宝鼎现”,而陆抄“元本”与《九宫正始》引“元谱”均作“宝鼎儿”。按:“宝鼎现”又名“三段子”和“宝鼎儿”,但宋元词中,均以“宝鼎现”为正名。又如:【谒金门】这支曲牌,在《九宫正始》引“元谱”及陆抄“元本”中均作【谒金门】,而在嘉靖写本中却作【谒春门慢】。按【谒金门】为唐代教坊曲名,调见《花间集》,又名“不怕醉”、【醉花春】、【东风吹酒面】、【垂杨碧】、【春早湖山】、【杨花落】等,皆以咏唱春天风光为名的,可见“谒春门”的“春”字是自有根据的。王骥德《曲律》将“谒金门”与【瑞鹤仙】、【宝鼎现】等曲,同列入双调,并且说明这些曲调“俱系慢词”。据此,“谒金门”可以订正为【谒金门慢】,而陆抄“元本”等俱作“谒金门”,作为南戏而用的南词来说,是应该加一“慢”字的。但是在嘉靖写本中,却是沿习宋人词调的规格,而注明这一“慢”字。在嘉靖写本,注明有“慢”字的地方是很多的,如【瑞鹤仙】、【五供养】、【高阳台】等曲,皆是如此。去掉“慢”字的做法,当是明代以曲代词的情况,说明宋代南词逐渐演变为南曲的痕迹。又如陆抄“元本”题作“甘州歌”,在嘉靖写本中则依据宋代词调全名作“八声甘州歌”。又如第十一出中有【锁寒窗】一曲,亦为词牌名,即【琐窗寒】,见《康熙词谱》二十七,而陆抄“元本”则作【琐窗郎】,据明蒋孝《南九宫谱》称:“琐窗郎”乃是【锁窗寒头】、【阮郎归尾】两曲的合名。按宋人词调当无此合曲,“琐窗郎”一曲乃由词的演变所致。还有一些词牌字句的限制,在嘉靖写本中体现得更为准确无误,如陆抄“元本”第十二出中有一段生脚说白,题名称作“木兰花”,而嘉靖写本是题作“四七句”。考“木兰花”乃唐教坊曲名,《康熙词谱》云:“木兰花”有两调,一名“木兰花”,一名“玉楼春”,其七字八句者,为“玉楼春”;七字四句者当为“木兰花”。故“木兰花”的词调限制,严格说来称为“四七句”是稳妥无误的。由此可见,嘉靖写本比之于陆抄“元本”,当更为准确可靠。
五
陆贻典说过,他抄校的元本《琵琶记》,是“信未经后人改窜者也”。现在嘉靖写本出土,两书对校后发现陆抄“元本”有许多地方是经后人“改窜”了的,除了上述的一些例证外,从文字的正误方面来看,嘉靖写本比陆抄“元本”更接近原著些,更优越些,也更准确些。同时,由于嘉靖写本的发现,也就可以校正陆抄“元本”的错误了。
嘉靖写本第三出【一剪梅】曲文是:“浪暖桃香欲化鱼,期逼春闱,诏赴春闱。郡中空有辟贤书,心恋亲帏,难舍亲帏。”其中的“春闱”二字是封建社会中科举制度的考场的代称,“亲帏”是亲人的代称,曲文中用此两词,意在对仗,是很工整并有所区别的。试想高则诚这位大文学家,是非常注重遣词的准确,绝不会将“春闱”与“亲帏”均误作“亲闱”的。但是陆抄“元本”以及明代的其他本子均将“春闱”误作“亲闱”了。蒋孝的《南九宫谱》以及王世贞《曲藻》中所称的一种“善本”,均不免有些错误。固然,“闱”与“帏”词意可通假,但却看出嘉靖写本的讲究和准确,在接近高则诚原著的程度上,比起其他本子,它的优越性是很明显的。
又如第二出下场诗,蔡公道白:“急办行装赴试期”,蔡伯喈接白:“父亲严命怎生违”。而陆抄“元本”却将“试期”的“期”,擅改为“闱”字,既不合蔡公语气,又与下句“怎生违”的“违”字音重,为绝句体例所忌。何况,陆抄“元本”原来的正文也是写着“期”字的,却又在旁边另改为“闱”字,明显看出这是陆贻典在抄校时有意地错改原文。
在第四出“玉交枝”曲文中蔡母有一句唱词“你蟾宫桂枝须早攀”,这“攀”是很准确的字,而在陆抄“元本”中,却又明显地误作“板”字。同一出中的【鹧鸪天】曲文中有合唱一句“桑榆暮景应难保”,而陆抄“元本”却作“亲闱暮景应难保”,把“桑榆暮景”这个古文中的成语改成“亲闱暮景”,这种缺乏意境的文字,实在别扭。陆抄“元本”中这类错误比比皆是。紧接上曲之前腔,旦唱“正似马行十步九回头,归家又恐伤亲意,搁泪汪汪不敢流。”在这三句曲文中,陆抄“元本”就有三处明显的错误:“似”字误作“是”,“又”字误作“只”字,“搁”字误作“阁”、“各”字。“似”字,像也,而误为肯定词,乃音讹而意错。“又”字,再也,而被误作“只”字,乃犯形误之错。“搁”字,停也,止住也,陆抄本作“阁”字,正文旁又书一“各”字,去掉偏旁成为“阁”字,乃别字,又改为“各”字,音同而其意更不通了。
又如:第十出旦唱“奴自有些钗梳,典当充粮米”,陆抄“元本”误作“奴自有些金珠,解当充粮米”,当以嘉靖写本“钗梳”为是。按常理推论,赵五娘既有“金珠”,那能吃糠饿饭,何至于此。同出蔡公唱:“我每不久须倾世,叹当初是我不是”,而陆抄“元本”误作“我每不久须倾弃”。“倾世”,谢世、去世的意思,陆抄本作“弃”,乃音误。
嘉靖写本第十二出【高阳台】曲文首句“梦绕亲帏”四字,陆抄“元本”作“梦远亲闱”,“远”、“闱”两字,均以形误。【高阳台】前腔有“阀阅,紫阁名公”句,陆抄本将“阀”字误作“华”字,音形均误。
第十三出有堂侯官和媒婆的唱词:“乔才堪笑,故阻佯推他也不肯从。岂无佳婿可乘龙!”而陆抄“元本”却误作“岂是我无佳婿得乘龙”,无故加添了“是我”两字,本来是末、净的唱词,并非外扮的牛丞相的唱词,怎么能用“我”字呢?显系误书加添之错。
以上所举的例证,已经可以看出嘉靖写本在文字和词句方面,从接近高则诚原著的角度来说,比陆抄“元本”,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像这类情形,在陆抄“元本”不下数百条的错误,可以根据嘉靖写本予以订正的。当然,嘉靖写本也有许多错别字,就不一一列举了。我作的《嘉靖写本琵琶记校录》一书,一一都作了详细的校勘可以检阅。
六
嘉靖写本《琵琶记》不仅是一部难得见到的接近原著的珍本,而且是一部更难见到的明代戏曲艺人的舞台演出本。除了其中生脚单头演出本的完整形式,已经充分证明这是一本地地道道的舞台演出本之外,它的剧本书写方式,也足以证明它是艺人的舞台演出本。保存在福建的南戏“七子班”,现在叫梨园戏、莆仙戏,以及广东的正字戏的艺人演出本与嘉靖写本的抄写方式和版样形状,都是完全相同的;单单莆仙戏的传统艺人演出本,与嘉靖写本样式相同的,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收集的就有八千本之多,这是非常有力的佐证。同时,从嘉靖写本本身的情形来说,还有下面叙述的几种表现:
1.关于剧本分出的问题。元代杂剧艺术的剧本是分折的,通常是四折一楔子,这是元代的民间通俗刻本《元刊杂剧三十种》中很明显的事实。这部《元刊杂剧三十种》,也是一部元代戏曲的舞台演出本。宋元时期的南戏,因为现在还未发现有宋元时期的刻本,它的剧本究竟分不分出,迄今没有定论。有一种说法是宋元南戏剧本概不分出,有《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和陆抄“元本”为证,分出形式的剧本是明代传奇开始才有的。我以为这种说法也有一定的根据,但是这种说法没有解释为什么宋元南戏不分出的原因。原因何在呢?就是没有将剧作家写的剧本与艺人舞台演出本加以分别来认识的结果。从嘉靖写本的发现,我认为宋元时期的南戏剧作者在编写剧本时是不分出数的,书写剧本的形式是连缀而下的,分出或者分折这种形式,是艺人在舞台演出时,为了角色人物上下场的舞台实践的需要而加以创造设计出来的办法。以后随着戏曲艺术的发展,在明代初期,从事戏曲创作的剧作家们为了结合舞台演出的实际,觉得这种分出的办法,对剧本创作有一定的规范作用,为了使剧本精练,避免早期南戏写作的结构松散冗长,也就普遍采用了分出的明确的形式,作为剧本体裁和规格的限制而固定了下来。明代嘉靖写本《琵琶记》通篇也是不分出数的,以“并下”或“下”来表示角色人物的上下场,这是与《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和陆抄“元本”是一致的,还保留了宋元南戏剧作者留传下来的旧习。但是,由于它毕竟是艺人们用在舞台演出的写本,艺人们就给这种写本加上出数,表示剧情变化,所以有“第四出”的字迹,明确地表示了舞台演出分出这种实际上沿用已久的习惯方式,这也是嘉靖写本《琵琶记》作为艺人演出本在剧本形式上的表现。
2.关于唱词念白的增减。戏曲艺术的案头文学剧本,在舞台的演出活动中,经常由于演员的艺术表现的需要,在唱词和念白上是要进行一些增加和删减的。嘉靖写本《琵琶记》在这方面的表现,也是很明显的,而且进一步予以新的创造。在“辞朝”一出中,嘉靖写本有比较大的改动。陆抄“元本”在这一出有大曲一套,是【入破第一】、【破第二】、【袞第三】、【歇拍】、【中袞第四】、【出破】、【煞尾】,共七支曲文。在嘉靖写本中,这有名的【入破】却被改动为【折桂令】、【滴溜子】、【寄生草】三支曲调来演唱,在原有曲文的基础上保留了原意,但是曲调上和文字上却进行替换和删节,适应场上的需要,使剧情更加紧凑。这是演出本对原有曲牌与曲文的改动的一种表现。另一种表现是对一支曲文保留一部分,删减一部分,如第三出【宜春令】前腔蔡公唱的曲文是“时光短,雪鬓垂,守清贫不图着甚的”。紧接着就是生脚的说白了。而在陆抄“元本”中,此曲还有几句这样的唱词:“有儿聪慧,但得他为官足矣。天子诏招取贤良,秀才每都求着科试。快赴春闱,急急整着行李。”这些都因演出需要被嘉靖写本进行了删减。在念白方面的增减和改动,在嘉靖写本中是很多的,如在“逼试”一出,蔡公蔡婆的大段对白,多有删节;生脚和末脚的插白不仅有增减,而且有变动。在某些唱词中,增加一些衬字,如“我”、“你”字,那是很普遍的。
3.关于唱腔点板的符号。这是演出本最明显的表现,比如嘉靖写本“生本”中【寄生草】曲文之旁所注明的符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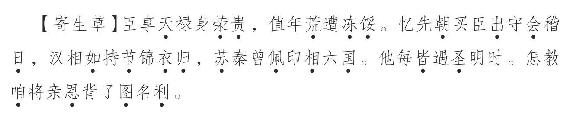
用“·”的符号,表示演唱时板眼和节奏;用“·”的符号在“会”字和“相”字的右上角,表示这些字特别读音和语气。有的曲文之旁,还用“—”的符号。
七
嘉靖写本《琵琶记》涉及有关剧本思想内容,有些问题也是值得探索的。最明显的是写本中缺了几出重要的戏的问题。其他各种版本中均有第一出副末开场的戏,写本中根本就没有发现有“副末”这个脚色,也没有“水调歌头”和“沁园春”这两阕至关重要的曲文。这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因为嘉靖写本是残本,这两阕词调又是首页的内容,脱落损毁的可能性很大;另外一种情况,可能原来剧本就不存在这一出戏。陆贻典在他写的《旧题校本琵琶记后》一文中说:“适钱子遵王出示《琵琶》一编,系嘉靖戊申刻之郡肆者,已又手一册示余,首脱一叶有奇,末脱二叶……”这段话说钱遵王交给他的那一本手书本是“首脱一叶有奇”,那不正好是第一出的开场戏吗?现在出土的嘉靖写本同样也是“首脱一叶有奇”,难道是一种巧合?过去的写本是不编页数的,是否“首脱”,或根本就没有这“一叶有奇”,也就难说了。如果根本就不存在“首脱”的问题,那就不是一个缺页的问题,而涉及剧本内容的重要问题了。因为历来的学者在评论这部作品的社会意义和思想内容的时候,大都在这场戏上做文章,“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这两句话,以及“全忠全孝蔡伯喈”这句下场诗,往往作为评论《琵琶记》的主要依据。有的明代刻本干脆把剧本标题作《忠孝蔡伯喈琵琶记》。但是,关于忠孝这个问题,很早以来就有人在议论,特别是在民间,说这个戏中的蔡伯喈,是一个典型的不忠不孝的坏家伙,是用雷火把他打死的,怎么偏偏又叫作“全忠全孝”呢?关于这些议论,争论是很大的,有人解释作者高则诚就是因为要翻那个原在民间流传的南戏“马踏赵五娘,雷劈蔡伯喈”的旧案,而创作这本“全忠全孝”的《蔡伯喈》。传说和议论都是绝对矛盾的,不管怎样说,到底存在不存在第一出开场戏?这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
其次是牛氏的问题,论者说这个人物写得概念化,写得不真实,她太懂礼教了,简直是封建礼教的化身,作者是在借这个人物进行说教。而主要根据的是剧本中有“牛氏规奴”这出戏,还有另一出“牛小姐愁配”的戏。但是,现存的嘉靖写本残本中,偏偏没有这两出戏。这部写本出土时被毁损的其余三本中,怎么推测也断断不能推测出还有一本“贴旦本”的单头演出本的。所以,嘉靖写本中是不存在这两出戏的。因之,涉及“风化体”和封建礼教的说教的评论,在这个新出土的写本中是找不到这两出戏的根据的。
另外,嘉靖写本中有两处涉及剧本内容的问题,也是值得探索的问题。在第九出状元骑马游街的戏中,嘉靖写本是没有丑脚坠马的情节的,与此情节有关的曲子和念白,看来是被删去了。如果是删节的话,则这个问题涉及演出本的问题,因演出实际情况而被删除,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不是删节的话,那就是剧本根本不存在这段戏的问题。这里因为有与坠马关系密切的一支北曲,这支北曲叫【北叨叨令】,是丑脚唱的。看来,如果是北曲的缘故,则这个写本乃是有意识地尽可能用南词,也尽可能地避免用北曲。在十一出和十二出中,出现了陆抄“元本”所没有的情节,就是牛相派媒婆去说亲,有送丝鞭和接丝鞭的情节。关于丝鞭作为提亲和允婚的凭证,这是元人的习俗。在明世德堂刊本《重订拜月亭记》中是有与这一情节相类似的一出戏的,叫作“官媒送鞭”。嘉靖写本中关于接丝鞭的戏是有白有唱,密切配合的。嘉靖写本这段戏,录写在下面,以供研究:的曲文的。据此,可以订正陆抄“元本”许多脱落的字句。
【高阳台】(生唱)宦海沉身,京尘迷目,名缰利锁难脱。目断家乡,空劳魂梦飞越。(净白)请状元接了丝鞭。(生唱)闲聒,闲藤野蔓休缠也,俺自有正兔丝和那亲瓜葛。(净白)状元,你休推辞,请接了丝鞭。(生唱)是谁人,无端调引,谩劳饶舌。
这首曲子的唱词,陆抄本也是有的,就是没有这些说白。显然是陆抄“元本”的脱误所致。应该说,嘉靖写本有接丝鞭的情节,是合乎原来剧本所交代的剧情的。不仅如此,继【高阳台】曲文之后,陆抄“元本”只有曲文而脱缺许多必要的插白。然而,没有这些必要的曲文中的插白,是很难读懂陆抄“元本”这出戏
综合以上所述,足以说明嘉靖写本的出土,的确是难得的一部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的珍本,也是一部难得的明代戏曲舞台的演出本。
(原载《戏曲研究》198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