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革命之城:投石党运动
1643年,路易十四登基。这位年仅四岁的太阳王从前两任波旁君王中继承的,是一座在近半个世纪的和平时期实现各方面转型的都城。巴黎的第一座现代大桥,第一座现代广场,均改变了巴黎人和城市的关系;而塞纳河上熠熠发光的魅力之岛也几近完工。
到了1648年,城市的建设戛然而止。血腥与杀戮曾频频降临巴黎的街头,而最近一次,即16世纪的宗教战争。然而,在17世纪中叶,巴黎的改造却因一场别样的战争而中断。这场战争也是最早的现代革命斗争,其原因不再是宗教的冲突,而是经济和政治的问题,涉及税赋承担的问题。
约五年后,冲突结束,变革之风吹遍了巴黎的大街小巷,让巴黎人感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前奏。一些商人和工人侮辱贵族和高官们,将他们从马车中拽下来,向他们投掷物品甚至石块。城市多处已成为战场,商店关门,街上设有路障,各方势力设立检查站,民兵在公共广场巡逻,时有发生小规模的战斗。人们争论是否要“拆除巴士底狱”。路易十四的堂姐蒙庞西耶公爵夫人后来写道,巴黎人很快“对街上横躺的死尸和伤者感到麻木”。
然而,事实最终证明,这次内战更似一次再造,而非毁灭。这次内战让巴黎人更进一步参与公共事务。为了知晓事态的最新进展,制定战略,了解伤亡,巴黎人无论男女,无论何种行当,都比以往更频繁地出入于新桥。贵族们每天每时散步于街头。他们甚至首次出现在公共场所用餐,也就是最早的论政咖啡馆,位于杜乐丽花园的勒纳尔家。支持造反的贵族们在那会面,交换战况新闻。对战争时期仍留在巴黎城内的人来说,新的巴黎身份认同(确切来说,是多种身份认同,因为不同阵营的人对战争的体验各不相同)形成于这个时期。这些身份认同都和巴黎这座城市紧密相连。
在这次起义的许多关键时刻,巴黎居民面临着共同的政治使命。而巴黎平民百姓也因此形成一股不可小觑的政治势力。1649年1月,反君主制的隆格维尔公爵夫人生下一子,取名为巴黎。一位同时代人这样说道:“人们都在说,全城上下的人都将成为孩子的教父和教母。”这次战争中,随着城市扩张,一股更强的能量产生,为人们所注意。女王的一位侍女这样形容道:“巴黎更像一个自成一体的世界,而不仅仅是一座城市,这次起义很快形成一股巨大的洪流,势不可挡。”自此以后,人们也将这座城市视为政治叛乱的温床。
事态发展如此之快,那些距离事发地点非常近的人也来不及掌握。当时的人很难知道,最新的冲突发生在哪一角落,也不知道事件的焦点在哪边。巴黎人不断地移动,迅速穿过街道,冲过大桥,用更快的节奏和更新的方式感知城市的变化。
这种想迅速、时时了解事态发展的需求,形成了现代都市中心和突发性新闻的关联。报纸和大批量生产的图像媒体诞生后,内战并非第一次武装冲突。然而,冲突期间,双方都能熟谙媒体之道,积极运用各种资源制造宣传机器,这在法国战争中属于首次。在此之前,法国从未有过印刷品如此迅速产出的时期。比如,图像不再像16世纪时那样,在事件发生后让人保留战争的恐怖记忆,而是趁热打铁,影响公众舆论。
印刷商生产报纸的速度也前所未有地迅速,而他们的读者数量也前所未有地庞大。对即时新闻的渴求,以及用于满足此种需求的媒体机器,一齐将巴黎的时钟拨快了。
很快,那时的读者就能看到这次媒体爆炸式发展的重大意义,并且开始分批收集和保存在街头分发的材料。如今,许多材料仍保留完好。(教皇本人就是一位收藏者,此外就是当时遭众人唾弃的宫廷首席顾问马萨林枢机。)不仅如此,来自巴黎各行各业、代表不同政治立场的人,无论是反对国王的公主,还是大权在握的官员,或是冲突时期留在巴黎城里到处打探消息的无名小卒,都详尽记录下冲突期间的大小事件,以及这些事件对城市和居民的影响。从未有一次武力冲突在结束后能留下如此多的印刷品。内战几年里产生的册子,数量为宗教战争(1589—1593)最激烈时期的四倍。
巴黎一发生动乱,便很快波及法国其他省份。这次叛乱也产生了国际影响。冲突发生时,第二次英国内战也爆发了。在查理一世遭角逐大权的各方势力囚禁的几年里,亨利四世和玛丽·德·美第奇生在法国的女儿哈丽雅特—玛丽也来到巴黎避难。玛丽也是在到达巴黎后,才得知丈夫已在1648年12月被捕。她丈夫于1649年1月30日遭到处决,而她是在2月19日才得知处决的消息。当时的观察家并没有忽略这两场内战同时爆发的事实。前文提到的那位侍女还说道:“似乎国王都同样厄运当头。”许多欧洲人担心,这种革命的情绪会四处传播,并且带来一个革命的时代。
然而,从冲突最紧要的关头来看,这次战争还是巴黎特有的现象,原因来自巴黎城市的规模以及当时新产生的一些城市特征。每一份回忆录,以及绝大多数的宣传材料,都有显示各自在巴黎地图上的位置。这些作品的作者很少会忽略事件发生的具体地点。谈到出行时,他们很少会忽略具体的路线。他们也因此帮助人们了解巴黎的地理,创造了巴黎作为政治活动中心的形象。
这次内战属于巴黎特有现象,最典型的是内战最初的几年,当时巴黎舆论保持高度一致,而这座城市也明显成为叛乱的主要角色。
这一切,就像许多现代的政治冲突,都由税收问题引起。1648年,三十年战争浩劫进入尾声,战后的法国几近破产。皇室决定提高税收,但是遭到各方的反对。当时的收成不好,饥荒四处蔓延。法国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中,而且皇室试图对巴黎高等法院成员增收遗产税,导致巴黎高等法院决定武装起义。民怨日益加深,到了7月30日,当时的摄政女王,奥地利的安妮(Anne of Austria)前去巴黎,表示要在税收问题上让步。她的一位随从发现,队伍走在街头时,“人们并没有像往常那样,欢呼‘国王万岁’”。
1648年8月20日,在三十年战争最后一大战役的伦斯战役中,孔代亲王率领法军击败西班牙军队。8月26日的巴黎,人群唱着赞美歌庆祝这次胜利,时年九岁的路易十四亲临现场。就像往常一样,从卢浮宫到巴黎圣母院,欢庆的沿途都站有士兵。然而,国王安全抵达宫殿后,有三个营的军队在新桥或附近地带,准备逮捕皮埃尔·布鲁塞勒。布鲁塞勒是高等法院里最有威望的成员,深受巴黎市民爱戴。这次逮捕行动是受摄政女王指使,目的是公开“羞辱”高等法院。
布鲁塞勒被逮捕,点燃了巴黎这个火药桶。几乎在一夜之间,整座城市变了个模样。正如一位观察家说的,“这座人间天堂”一下子变成了一座军营。巴黎人用长长的链条以及大约1300个路障封闭了城市中心,路障取材于马车、木桶或者其他大号容器,里面是一切可能的填充物,上到碎石,下到垃圾。尽管人们慌慌忙忙地设置了路障,但官员兼高等法院顾问勒·费夫尔·德奥姆松宣称,这“比专业士兵的还要坚固”。
这幅版画(图1)是少数现存的关于这次战争的作品,图中可以看到,路障后面,圣安托万大门关闭。人们没有来得及精心制作这幅画,为的是尽快传播信息。路障后面的巴黎仍然一片祥和,固若金汤,也许事实的确如此。在这座人口约45万到50万的巴黎,大约有5万到10万人拿起了武器,反抗皇室的军队。

图1 投石党的宣传中,这支抵抗军组织有序,足以对抗皇家军队。这幅1648年创作的作品中,投石党设置路障,控制住圣安托万大门
无论这场发生在8月的冲突是否是一场革命(历史学家对此仍然争论不休),这一天都是革命性的,其影响也是革命性的。几万人所展示的威力很快便促使奥地利的安妮下令释放布鲁塞勒。当布鲁塞勒回到巴黎后,人们用传统皇家礼仪举行了欢庆活动,并且在巴黎圣母院进行了弥撒。结束以后,人们才解开链条,商店重新开业。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巴黎人仍然情绪不定。有传言说摄政女王将会采取报复行动,人们几度重新锁起链条,设置路障。然而,起初,巴黎人继续上下一心,发出一致的声音,如此齐心一致,以至于当时的人总是简单地用“这城市”或者“巴黎”指代反抗皇室的势力。勒·费夫尔·德奥姆松对“起义中市民能够一直维持的秩序感到惊讶”,他感叹“虽然没有预先选定的领袖或者执行官,每一个人却怀着同样的目标”。事实上,唯一出现的“组织和秩序”问题来自圣路易岛,这个当时建成不久的地区尚未完全融入巴黎。
尽管民众诉求在变化,有一底线条件十分明确,马萨林(Jules Mazalin)枢机必须下台。这位宰相出生于意大利,民间广泛流传此人涉嫌金融腐败。巴黎医生居伊·帕坦说,“整座城市高度团结一致,反抗马萨林”。蒙庞西耶公爵夫人称,她“从未听过任何人反对国王”,却能听到街上有人高喊:“国王万岁——马萨林下台!”
民众的团结一致改变了政治格局,并且带来了真正意义上的反对派,也就是初期的公众舆论。在这样的语境下,投石党这个由反对派领袖创造的名词也被人接受。Fronde原本形容扔石头的小孩。这些反对皇室政策的人很快就创造出一个动词形式形容自己的运动,即fronder,以反抗来捍卫自己的不同意见。他们发明了un vente de Fronde(变革之风),并且形容自己是frondeurs(投石党人),为变革而斗争的人。
1649年1月6日凌晨,摄政女王终于发动了蓄谋已久的报复行动(讽刺的是,这一天恰巧也是主显节)。天未破晓,奥地利的安妮带着儿子离开巴黎,在圣日耳曼莱昂的一座皇家城堡设立了宫廷。随行的弗朗索瓦·德莫特维尔曾明确表示,反对利用巴黎人“害怕失去国王的心理”惩罚巴黎人。
然后,在国王安全地离开巴黎后,摄政女王拿出了早已准备好的手段,那就是将巴黎和外界隔绝。在1月9日,“巴黎大围城”或者“大封锁”开始了。摄政女王下令附近的村庄停止向巴黎城供应粮食,特别是面包。
她的做法反而促使巴黎人更加团结。巴黎城里,有36位亲王和贵族同巴黎高等法院签订了反对马萨林的协议。(一名皇宫的知情人说,这些人对皇室企图“谋杀”巴黎人的做法“极其厌恶”。)这些人聚集起军队防卫巴黎,并且在公共场所部署民兵,特别是皇家广场。其中一名领袖,诺瓦穆蒂公爵,带领民兵采取了更加冒进的行动:他们和敌人激战了一天,带着500辆卡车的面粉胜利归来。1月12日,他们攻陷了巴士底狱,那里的长官投降后,高等法院任命布鲁塞勒接替。由此,一位观察家指出,在“这座城市”拿起武器,解救身陷牢狱的布鲁塞勒过去仅仅四个半月,布鲁塞勒成为这个曾经囚禁他的地方的长官。
不过,这种振奋人心的时刻,在四面受围的城市实属罕见。一位挺过了这次封锁的小官吏,细致地观察了这段困难时期的两大成因。其一是粮食缺乏,其二是冬日严寒。亏得此人,今天我们能够得知,当时曾下过可怕的大雪。冰雪融化后,塞纳河水位达到了1576年以来最高值,人们撑着小船穿过玛莱区的大街小巷。到了1月23日,城里几乎买不到面包,而能买到的,价格也涨到三倍。到了2月,肉价飞涨,而鱼价则更高不可及,因此巴黎大主教允许人们在大斋节时食肉。当时,法国皇室提出悬赏,能打入巴黎并且散布“巴黎高等法院在出卖法国人”的,每天犒赏30索尔(约等于1磅肉和1磅面包的价格)。
即使贵族也看出形势艰难。赛维涅夫人现存的信件中,有一封的时间为1649年3月,信中她猜测,“巴黎人不过多久会饿死”。在摄政女王带着儿子悄悄逃离巴黎的时候,被丢下的人中有一位侍女名叫莫特维尔。莫特维尔孤家寡人,身无分文,在皇室撤离后,生活更加惨淡。她的回忆录揭示了那些和皇室关系紧密者在当时的悲惨遭遇。暴民威胁要“洗劫”这些人的家;这些人也不敢“公开露面,生怕被认出,小命难保”。一些富有的贵族则是聘请武装警卫,但这对莫特维尔来说则是遥不可及。因此,在皇室逃离巴黎几天后,莫特维尔和姐姐一起试图回到皇宫。莫特维尔曾讲述过自己如何到达圣奥雷诺大门,也就是距离她们最近的出城口。从她的描述可知,巴黎城内的这片最上流的居民区已迅速而彻底地沦为地狱。
在卢浮宫附近的圣奥雷诺路上,姐妹俩突然被一群人发现。两人跑到皇家士兵那里寻求保护,但是士兵们视而不见;这些士兵已经变节,转靠了投石党。
自那一刻起,两姐妹逃离巴黎之旅,立刻演变成在圣奥雷诺路上的飞奔逃命,一路经过巴黎城内最豪华的宅邸。姐妹们到达附近的、亲摄政女王的旺多姆公爵住所,但是那里的警卫猛地关上大门。而那时,这两姐妹发现人群“抠出铺在路面的石块,想要砸死她们”。于是她们跑得更快,到了圣洛克教堂,而暴徒们依然穷追不舍。尽管弥撒正在进行,一位妇女仍然袭击了莫特维尔,并大呼将她“乱石砸死,剁成碎片”。有位牧师救下了她们,并联系到其他藏躲起来的贵族,让贵族偷偷地将姐妹带到卢浮宫,受到流亡在此的英格兰女王的庇护。于是,她们一起整理生存的必需品,一起避难。
围城开始后,摄政女王的顾问向她保证,“等个八到十天,巴黎城里的人将弹尽粮绝,乖乖投降”。然而,巴黎城里的人决心如此强烈,以至于抵抗持续了三个月。到了3月30日,一支包含186位贵族和高等法院成员的代表团宣布,奥地利的安妮除了没有罢免她的头号心腹马萨林,已经答应了所有条件。次月,皇室终于重返巴黎。不过,他们回来看到的巴黎,早已不是离开时的巴黎了。
当评论家谈论21世纪的革命运动时,会反复强调一个词:信息流通。在1649年的围城中,许多巴黎人能够保持思想和行动的一致,靠的都是革命初期的信息流通。巴黎城内,信息能够以多种形式迅速地传播,其中一些形式属于第一次出现,在此之前,信息都从未如此广泛并且迅速地得到传播。
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当时仍然适用:人们站上演讲台(就像图2显示的,一个人站在疑似波旁国王的骑马像的底座上),向人群发表演说。不过,这幅1649年发行的版画却是用来替代传统的演说家的角色的:讲者也许一次只有一拨听众,而图像却能一次向多个地方传播。围城期间,这幅画广为流传,上面的文字写着:“投石党人鼓励巴黎人反抗马萨林枢机的暴政。”演说家手持兵器,随时准备保卫巴黎:他的手势指向河对面的卢浮宫。他的听众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许多布尔乔亚、头戴标志性头饰的官员、贵族(比如站在前面的男子,头戴有羽毛装饰的帽子,身披昂贵的斗篷)。人群后面,不少妇女也加入进来。

图2 这幅作品以卢浮宫为背景;图中,一位投石党人正在对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人发表演说
保皇党也有自己的图像宣传手段。其中一幅版画(图3)的场景很可能创作于“围城之后,国王归来”。图中,塞纳河上,百舸争流,欢乐的船夫们玩起了游戏,取悦在河岸观看他们的年幼国王。从这幅国王归来的画面中可以看到,国王正穿过新桥,身边跟随着卫队。图中的巴黎还是面目全新,毫发无损。队伍经过的是全巴黎最好的、铺着大卵石的新桥,并且向巴黎家喻户晓的卢浮宫进发。
两个阵营的版画都在城市不同角落出售,并张贴在一些重要的地点,供那些无力购买的人观看。新桥的一头有一些特别的柱子,实则为指示牌。一位显要的投石党人宣称,这些图像位置恰当,能够“唤起人们强烈的同情心”。此人就是后来的雷斯枢机。

图3 在保皇派的宣传画里,巴黎是一座未遭任何暴力侵犯的城市。图中,围城结束,年幼的路易十四骑在马上,返回巴黎,经过路面完好如新的新桥
在巴黎人看来,在人来人往的地方张贴布告,可以一夜之间“传遍巴黎各个角落”:其中一幅谴责“恶棍马萨林”的,明目张胆地贴在巴黎圣母院的门口。这幅画面用船的形象让巴黎人联想到这座城市的盾徽。上面的文字解释说,这艘船指代“拿起武器”保卫法国的首都,议会和贵族们是船的舵手。这张布告是在1649年1月8日张贴的,两天前,奥地利的安妮带着年幼的国王逃离巴黎,对巴黎的封锁也刚刚开始。这张布告似乎在鼓励巴黎人投靠船上的领袖,保卫巴黎。这张布告同时也发出信息,表明他们将会讨得圣上欢心;船的上方,飘在天上的年幼国王,身后是一位长着羽翼的角色,即“指引法兰西的神灵”。

图4 在巴黎围城时期,反对派到处张贴类似这样的布告,既提供了信息,也掀起了舆论
还有一些布告则是在天未破晓时,挨家挨户地发放,一次就是几百份。就像图像一样,这些布告也很快送达庞大的受众群体,包括一些识字不多甚至目不识丁的人。许多记录里有提到公众读报的场面:一群人挤在一幅海报面前的场景,有些人大声阅读上面的信息,然后对上面的观点进行讨论。在这幅新桥的插画(图5)里,一男子站在步行道上,向约二十名听众宣读,听众既有男性也有女性。
人们不仅到处张贴印刷品,也直接在街道上分发。这是一些被称为“纸票”的小纸片,约5英寸长,3到4英寸宽,大量印刷,趁着天未破晓就发放到大街小巷。看到的人会拾起来,小心翼翼地收好,私下里阅读。纸票里经常有耸人听闻的消息,比如可能对谁进行逮捕,或者军队马上攻入巴黎。就像今天的社交媒体,这些纸票能够短时间聚集一大批受众。

图5 关于新桥的画作通常有描绘人们大声阅读的场面。在投石党运动中,这种阅读场面能帮助不识字的人了解事态的最新进展
革命之城的巴黎成为印刷品的海洋的另一原因是,一种将政治新闻变成娱乐的形式诞生了,这种形式就是政治讽刺歌曲(vandevilles)。
这个名词是缩写形式,大意是“城里发生的事件”,它们也确实记录了事件。内战发生之前,讽刺歌曲已经出现,却从未广泛传播。内战期间,讽刺歌曲首次被定义为一类流行歌曲,用挖苦或者煽动的方式记录时下发生的事件,听者能很快记住歌词和曲调。在此期间,巴黎人,无论贫富,都迷恋上了讽刺歌曲,并在街上哼唱。在人们心中,这些歌曲一开始就和新桥联系在一起:最早的词典条目中,这些歌曲就等于“在新桥上哼唱的歌曲”。
讽刺歌曲形式也比较简单:歌手们将最新流行的曲调改编,用最近的政治事件填词。歌手创作的速度极快,不到两天就可以把事件写成歌词。因为旋律都早已为人熟知,歌的曲调也容易记下。歌曲改编后与之前的反差(比如改编前是言情歌曲,在讽刺歌曲里,变成了对腐败的口诛笔伐),令人印象深刻。其中一首流行的民谣《醒来吧,白日做梦的人》,歌词是博福尔公爵给巴黎高等法院的致辞:“法兰西的人民,听我说……”此人是一位广受拥戴的投石党人。大街小巷,随处可见“传唱员”,专门受雇去传唱最新的讽刺歌曲。比如,有一首作品由“六名女鱼贩”创作,当时的巴黎人正在城中设立路障。仅仅在围城时期,发行的政治讽刺歌曲就多如牛毛,乃至产生了专门的热门歌曲合辑。
在发布信息以及凝聚巴黎人这点上,没有哪一种印刷形式能企及一种周期性出版物,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报纸。在巴黎受围时期,城市无时无刻不产生着新闻,而法国新闻媒体也首次成为一种大众媒体。
手写和印刷的报纸均于17世纪上半叶出现在欧洲各国。然而,大多数情况下,报纸上往往登载国外新闻,因为当时的政府限制媒体报道可能具有煽动性的本国新闻,违反者将不予出版。在投石党运动发生前的法国,马萨林派系下的泰奥夫拉斯特·勒诺多的报纸《公报》享有垄断地位,而这份报纸主要报道官方版本的时事新闻。在布鲁塞勒被捕后的几天里,巴黎发生暴力骚乱,而《公报》刻意只用极短的篇幅轻描淡写,甚至没有提到布鲁塞勒的名字:“骚动几乎还没发生就得到平息……这些事件似乎只是为了能让‘国王万岁’的呼声继续回荡在巴黎。”
围城开始后,那些原本负责审查新闻的人逃出巴黎,新闻界进入自治状态。高等法院不断颁布命令,要求印刷商发布新闻前获得许可,但是在这种狂热时期,规定形同虚设。一种比以往都要自由的报纸由此诞生,其产生速度好比巴黎城里的路障。这类新闻专门聚焦当地和当下发生的事件,并以最快的速度产生。
新闻制作人用了一种小到足以塞进口袋的报纸格式,每份8到20页,长8.5到9英寸,宽6英寸。这种设计一方面降低成本,另一方面印刷很快,甚至只需一夜的工夫。报纸没有装订,只用一个书钉或者胶水将页面贴在一起。有的时候,报纸的后面还在写作中,而印刷的人已经在排版报纸的头几页了。
这种新的经营模式也吸引许多人投入报纸产业。
围城发生后,勒诺多跟随宫廷到了圣日耳曼莱昂,用马萨林在那里设立的报社进行保皇派的宣传。然而,由于投石党对巴黎进行入境控制,这种宣传很少能够进入巴黎城内。(不过,在2月11日深夜,一位贵族散发反对巴黎高等法院的宣传册而遭到逮捕。这类人是躲藏在面粉袋里偷偷混进巴黎的。)勒诺多的两个儿子,伊萨克和厄塞布则留在巴黎城内,开始发行亲高等法院立场的期刊《法国通讯》,这也是第一份名字本身就代表速度的法国期刊。这个名字也预示着,其报道内容将是重磅新闻。
最早的一期在1649年1月第2周(5日到14日)发行,该期的专题是深入报道皇室逃离巴黎;后面的几期则是详细讲述巴黎如何在围困中求生的许多故事,比如,巴黎市政府下令让面包师制作一磅、两磅和三磅规格的面包条,发放给穷苦百姓。
在内战的几年里,市面上发行着三十多类期刊。尽管多数并没有存活很久,却带来了信息革命。历史上第一次,巴黎人不仅有了专门报道身边之事的报纸,还能够比较不同角度的新闻。
另一种出版物是随着内战诞生的,那就是像当时的报纸一样便携的政治宣传册,这种读物被称作“马萨林纳德”,即挖苦马萨林枢机的文章,大多数这类读物都是亲投石党立场的。在这座“对新闻如饥似渴”的城市,对这类手册的需求似乎难以彻底满足。约有一千多人在各条街巷散发这类手册,嘴里喊着当时的头条新闻:“《法国政府无能》,快来看看吧!《马萨林被捕》,重大消息!”这情形就像今天街头的新闻报童。
在几年战争时期,共有6000份这样的手册出版,这个数值可能有所低估。在围城的后期,有的宣传册声称,仅仅1649年,该手册就发行了3500份。根据上面的预估,该册子印刷了5000份,而那个时期,500到700份已经属于大规模的印刷量了。那些受欢迎的册子甚至还会重印。其中一份手册标题为《印刷商致谢马萨林枢机》,于1649年3月4日出版,也就是围城期间。这份册子解释说,这个艰难时期,印刷商别无抱怨,他们不同于其他巴黎人。因为他们对马萨林的仇恨如此强烈,以至于“半座巴黎都忙着印刷和售卖手册,而另一半则忙着编写内容。报社从未停工,而印刷商现在也成为巴黎最好的职业。他们赚着原本该属于他们的钱”。
一些马萨林纳德和报纸相似,也讲述具体的事件。一些则是短篇的政治论述文,比如讨论“为何法国人民有发动战争的合法权利”之类的问题。其他则是一些道德上的呼吁,尤其是对正在挨饿的巴黎市民表达同情。所有文章都详细描述时下发生的事件;有一些则比报纸更加详尽,标上具体的日期和排字时间,比如“上午十点三刻”。那些最好的马萨林纳德是上乘的读物,既有政治点评,也有观点,且都是记录当下发生之事。
这类宣传册也是另一种叙述城市的手段,且塑造了冲突期间巴黎不断增强的自我意识。在相当一部分马萨林纳德的叙述中,巴黎都是中心的角色:对政治反抗的报道,前所未有地关注反抗进行中的城市。
一些宣传册中,现代巴黎的一些建筑或景点也被写活了,能借它们的口表达巴黎这座城市的状况。新桥上的亨利四世头像和其他的景点(比如他的“儿子”,也就是皇家广场的路易十三像)互相探讨这座美妙的都城。比如,在一部对话录中(图6为其扉页),亨利四世的塑像和新桥一端的萨玛莉丹塔一同对亲眼所见的“悲惨时代”表示同情。这座塔号称其牢固的钟楼已“彻底损坏”,因而“时间也已脱轨”。而铜像国王也承认,他现在也是靠着每日的《法国通讯》来大致确定“当下的时刻”。
在另外一些宣传册中,巴黎本身也发出了一种声音,并且也成为内战这个剧本的一个角色。在日期为1649年1月8日的马萨林纳德中,“巴黎这位善良的女士”选择了“巴黎高等法院这位精明的老爷”作为她的丈夫,并且宣誓要让法国的财政回到正轨。在另一份围城末期出版的册子里,巴黎发出“战争期间,我不再是巴黎,我只是地狱”的声音。这些册子中,巴黎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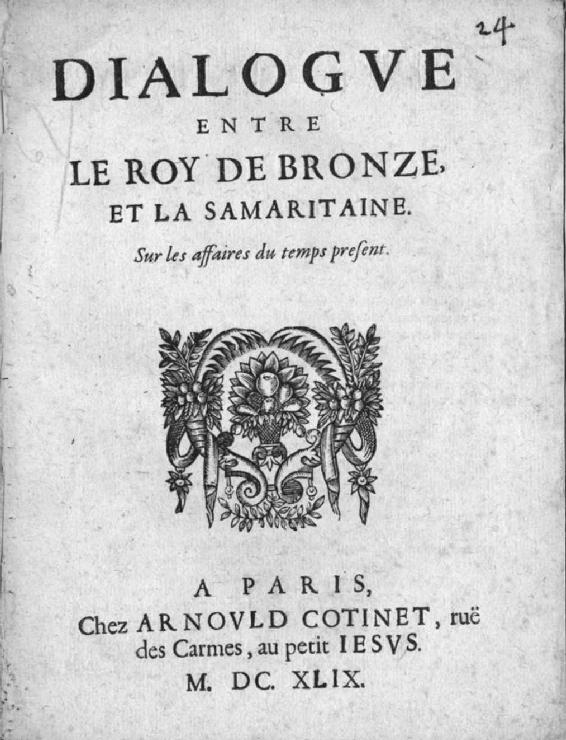
图6 这本内战期间出版的宣传册里,亨利四世的塑像表达对首都所遭受的“悲苦时刻”的哀悼之情
事实上,内战的几年里,这些现代世界的奇迹也迅速转变成城市的噩梦。虽说关于围城期间的平民死亡,尚没有确切的数字,但有一家报社宣称,在1652年的5月中旬,也就是食物价格高于封锁时期的几天里,约有十万人(超过五分之一的巴黎人)在巴黎街头乞讨食物,“其中,半数死于饥饿”。三个月后的一份手册曾警告说,“公共墓地已经无法容下所有的尸体,豺狼开始在巴黎晃荡”。在如此严重的危机下,教会的命令也形同虚设。巴黎的修女和牧师写信给外省的教会分会,说明“成千上万人”正在挨饿,而当时的政府却仅能提供“勉强活命的面包”。挨饿的巴黎人每两三天只能得到一份食物,而食物的分量少得可怜,以至于有位牧师在信件中放入一块作为样品,用以告知情况之紧急。
投石党运动日渐平息。1652年10月21日,路易十四刚打完叛军,返回巴黎。仅仅过了三天,就有一组巴黎代表团写信给这位年轻的国王,正式“请求”他出手相助。这些代表估计,仅仅在这场战争的最后六个月里,巴黎就有五万多人死亡,几乎是城市人口的9%到10%。
在1652年5月,一位记者写道:“这个王国正在烧成灰烬,法国即将灭亡。”街道又一次被链条和路障封锁,不过,这一次,商人们并不想寻求政治变革,而只想保护自己免于团伙抢劫。巴黎不同社会阶层在过去的齐心不复存在。7月4日发生的事件正是“结局的开始”:一群暴徒袭击了市政厅,并且实施纵火,当时那里正进行着会议,探讨如何组织临时政府。投石党和高等法院的几位重要领袖死于这次袭击;民兵也杀死了许多暴徒。很快,就有谣言说,投石党的一派正在策动巴黎人反对起义的早期领袖。
在这次“市政厅大屠杀”之后,越来越多的巴黎人对起义表示不满,他们恳请国王归来。在节日欢庆期间,巴黎人习惯在沿街窗户挂一盏灯。10月21日国王回到巴黎时,巴黎全城上下的居民都在窗边挂上了“皇家灯”。
返回巴黎居住的路易十四年仅14岁。他所面对的新巴黎,虽饱受战争岁月的摧残,却绝不至于落魄。
1652年,投石党运动几近尾声,英国建筑专家、日记作者约翰·埃弗兰(他还是英国驻巴黎大使的女婿)出版了《法国的现状》。这是一本集旅行游记、指南和“励志文学”于一体的作品。埃弗兰并没有回避内战这个话题,而是强调他的一种信念。在他看来,困难只是暂时的。“(巴黎)仍然是其他城市无法企及的。”在1652年出版的著作结尾,他预测:“只要很短的时间与和平,[巴黎]无疑会超过甚至远超现有的规模。”他也预测,一些“无与伦比”的新街道和新建筑将会出现在巴黎。
埃弗兰的作品既承认了巴黎在内战发生前水涨船高的名声,同时也指出,冲突并没有对巴黎的城市形象带来不可恢复的破坏。有了冲突期间产生的新闻机器,这次内战事实上也向大众推广了巴黎这座城市。大量涌现的政治评论不断地满足全欧洲的巨大胃口。投石党的出版物提供了战时新闻,同时也起到了宣传作用,告诉巴黎人他们正在为这座伟大的城市而战,此外,出版物也夸奖了城市的景点。当时描绘起义各大事件的图像中,几乎也同时在炫耀巴黎新建的公共工程。
另一本在战争末期出版的作品也对城市前景表示乐观。该书的作者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巴黎人,人们称之为“贝尔托爵士”。他的作品让巴黎同胞看到,城市有着生机勃勃的日常生活,从露天市场到正在摆卖的衣服,包括各种各样偷来的斗篷。不同于巴黎人过去四年读过的期刊和宣传册,贝尔托的作品只字未提战争和城市。事实上,贝尔托的作品里只有一次提到了投石党。在该段落,一个二手衣服贩子低价转让战场上遗留的一件衣服,为了保证货真,贩子指出了衣服中间的“子弹孔”。贝尔托想要表达的意思十分明显:即使战争尚未完全结束,但投石党运动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页。
事实上,在围城末期,印刷商已经开始把最畅销的马萨林纳德做成合辑出版。过去为巴黎人更新消息、争取人们认同的政治手册又一次获得了生命,让人们保留对旧日事件的记忆。
路易十四不遗余力地让这场内乱成为过去。对此前反对他的权贵,他禁止他们进入宫廷。而且他不再愿意唤起对战争的回忆。这位未来的太阳王找到了更加微妙的手段,表明过去并非彻底遭人遗忘。
1660年夏天,路易十四娶了西班牙的公主,这次婚礼在西法边境举行。国王和新娘回到巴黎的路途中举行了一场华丽的入城仪式。这次活动也广泛地向各地宣传,甚至被用作1661年官方年历的封面,似乎宣示,巴黎不会马上遗忘这次大型仪式。
国王选择让巴黎人庆祝联姻的日期是8月26日,而在1648年的这一天,另一场街头游行之后,巴黎圣母院进行了弥撒,之后便是布鲁塞勒遭捕。居伊·帕坦是巴黎的一位知名医学专家,常和欧洲科学界的大师有来往。在他看来,“巴黎高等法院的人必然能够看到,这次仪式更像是一次救赎,一次惩罚,而非一次华丽的游行”。
投石党也许被官方所遗忘,但是从内战中吸取的教训让巴黎获得了新的形象。战争期间为传播信息而产生的技术,无论是海报还是纸票都继续沿用,尤其在广告上。比如,在1657年3月,超过两万张纸票发行,用于宣传生蚝的优惠价格;类似的宣传活动也用在推广巴黎城里萌芽的奢侈品产业。内战让巴黎人认识到信息流通的重要性,城市因此成为一座广告之都,一个能迅速有效地推广创新成果的变革中心。
巴黎也获得了另一个名声,成为一座敢于抗争的城市,一个革命思想的摇篮,一座敢于挑战固有观念和刻板价值体系的首都。自18世纪之初起,这座现代城市催生了启蒙运动,即现代史上最激烈的思想变革,一直持续到该世纪末。

图7 在这幅1661年的官方年历上可以看到,在投石党运动结束后,皇家军队胜利回到巴黎
到了1772年,历史学家和新闻记者让—巴蒂斯特·梅利撰写五卷本作品,描述了投石党运动的政治历史。他将投石党描绘成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几年“动荡”的前兆,以及“一场引发了史上最重大的、改变政府性质的革命的战争”。在“革命时代”,也就是1789到1848年,梅利的先见很快得到了验证。这个时期见证了许多国家的君主制和一些长久传统的终结。在这期间,巴黎是这些革命的震中,也是重塑欧洲世界的革命思想的摇篮,而城市再一次因接连三次革命而分裂。
其中,第三次革命发生在1848年。这次革命推翻了法国最后一位国王路易·菲利普。过了不到十年,由奥斯曼男爵发起的第二次巴黎大改造开始了。而奥斯曼的大改造,其核心指导思想,也来自投石党运动的余波。而投石党运动也是巴黎史上第一次现代意义的政治抗争。
有人说,路易十四绝不会忘记,巴黎人曾反对他的君权,因此把精力全部投在凡尔赛宫上,忽略了巴黎这座反叛的都城。但这个说法忽视了巴黎历史上最重要的时期,也就是1660年后的十二到十五年。从那时起,这位太阳王和由大臣以及公务员组成的卓越团队一起启动了一些大胆的计划,其中包括两项巴黎的特色工程:林荫大道和明亮灯火。在投石党运动结束后不到十年,这位年轻的国王开始对首都进行现代化改造,而进度也不像之前两位波旁国王那样,一次只进行一个。他开发出了一种被称为“宏伟构想”的计划,对城市上上下下进行全面的规划。
约翰·埃弗兰在1652年的预言因此很快成真:“美得无与伦比”的街道穿过城市,而巴黎这个名字也前所未有地和城市规划紧密关联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