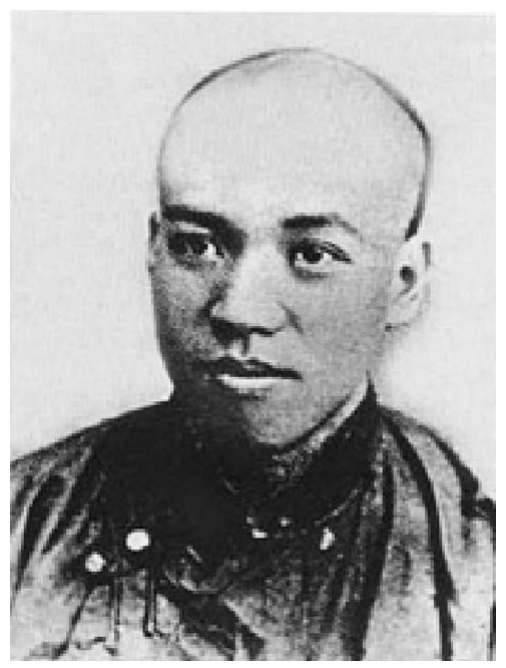第四节 儒家公共哲学及“公德”、“正义”问题
关于个体隐私与亲亲等合理之私领域的保护,最明显的即是孔子有关“亲亲互隐”的提倡与孟子的维护、发展。然而此一点颇为人所诟病。实际上,我们平情体察,孔孟有很多高于一般人的智慧,其涵盖的深意及对中国历史文化、政治法律制度、民间社会的正面的深入的影响,不是肤浅地运用简单的形式逻辑与抽象的知性,加上强词夺理所能驳倒的。
荀子的礼学也有丰富的公共哲学资源。关于公正、正义,荀子有很多讨论。他提出过“公正无私”、“志爱公利”的命题(《荀子·赋》)。荀子认为,禹之所以为禹,在于他有“仁义法正”,老百姓也可以成为禹:“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荀子·性恶》)在为官者执法与执政的问题上,荀子说:“故公平者,听之衡也。中和者,听之绳也。其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听之尽也。偏党而无经,听之僻也。”(《荀子·王制》)“公生明,偏生暗。”(《荀子·不苟》)“上端诚则下愿悫矣,上公正则下易直矣。”(《荀子·正论》)“政令法,举措时,听断公……是诸侯之所以取国家也。”(《荀子·荣辱》)“怒不过夺,喜不过予,是法胜私也。《书》曰:‘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此言君子之能以公义胜私欲也。”(《荀子·修身》)
儒家一贯强调私恩与公义的差别,区分了公共领域与私人空间,大小戴《礼记》和郭店楚简都有“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断恩”(郭店简中“断”为“斩”)的论说,在实践上更是如此。门内以恩服为重,门外以义服为重,私恩与公义是有明确界限的。郑玄注文中有“事亲以恩为制,事君以义为制”。怎么能说儒家只讲亲情,不讲正义、公正、公德?怎么能把今天贪污腐败的根子找到儒家价值上?有关“亲亲互隐”与公私权界的问题,我们专设了下一讲。
后世儒家不断纠正法家,解构法家。商韩之法的“公”,指国家权力、帝王权力,这与孔孟之公共事务的正义指向有原则的不同。法家有功利化、工具性的趋向,为富国强兵的霸王之政治目标,牺牲人的丰富的价值乃至戕害人性与人情。商韩之法以刑赏二柄驾驭、驱使百姓,而且意在泯灭百姓私人利益,化私为公(其公即是霸主的“国家利益”)。刘宝才、王长坤认为:“儒家承认在道德原则指导下追求私利的合理性,并要求统治者‘制民之产’、‘节用而爱人’、‘与民同乐’,表现了可贵的民本主义的思想。法家主张立公废私,任公不任私。为了维护公利、公义,个人应该牺牲一切。法家的这种公私观,从历史上看,对于维护新兴地主阶级的国家利益,削弱和限制大臣贵戚们的利益,对于当时正在进行的统一中国的伟大事业,具有积极意义。但法家的公私观仅仅与法治思想联系在一起,认为公与私绝对对立……一面夸大人的自私心,一面主张绝对去私立公,在两者的尖锐对立中走向绝对君主专制主义……历史实践证明,在公私观问题上儒家的理论高于法家。”[17]
有关孔子对最卑贱的小民的关怀,要求官府首要职责在保障其辖区人民的温饱,以及庶富教的方略,罗思文(Henry Rosemont)认为,乃是具有通向作为民主理想的公共自治同样要求的特质。他还重视儒家君子品格的社会性。罗思文肯定孟子有关杀死那些不关心民生的暴君的合法性,并将这些不顾民生之辈置于道德等级的最下层。罗思文认为,孟子,尤其荀子的《王制》有关以职业训练、公共福利和健康保险等社会事业来帮助人民,要求政府提供足够的物资和服务以接济人民,对病人、穷人、文盲、孤寡及社会福利的关怀,在与他们同时代的西方思想家那里是找不到的,也与马基雅维里大相径庭。他说:“无论是柏拉图的《理想国》、《律法书》,还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我们都找不到有关政府如何有义务救济老弱病残及贫民的言论。这一点非常重要。”[18]
有人指责中国传统文化中,特别是儒学,没有人的权利的看法,只有义务的看法,这是不准确的。权利与自由等都是历史的范畴,只能以历史主义的眼光来看待。重视人的生命,维护其财产,珍视其名誉,都是人的基本权利,儒家非常强调这些基本权利。不唯宁是,孔子与孟子的公私观内蕴着深厚的公共性与公正性的思想资源。孔孟一方面以天、天道与天德为背景,其仁、义的价值与仁政学说中,充满了对民众的最基本的生存权与私利的关怀,甚至把保护老百姓的生存权、财产权、受教育权、参与政治权和防止公权力滥用,作为真正的“公”,是良好政治的主要内容,在历史上制度化为土地、赋税制度、农商政策与类似今天社会保障的养老、赈灾、救济弱者制度,以及拔擢平民子弟的教育制度与文官制度及其他制度;另一方面,也是以天、天道与天德为背景,孔孟深深体验到人性、人情的根本,护持亲情与家园,这些理念也逐步制度化为隐私权、容隐权与亲情权的保护。第三方面,孔孟强调从政者的敬业、忠诚、廉洁、信用品性等责任伦理,在君臣关系的处理上包含了区分职权、责任及相互制约的萌芽,尊重民意,强调察举以及官守与言责,不仅是公共责任意识,而且是分权制衡的初步。孔孟的人文价值理念长期浸润在中国民间社会,又不断转化为传统政治法律制度,是我国现代化建设重要的精神资源与制度的参鉴。
属于常识性错误,至今还被不少论者奉为圭臬,成为思维定势的,还有黑格尔所谓孔子的主张只不过是俗世伦理、常识道德,罗素所谓中国伦理不注重公共义务,梁启超所谓中国传统伦理注重“私德”不注重“公德”等等。这些都需要认真地辨析。至于有的论者把“私德”说成“私欲”,则更是荒谬绝伦。儒家讲的“私”与“己”是不同的概念。
我在这里特别要说说所谓儒家文化不讲“公德”的问题。梁启超即为这种公德私德理论的始作俑者。“试观《论语》、《孟子》诸书,吾国民之木铎,而道德所从出者也。其中所教,私德居十之九,而公德不及其一焉……若中国之五伦,则惟于家族伦理稍为完整,至社会国家伦理,不备滋多。此缺憾之必当补者也。皆由重私德轻公德所生之结果也。”那么,我们就有必要首先弄清梁启超究竟是如何来界说公德与私德的?其理论依据何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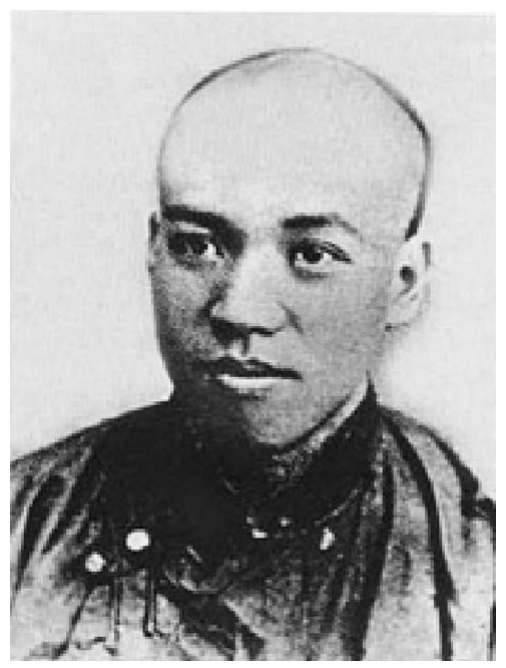
梁启超
先且看梁启超对公德与私德的界说及其来源和背景。梁启超于20世纪初在《论公德》一文中称:“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二者皆人生所不可缺之具也。无私德则不能立,合无量数卑污、虚伪、残忍、愚懦之人。无以为国也。无公德则不能团,虽有无量数束身自号、廉谨良愿之人,仍无以立国也。”[19]“有益于群者为善,无益于群者为恶。此理放诸四海而皆准,俟诸百世而不惑者也。”[20]基于上述这种对公德与私德的看法,梁启超认为:“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21]故他试图“发明一种新道德”以补我国民最缺的公德,他所谓的“吾辈生于此群,生于此群之今日,宜纵观宇内之大势,静察吾族之所宜,而发明一种新道德,以求所以固吾群、善吾群、进吾群之道”[22]即表明这一点。梁启超当时以功利主义者边沁(JeremyBentham,1748—1832)作为参照。但边沁的功利主义伦理学与孟子的德性伦理学属于不同的伦理系统,很难加以比较。当然,梁启超此论源于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与《劝学篇》。
梁启超《论公德》一文属于他的系列文章《新民说》中的篇章,发表于1902年。1903年梁启超曾赴美访问考察,1904年初梁启超发表了他的《论私德》一文。在此《论私德》一文中,梁启超称:“公德者,私德之推也,知私德而不知公德,所缺只在一推;蔑私德而谬托公德,则并所以推之具而不存也。故养成私德,而德育之事思过半焉矣。”[23]“一私人而无所私有之德行,则群此百千万亿之私人,而必不能成公有之德性。”[24]“是故欲铸国民,必以培养个人之私德为第一义;欲从事于铸国民者,必以自培养其个人之私德为第一义。”[25]梁启超《论私德》一文中的这种观点可谓是对他《论公德》一文中的观点的反戈一击和根本否定,这也表明梁启超在通过深入地实地考察和真正地体验后对那种以英、美民族性为蓝本的“公德”、“私德”理论有着深刻地反省。正是基于这种深刻地反省,他认为自己在输入、引进泰西之学时所宣扬的所谓“公德”标准,“谓其有‘新道德学’也则可,谓其有‘新道德’则不可。何也?道德者行也,而非言也”[26]。并且,梁启超在这种深刻地反省中也对儒家伦理有了重新的认识,“其先哲之微言,祖宗之芳躅,随此冥然之躯壳,以遗传于我躬,斯乃一社会之所以为养也,一旦突然欲以他社会之所养者养我,谈何容易耶!”[27]可见,梁启超至此不仅完全抛弃了他自己以前那种儒家只重私德而轻公德的看法,而且还深刻地认识到儒家伦理的真正的价值和作用。梁启超生前就抛弃了他自己所输入和引进的那种公德私德理论。
近些年来,一些学者讨论所谓“公德”、“私德”,大多未脱离梁启超的路数,一般都只用了梁氏的前一半。也有人把公私德定义为所谓“社会性的公德”与“宗教性的私德”,将仁义忠孝等儒家德目分别归类,削足适履。其实,细考孝、悌、忠、敬、仁、义、礼、智、信、诚等道德产生的历史原因、内涵之衍生变迁过程,不难知道每一德目都既是私德又是公德。
最后,关于公正。“公正原则是任何一个社会成立的基础,它牵涉到权利、义务、利益以及对、错、道德、不道德等概念。如果我们这样了解社会以及公正原则在社会中所具有的功能,则涂尔干的那句话——每一个社会都是一个道德的群体——的意义就变得更加清楚。因为每一个社会都是靠一组公正原则才得以成立,而这组原则是用以界定什么是对与错的根据。如果我们把对、错的范围限制在分配的问题上,这组原则就是有关分配公正的原则。”[28]
什么是社会正义呢?黄克武说:“结合个体环绕着自我利益的关怀,即是社会正义。”[29]我认为,环绕着下层百姓的根本利益的关怀,即是社会正义。是不是只有从社会契约论出发才能生长出社会正义?儒家关于社会正义的讨论是需要另一视域才能看清的。我认为,孔孟主张的恰好是实质公正而不是形式公正。
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学所追求的根本目标就是正义:“政治学上的善就是‘正义’,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按照一般的认识,正义是某些事物的‘平等’(均等)观念。……简而言之,正义包含两个因素——事物和应该接受事物的人;大家认为相等的人就该配给到相等的事物。可是,这里引起这样的问题,所谓‘相等’和‘不相等’,它们所等和所不等者究为何物?这个问题中所包含的疑难应在政治学上从事明智(哲学)的考察。”[30]
但不同的阶层对于正义的认识是迥然不同甚至截然对立的,因为各方都会按照自己各自的利益进行判断。也就是说,平民们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主张人与人之间应该在一切方面都完全平等;而寡头们则主张,应该按照人们才能的高下、财富的多少、德性的优劣及对城邦贡献的大小来有差别地分配权利。
亚里士多德认为,正是这样要求平等的愿望构成了城邦冲突的源泉,城邦的内讧往往就是因其而引起的。基于对双方片面性及其危害的深刻认识,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两种不同的平等观,以试图将两者综合统一起来。
“所谓平等有两类,一类为其数平等,另一类为比值平等。‘数量相等’的意义是你所得的相同事物在数目和容量上与他人所得者相等;‘比值相等’的意义是根据各人的真价值,按比例分配与之相衡称的事物。”[31]

亚里士多德
合理的方法应该是既肯定平民的自由身份,也要考虑到人与人之间在才能、德性与贡献上的差异,以“中道”的原则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力求将两者统一起来,避免走向极端:“正当的途径应该是分别在某些方面以数量平等,而另一些方面则以比值平等为原则。”[32]
人们一般将这两种不同的权利(利益)分配原则简称为“应得”和“配得”原则;也有人将以公共利益为依归的正义称为广义的、普遍的正义或政治上的正义,将两种具体的权利(利益)分配原则称为狭义的正义。
以此为参照来认识儒家文化的公私观,不难看到,不仅孔孟儒家关于利益(权利)的分配应根据人的德性、才能和贡献而有等级之别的思想,与亚里士多德的“配得”观念或“分配的正义”观具有很强的内在相通性,而且当孔子提出“有教无类”、主张尊重一切人的生命权和幸福权时,其实在一定意义上也蕴含着亚里士多德的第一种正义观的含义。
罗尔斯关于正义的两个基本原则是:
“第一个原则:每个人对与其他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
第二个原则: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1)被合理地期望适合于每一个人的利益;并且(2)依系于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放。”[33]
第一个原则被称为平等自由原则,意味着每个人在包括政治自由、言论集会自由、良心思想自由、个人人身自由与财产权等在内的基本自由权利方面乃是一律平等的;第二个原则被称为差别原则,即物质利益的分配不仅应该惠及每一个人,而且应该在规则上最有利于不利者。按照罗尔斯的设想:
“它们区别开社会体系中这样两个方面:一是确定与保障公民的平等自由的方面,一是指定与建立社会及经济不平等的方面。……按照第一个原则,这些自由都要求是一律平等的,因为一个正义社会中的公民拥有同样的基本权利。”[34]
“第二个原则大致适用于收入和财富的分配,以及对那些利用权力、责任方面的不相等或权力链条上的不同的组织机构的设计。虽然财富和收入的分配无法做到平等,但它必须合乎每个人的利益,同时,权力地位和领导性职务也必须是所有人都能进入的。”[35]
“这两个原则是按照先后次序安排的,第一个原则优先于第二个原则。”[36]
尽管毋庸讳言,由于时代的原因,儒家文化在第一个原则方面的确有所欠缺,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孔孟儒家力图通过礼义教化和规范来防止社会分配的严重不均,维护、保障老幼鳏寡的利益的思想,则与罗尔斯正义观中关于应该有利于社会的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的主张,不无契合之处;而上述孔子有教无类等思想,及作为儒家文化重要体现和成果的文官制、科举制等,与罗尔斯的第二个正义原则中所提出的在机会公平均等的条件下,权力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的要求更有着强烈的共鸣。
【注释】
[1]“公正的优先性”所指的是,在社会所可能具备的众多美德中,公正这项美德所占有的地位是最高的(见石元康:《罗尔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近年来,我请香港大学慈继伟教授来武汉大学系统地讲“自由主义”、“儒家与自由主义”、“正义的两面”等课程,并与慈先生多次交谈。是正当优先还是善优先,这是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争论的一个问题。这个优先当然是源头意义上的。“正当”讲的是“应该”,是无选择的。从价值源头的意义上讲,善优先于正当;从规范上讲,正当优先于善。慈先生与我都认为:儒家的善与正当是合一的;儒家不能归类为社群主义;儒家也不是政治权威主义;儒家诸价值与自由主义可以沟通、对话、融合。又请参看哈佛燕京学社与三联书店主编:《儒家与自由主义》,三联书店2001年版,特别是其中的第一篇:《儒家与自由主义——和杜维明教授的对话》。
[2]参见〔美〕本杰明·史华兹:《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程钢译,刘东校,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0—31、61、71、80、109页。
[3]〔日〕溝口雄三:《中国公私概念的发展》,《思想》669号,东京岩波书店1980年3月;《中国的公私》上下,《文学》59卷第9、10期,东京岩波书店1988年10月;《中国与日本“公私”观念之比较》,香港《二十一世纪》1994年2月号总第21期。又见溝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索介然、龚颖译,中华书局1997年版。
[4]简良如:《黄宗羲〈明吏待访录〉之公私观——兼与卢梭〈社会契约论〉之比较》,台北《中国文哲研究集刊》2005年9月第27期,第216—217页。
[5]刘泽华、张荣明等:《公私观念与中国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6]刘泽华:《春秋战国的“立公灭私”观念与社会整合》,刘泽华、张荣明等:《公私观念与中国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8—19、21页。
[7]黄俊杰、江宜桦编:《公私领域新探:东亚与西方观点之比较》,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5年版。
[8]黄俊杰、江宜桦:《导言》,同上书,第1页。
[9]黄俊杰、江宜桦:《导言》,黄俊杰、江宜桦编:《公私领域新探:东亚与西方观点之比较》,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5年版,第1页。金泰昌:《以“活私开公”的公共哲学构筑“世界—国家—地域”之共働型社会结构》,黑住真:《“公共”的形式与近世日本思想》,俱见黄俊杰、江宜桦所编书。
[10]黄俊杰:《东亚近世儒者对“公”“私”领域分际的思考》,黄俊杰、江宜桦编:《公私领域新探:东亚与西方观点之比较》,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5年版,第134页。
[11]以上参见黄俊杰:《东亚近世儒者对“公”“私”领域分际的思考》,黄俊杰、江宜桦编:《公私领域新探:东亚与西方观点之比较》,第119—121页;刘畅:《古文〈尚书·周官〉“以公灭私”辨析》,刘泽华、张荣明等:《公私观念与中国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6—87页。
[12]刘泽华先生说,此处的“公”已隐含有对“私”的否定。见《春秋战国的“立公灭私”观念与社会整合》,刘泽华、张荣明等:《公私观念与中国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页。刘文没有说此处隐含着否定谁家之私,我看至少并未否定民众之“私”。
[13]关于儒家理念中的权利意识、公私权界观,以及儒家与专制主义的区别,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汉代的《盐铁论》。以桑弘羊为代表的国家主义者,主张盐铁官卖,由中央政府垄断,强力控制商人与商业,由政府自上而下维护社会秩序,而以贤良文学为代表的广大儒生则主张盐铁由民间经营,反对控制商人与商业,由各地方与民间形成并维系自发的有层次的社会秩序。杜维明很重视这一点,详见《儒家与自由主义》,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84页。又,桑弘羊主张以商韩什伍连坐之法控制民间,而贤良文学则举起孔孟与公羊《春秋》“亲亲互隐”的大旗,强调保护老百姓的亲情权、隐私权、容隐权,详见本书第六讲。
[14]荀子与《礼记》中关于公共、正义价值的论述,见下节。
[15]详见任铭善:《礼记目录后案》,齐鲁书社1982年版。
[16]详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7]刘宝才、王长坤:《儒法公私观简论》,刘泽华、张荣明等:《公私观念与中国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3页。
[18]罗思文:《谁的民主?何种权利?——一个儒家对当代自由主义的批评》,商戈令译,见《儒家与自由主义》,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41—242页。
[19]梁启超:《论公德》,《饮冰室合集》第6册《专集之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页。
[20]同上书,第15页。
[21]同上书,第12页。
[22]同上书,第15页。
[23]同上书,第119页。
[24]同上。
[25]同上。
[26]梁启超:《论私德》,《饮冰室合集》第6册《专集之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31页。
[27]同上书,第132页。
[28]石元康:《罗尔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页。
[29]黄克武:《引言》,黄克武、张哲嘉主编:《公与私:近代中国个体与群体之重建》,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年版,第iv页。
[30]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48—149页。
[31]同上书,第234页。
[32]同上书,第235页。
[33]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6页。
[34]同上书,第57页。
[35]同上书,第57页。译文略有改动。
[36]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