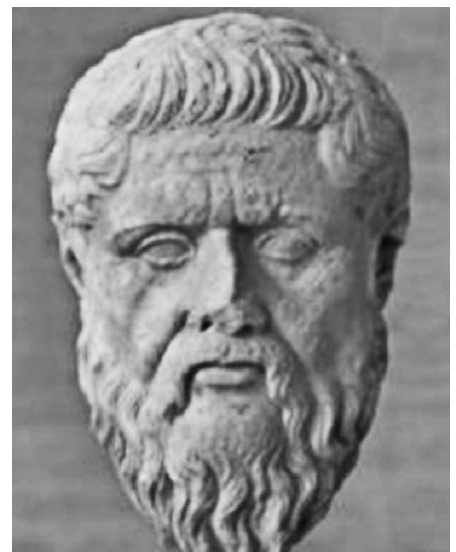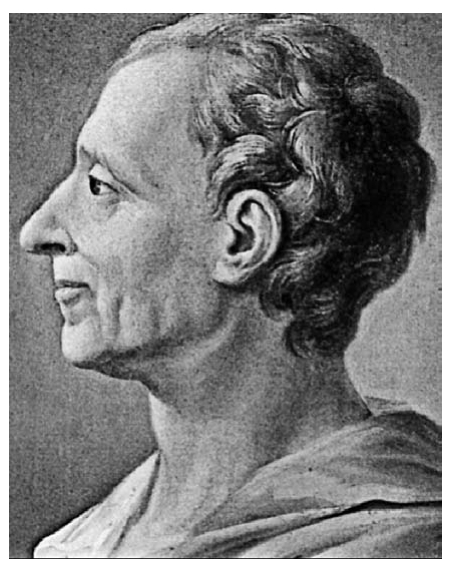-
1.1第一讲 儒学概说
-
1.1.1第一节 原 “儒”
-
1.1.2第二节 孔子与门人
-
1.1.3第三节 四个发展阶段
-
1.2第二讲 五经四书
-
1.2.1第一节 五 经
-
1.2.2第二节 四 书
-
1.3第三讲 人文精神
-
1.3.1第一节 中华人文的特质
-
1.3.2第二节 儒学与中华民族精神
-
1.4第四讲 核心价值
-
1.4.1第一节 中国儒学的中心观念
-
1.4.2第二节 韩国儒学的中心观念
-
1.4.3第三节 日本儒学的中心观念
-
1.4.4第四节 以仁爱为本的核心价值系统
-
1.4.5第五节 儒家核心价值的现代意义
-
1.5第五讲 公私观与正义论
-
1.5.1第一节 公与私
-
1.5.2第二节 孔子的公正性诉求
-
1.5.3第三节 孟子的正义论
-
1.5.4第四节 儒家公共哲学及“公德”、“正义”问题
-
1.6第六讲 亲亲相隐
-
1.6.1第一节 三文本的要旨
-
1.6.2第二节 “直”、“隐”与“爱有差等”
-
1.6.3第三节 西方思想史上的“亲亲相隐”
-
1.6.4第四节 容隐制与人权
-
1.7第七讲 人性学说
-
1.7.1第一节 孟子的性善论
-
1.7.2第二节 荀子的性恶论
-
1.7.3第三节 汉唐诸儒的人性论
-
1.7.4第四节 宋代理学的心性论
-
1.8第八讲 和谐与中庸之道
-
1.8.1第一节 民族性格
-
1.8.2第二节 四个向度
-
1.8.3第三节 中庸之道
-
1.9第九讲 理想境界
-
1.9.1第一节 君子、圣人、仁人与成人
-
1.9.2第二节 子思、孟子的理想人格论
-
1.9.3第三节 孔孟人格境界论及宋明儒的发展
-
1.9.4第四节 儒学的生死观及其当代价值
1
中国儒学之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