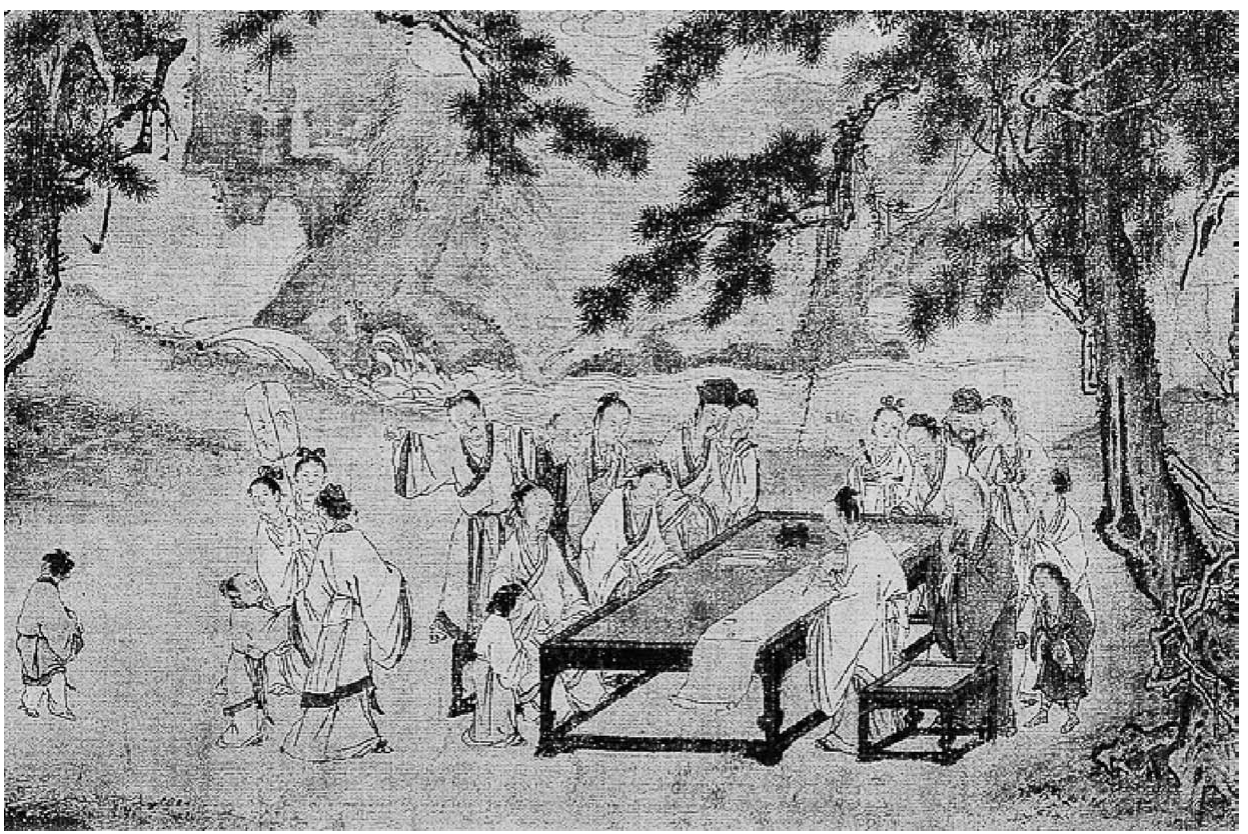第二节 儒学与中华民族精神
儒学史与社会文化史是相辅相成、相交相融的。儒家发挥了周公、孔子以来的人文主义精神,在中国传统民间社会中,影响最大。儒学的最高信仰和终极理想,可以用“天人合一”、“性道合一”的命题来加以表达。儒学是一个不断与时俱进的活传统,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精神资源和现代人安身立命的根据。
中国文化精神与民族性格主要是由儒家奠定和陶冶的。就整部中国历史来说,中国社会是四民(士农工商)社会,士为四民之首。士的变动可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变动。士代表、弘扬、实践、坚守了中国人的人文理想,担当着中国社会教育与政治之双重责任。钱穆先生说:“此士之一流品,惟中国社会独有之,其他民族,其他社会,皆不见有所谓士。士流品之兴起,当始于孔子儒家,而大盛于战国,诸子百家皆士也。汉以后,遂有士人政府之建立,以直迄于近代。”[6]钱穆指出,中国古代社会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不需要教堂牧师和法堂律师,而形成一种绵延长久、扩展广大的社会。这靠什么呢?主要靠中国人的人与人之道,靠“人”、“人心”、“人道”等等观念,靠士在四民社会中的作用及士之一流品的精神影响。“孔子之伟大,就因他是中国此下四民社会中坚的一流品之创始人。”[7]中国古代社会,从乡村到城市乃至政府都有士。这个士的形成,总有一套精神,这套精神维持下来,即是“历史的领导精神”。“中国的历史指导精神寄在士的一流品。而中国的士则由周公、孔、孟而形成。我们即由他们对于历史的影响,可知中国历史文化的传统精神之所在。”[8]指导中国不断向前的精神被钱穆称为“历史的领导精神”。他通过详考历史、对比中外,肯定地指出,士是中国社会的领导中心,一部中国历史的指导精神寄托在士的一流品,一部中国历史主要是由儒家精神——由周公、孔子、孟子培育的传统维系下来的。

《新定三礼图》中所载的“士玄端”
中国历史的“领导精神”即是人文精神,重视历史的精神,重视教育的精神和融和合一的精神。
钱穆认为,中国传统人文精神源于五经。周公把远古宗教转移到人生实务上来,主要是政治运用上;孔子进而完成了一种重人文的学术思想体系,并把周公的那一套政治和教育思想颠倒过来,根据理想的教育来建立理想的政治。经周、孔的改造,五经成为中国政(政治)教(教育)之本。经学精神偏重在人文实务,同时保留了古代相传的宗教信仰之最高一层,即关于天和上帝的信仰。中国人文精神是人与人、族与族、文与文相接相处的精神,是“天下一家”的崇高文化理想。中国文化是“一本相生”的,其全部体系中有一个主要的中心,即以人为本位,以人文为中心。传统礼乐教化代替了宗教的功能,但不与宗教相敌对,因此不妨称之为“人文教”。中国文化精神,要言之,只是一种人文主义的道德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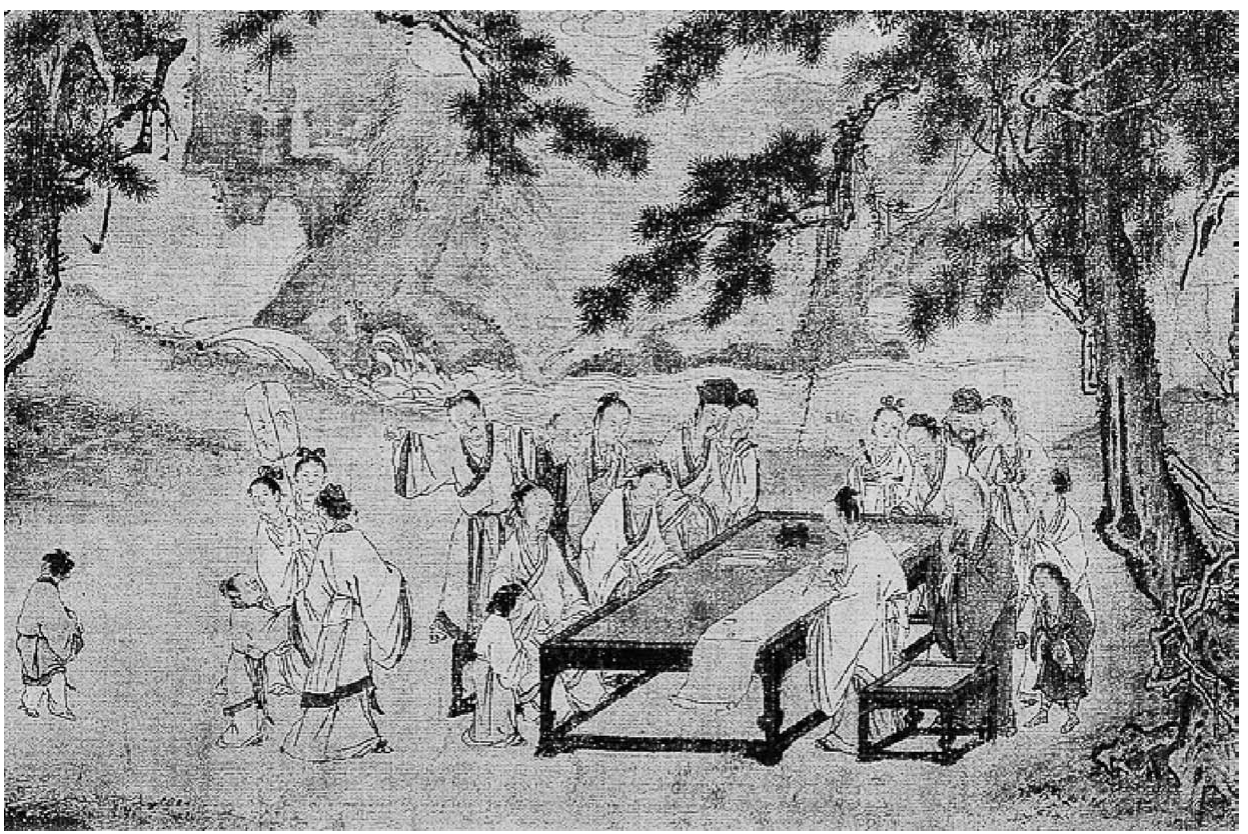
(南宋)马远《西园雅集图》
中国传统注重历史的精神源于五经。周孔重视人文社会的实际措施,重视历史经验的指导作用。尤其孔子具有一种开放史观,并在新历史中寄寓褒贬,这就是他的历史哲学与人生批评。孔子促使了史学从宗庙特设的史官专司转为平民学者的一门自由学问,倡导了经学与史学的沟通。钱穆指出,中国历史意识的中心是人。中国人历史意识的自觉与中国先民,特别是周公、孔子以来的人文自觉密切联系在一起。在中国,特别在儒家,历史、民族与文化是统一的。民族是文化的民族,文化是民族的文化,而历史也是民族和文化的历史。民族与文化只有从历史的角度才能获得全面的认识。中国人对历史的重视,对史学的兴趣及史学之发达,特别是“经世明道”,“鉴古知今”,“究往穷来”,求其“变”又求其“常”与“久”的精神,来源于儒学。
中国传统注重教育的精神源于五经。钱穆认为,中国古人看重由学来造成人,更看重由人来造成学。中国人研究经学,最高的向往在于学做周公与孔子的为人,成就人格,达到最高的修养境界。中国古代文化及其精神是靠教育薪火相传、继往开来的。中华民族尊师重道的传统由来已久,而儒家则把教育推广到民间,扎根于民间,开创了私家自由讲学的事业,奠定了人文教育的规模和以教立国的基础。中国人教育意识的自觉不能不归功于儒家。
中国传统注重融和合一的精神源于五经。中国古人的文化观,以人文为体,以化成天下为用。五经中的“天下”观,是民族与文化不断融凝、扩大、更新的观念。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同化力,表明中国人的文化观念终究是极为宏阔而适于世界性的。这源于儒家的一种取向,即文化观念深于民族观念,文化界限深于民族界限。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的性格中的“和合性”大于“分别性”,主张宽容、平和、兼收并蓄、吸纳众流,主张会通、综合、整体、融摄,这些基本上都是儒者所提倡和坚持的价值[9]。
钱穆得出中国历史文化的指导精神即为儒家精神的结论,是有其可靠的根据的。他极其深入地考察了中国历史思想史,十分肯定地说:“中国思想以儒学为主流。”“儒学为中国文化主要骨干。”[10]在先秦思想史上,开诸子之先河的是孔子。孔子的历史贡献,不仅在于具体思想方面的建树,更重要的在于他总体上的建树。他既是王官之学的继承者,又是诸子平民之学的创立者,是承前启后开一代风气的人物。正是这一特殊历史地位,决定了他在先秦诸子学说中的重要作用。整个说来,诸子学说标志春秋以来平民阶级意识的觉醒,是学术下移民间的产物。钱穆认为,中国古代,是将宗教政治化,又要将政治伦理化的。换言之,就是要将王权代替神权,又要以师权来规范君权的。平民学者的趋势只是顺应这一古代文化大潮流而演进,尤其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因为儒家最看重学校与教育,并将其置于政治与宗教之上。儒家已不再讲君主与上帝的合一,而只讲师道与君道的合一。儒家只讲一种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的人生人道,这就是人道或平民道。在孔孟仁学体系的浸润下,儒家完成了政治与宗教的人道化,使宗教性与神道性的礼变成了教育性与人道性的礼。
钱穆比较了儒、墨、道三家的异同,指出,墨、道两家的目光与理论,皆能超出人的本位之外而从更广大的立场上寻找根据。墨家根据天,即上帝鬼神,而道家则根据物,即自然。墨、道两家都有很多思想精品和伟大贡献。但无论从思想渊源还是从思想自身的特点来看,儒家都在墨、道两家之上。这是因为,儒家思想直接产生于中国社会历史,最能反映和体现中国社会历史的实际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与思维方式。先秦以后,历代思想家大体上都是以儒家为轴心来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并融会其他诸家的。如果说儒家是正,那么,墨、道两家是反,它们两家是以批评、补充儒家的面貌出现的。如果说儒家思想多为建设性的进取,那么墨、道两家则主要是社会批判性的。

董仲舒
关于先秦学术思想的总结,钱穆认为,这一总结是在秦始皇到汉武帝这一段历史时期内完成的。学术思想的统一伴随着政治上的统一。在政治上,以李斯为代表的法家为轴心的统一,历史已证明是失败的,其标志是秦王朝的灭亡;而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为轴心的统一,则是适应并促进当时社会发展的,是成功的,其标志是汉唐大业。当时在学术上的调和统一有三条路,一是超越于儒、墨、道法诸家之上,二是以道家为宗主,三是以儒家为宗主。第一条路的代表是吕不韦及其宾客,但他们没有超越诸家之上更高明的理论,没有吸收融合诸家的力量,因此《吕氏春秋》只是在诸家左右采获,彼此折中,不能算是成功的。第二条路的代表是刘安及其宾客。由于道家思想本身的限制,不可能促进当时历史大流向积极方向前进,因此《淮南子》也不是成功的。第三条路的代表是儒家,即是这一时期出现的《易传》及收入《礼记》中的《大学》、《中庸》、《礼运》、《王制》、《乐记》、《儒行》诸篇的作者们。他们以儒家思想为主,吸收墨、道、名、法、阴阳诸家的重要思想,并把这些思想融化在儒家思想里,成为一个新的系统。例如《易传》、《中庸》,弥补了儒家对宇宙自然重视不够的毛病,吸纳了道家,建构了天道与人道、宇宙界与人生界、自然与文化相合一的思想体系。《易传》、《中庸》吸取老庄的自然观来阐发孔孟的人文观,其宇宙观是一种德性的宇宙观。《大学》、《礼运》仍是德性为本论,把孔孟传统以简明而系统的方式表达了出来,提高了道的地位,融合了道家观念及墨家重视物质经济生活的思想。这不仅表明了儒家的涵摄性,而且表明了儒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主干地位,并不是自封的,并不是靠政治力量支撑得来的,而是中国历史与中国社会选择的结果,是自然形成的。其原因在于儒学的性质与中国社会历史实际相适应[11]。
钱穆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彻头彻尾,乃是一种人道精神、道德精神。”[12]“中国传统人文精神所以能代替宗教功用者,以其特别重视道德观念故。中国人之道德观念,内本于心性,而外归极之于天。”[13]他认为,孟子“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之教,实得孔学真传。他强调说:“孟子主张人性善,此乃中国传统文化人文精神中,惟一至要之信仰。只有信仰人性有善,人性可向善,人性必向善,始有人道可言。中国人所讲人相处之道,其惟一基础,即建筑在人性善之信仰上。”[14]
钱穆指出,整个人生社会唯一理想之境界,只是一个“善”字。如果远离了善,接近了恶,一切人生社会中将没有理想可言。因此,自尽己性以止于至善,是中国人的最高道德信仰;与人为善,为善最乐,众善奉行,是中国人的普遍宗教。由于人生至善,而达至于宇宙至善,而天人合一,亦只合一在这个“善”字上。中国人把一切人道中心建立在这一“善”字上,又把天道建立在人道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全只是在人圈子里尽人道。人道则只是一善字,最高道德也便是至善。因此说,中国的文化精神,要言之,则只是一种人文主义的道德精神。”[15]道德在每个人身上,在每个人心中。儒家文化希望由道德精神来创造环境,而不是由环境来摆布生命,决定人格。道德是每个人的生命,每个人的人格,是真生命、真性情的流露。“这一种道德精神,永远会在人生界发扬光彩。而中国人则明白提倡此一道德精神而确然成为中国的历史精神了,这是中国历史精神之最可宝贵处。”[16]总之,钱穆认为,道德精神是中国人内心所追求的一种做人的理想标准,是中国人向前积极争取蕲向到达的一种理想人格。
正是在这一前提下,钱穆肯定“中国文化是个人中心的文化,是道德中心的文化,这并不是说中国人不看重物质表现,但一切物质表现都得推本归趋于道德。此所谓人本位,以个人为中心,以天下即世界人群为极量”[17]。所谓以个人为中心,以人为本位,则是以个体修身为基元,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贯理想。钱穆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中之人文修养,是中国文化最要支撑点,所谓人文中心与道德精神,都得由此做起。钱先生引用《大学》所说的“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作为人文修养的主要纲目。他指出:“所谓人文,则须兼知有家庭社会国家与天下。要做人,得在人群中做,得在家庭社会国家乃至天下人中做。要做人,必得单独个人各自去做,但此与个人主义不同。此每一单独的个人,要做人,均得在人群集体中做,但此亦与集体主义不同。要做人,又必须做一有德人,又须一身具诸德。……人处家庭中,便可教慈教孝,处国家及人群任何一机构中,便可教仁教敬。人与人相交接,便可以教信。故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乃一切寄托在人生实务上,一切寄托在人生实务之道德修养上,一切寄托在教育意义上。”[18]在这里,我们可知儒家人文精神本质上是人的道德精神,而道德精神落脚在每一个体的人,并推广至家、国、天下。也就是说,通过教化和修养,不同个体在家、国、天下等群体中尽自己的义务,彼此相处以德,终而能达到“天下一家”的道德理想境界。钱穆认为,中国文化之终极理想是使全人生、全社会,乃至全天下、全宇宙都变为一孝慈仁敬信的人生、社会、天下、宇宙,这即是人文中心道德精神的贯彻。钱穆认为,知识和权力都是生命所使用的工具,不是生命本身,只有人的道德精神才是人的真生命,也才是历史文化的真生命。因此我们要了解历史文化,也必须透过道德精神去了解。他把道德精神作为推动历史文化的动力和安顿人生的根据。

古代玉琮。其形状象征天圆地方。
钱穆用两大命题来概括儒家哲学精义,其一为“天人合一”,其二为“性道合一。”
关于“天人合一”。他说:“人心与生俱来,其大原出自天,故人文修养之终极造诣,则达于天人之合一。”又说:“中国传统文化,虽是以人文精神为中心,但其终极理想,则尚有一天人合一之境界。此一境界,乃可于个人之道德修养中达成之,乃可解脱于家国天下之种种牵制束缚而达成之。个人能达此境界,则此个人已超脱于人群之固有境界,而上升到宇宙境界,或神的境界,或天的境界中。但此个人则仍为不脱离人的境界而超越于人的境界者,亦惟不脱离人的境界,乃始能超越于人的境界者。”[19]
钱穆在综合中国经学的主要精神时指出:“一是天人合一的观念,对于宇宙真理与人生真理两方面一种最高合一的崇高信仰,在五经中最显着、最重视,而经学成为此一信仰之主要渊源。二是以历史为基础的人文精神,使学者深切认识人类历史演进有其内在一贯的真理,就于历史过程之繁变中,举出可资代表此项真理之人物与事业及其教训,使人有一种尊信与向往之心情,此亦在经学中得其渊源。”[20]
也就是说,人们可以不脱离现实界而达到超越界,现实的人可以变为超越的人,可以摆脱世俗牵累,达到精神的超脱解放。中国传统认为圣人可以达到这一境界,但圣人也是人,所谓“人人可以为圣人”,是人人都可以通过道德修养而上达于天人合一之境界。要做一个理想的人,一个圣人,就应在人生社会实际中去做。要接受这种人文精神,就必须通晓历史,又应兼有一种近似宗教的精神,即所谓“天人合一”的信仰。中国传统文化的终极理想,是使人人通过修养之道,具备诸德,成就理想人格,那么人类社会也达到大同太平,现实社会亦可以变为超越的理想社会,即所谓天国、神世、理想宇宙。在钱穆那里,“天人合一”不仅指自然与人文的统一,而且指现世与超世的统一,实然与应然的统一,现实与理想的统一,尤其是超越与内在的统一,对天道天命的虔敬信仰与对现世伦常的积极负责的统一,终极关怀与现实关怀的统一。
关于“性道合一”。“性道合一”其实也是“天人合一”,因为性由天生,道由人成。中国人讲道德,都要由性分上求根源。换句话说,道德价值的源泉,不仅在人心之中,尤其在天心之中。《中庸》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道”指人道、人生或文化,是对人生、人类文化一切殊相的一种更高的综合。那么“修道之谓教”的教育,也是一种道。中国人讲的“道”不仅仅指外在的文化现象,而且指人生本体,指人生的内在的意义与价值。中国文化最可宝贵的,在其知重道。道由何来呢?道是人本位的,人文的,但道之大原出于天。“性”的含义,似有动力、向往、必然要如此的意向。“中国传统文化,则从人性来指示出人道。西方科学家只说自然,中国人则认为物有物性,才始有物理可求。西方宗教家只说上帝,中国人则说天生万物而各赋以性。性是天赋,又可以说是从大自然产生,故曰‘天命之谓性’。”[21]中国人最看重人性。中国古人讲“性”,超乎物理、生理之上,与西方观念不同。人生一切活动都根于人性,而人性源于天。由天性发展而来的、人心深处的性,是一共相。性善之性、至诚之性、尽己之性的“性”,既有人先起的性,又有人后起的性,是人性及其继续发现和发展。一切由性发出的行为叫做道,既然人性相同,则人道也可相同。“中国人说率性之谓道,要把人类天性发展到人人圆满无缺才是道。这样便叫做尽性。尽己之性要可以尽人之性,尽人之性要可以尽物之性,这是中国人的一番理论。”[22]
钱穆强调人性不是专偏在理智的,中国人看性情在理智之上。有性情才发生出行为,那行为又再回到自己心上,那就叫做“德”。人的一切行为本都是向外的,如孝敬父母,向父母尽孝道。但他的孝行也影响到自己心上,这就是“德”。“一切行为发源于己之性,归宿到自己心上,便完成为己之德。故中国人又常称德性。……中国人认为行为不但向外表现,还存在自己心里,这就成为此人之品德或称德性。性是先天的,德是后天的,德性合一,也正如性道合一,所以中国人又常称道德。”[23]

(北宋)赵佶《听琴图》(局部)
综合以上“天人合一”、“性道合一”之论,可知儒家人文的道德精神是有其深厚的根源与根据的。其特点有三。第一,这种人文主义是内在的人文主义,由此可以说“中国文化是人本位的,以人文为中心的,主要在求完成一个一个的人。此理想的一个一个的人,配合起来,就成一个理想的社会。所谓人文是外在的,但却是内发的”[24]。中国文化是性情的、是道德的,道德发于性情,这还是性道合一。第二,中国的人文主义又不是一种寡头的人文主义,“人文求能与自然合一。……中国人看法,性即是一自然,一切道从性而生,那就自然人文合一。换句话说,即是天人合一”[25]。中国人文主义要求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使天、地、人、物各安其位,因此能容纳天地万物,使之雍容洽化、各遂其性。第三,这种人文主义深深地植根于中国原始宗教对于天与上帝的信仰,对于天命、天道、天性的虔敬至诚之中,说人不离天,说道不离性;因而这种人文主义的道德精神又是具有宗教性的。综上所述,内在与外在的和合、自然与人文的和合、道德与宗教的和合,是中国人精神不同于西方人文主义的特点。不了解这些特点,亦无从界定中国民族精神。
钱穆说,中国人的最高信仰,乃是天、地、人三者之合一。借用西方基督教的话来说,就是天、地、人三位一体。天地有一项工作,就是化育万物,人类便是万物中之一。但中国人认为,人不只是被化育,也该能帮助天地来化育。这一信念也是其他各大宗教所没有的。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或宗教的信仰,总是认为有两个世界存在,一个是人的、地上的或物质、肉体的世界,一个是神的、天上的或灵魂的世界。中国人则只信仰一个世界。他们认为,天地是一自然,有物性,同时也有神性。天地是一神,但同时也具物性。天地生万物,此世界中之万物虽各具物性,但也有神性,而人类尤然。此世界是物而神、神而物的。人与万物都有性,此性禀赋自天,则天即在人与万物中。人与物率性而行便是道。中国人的观念中,人神合一,人即是神,也可以说人即是天。人之善是天赋之性,人能尽此性之善,即是圣是神。这就是性道合一、人天合一、人的文化与宇宙大自然的合一、神的世界与人的世界的合一。人的一切代表着天,整个人生代表着天道。因此,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最高信仰,文化与自然合一则是中国文化的终极理想[26]。
按钱穆的理解,中国思想史里所缺乏的是类似基督教那种一元外在超越的宗教;但中国却有一种入世的人文的宗教。儒家思想的最高发展必然常有此种宗教精神作源泉。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就是这种人文教的最高信仰,最高教义。这种人文教的天堂就是理想的社会,这种人文教的教堂就是现实的家庭与社会。要造成一理想的社会,必先造成人们理想的内心世界,人人共有的心灵生活。这种内在的心地,孔子曰仁,孟子曰善,阳明曰良知。只要我们到达这种心地,这个人就已先生活在理想的社会中。这是这种理想社会的起点。必须等到人人到达这种心地与生活,才是这种社会的圆满实现。这是人类文化理想的最高可能。达到这种心地与生活的人生就是不朽的人生。儒家的这种人生实践又必然带着中国传统的宗教精神,即入世的人文教精神。
儒家思想的重心与价值,只是为人类提出一个解决自身问题的共同原则。这些原则本之于人类之心性,本之于社会,本之于历史经验,最为近人而务实。另一方面,儒家的终极关怀又具有天命根据与冥悟体认的宗教性格。“天”、“天命”、“天道”是宇宙万物、人类生命的本原,是生命意义的价值源头,亦是一切价值之源。儒者彻悟生死和在精神上超越俗世、超越死亡的根据是天、天道、天命及其对人之所以为人的规定。儒者确实有极其浓厚的世间关怀,然而在其世间肯定之中仍有其超越的形而上的要求,即终极的最后的关怀。儒者为捍卫人格尊严而不惜“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儒者“以天下为己任”、“救民于水火”的信念目标和救世献身的热诚,尤其是至诚至信、虔敬无欺的神圣感,尽心知性、存心养性、“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的安身立命之道,都表明了他们具有宗教的品格。儒者的使命感、责任感、担当精神、忧患意识和力行实践的行为方式,特别是信念信仰上的终极承担,都有其超越的理据。总之,我们需要重新发掘、体认和诠释儒家“天命论”与“心性论”的精神价值。
像钱穆这样的知识分子,终其生不忘“吃紧做人”。“数十年孤陋穷饿,于古今学术略有所窥,其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虽居乡僻,未尝敢一日废学,虽经乱离困厄,未尝敢一日颓其志,虽或名利当前,未尝敢动其心,虽或毁誉横生,未尝敢馁其气。虽学不足以自成立,未尝或忘先儒之榘矱,时切其向慕。虽垂老无以自靖献,未尝不于国家民族世道人心,自任以匹夫之有其责。”[27]他终生坚持儒家的最高信仰和终极理想,直到九六高龄,在临终前三个月还对“天人合一”这一儒家哲学最高命题“专一玩味”,因自己最终“澈悟”而感到“快慰”。从钱穆的人生,我们亦可看出儒家人文教的宗教情意结对中国士人知识分子的精神安立的作用。
钱穆重视儒学在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生活方式中的客观基础,特别是在水汭地域、农耕文明、统一天下、四民社会、文治政府、廊吏或科举制度背景下的儒家文化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儒学的产生、发展及其成为中国几千年文明维系的轴心,都是有其客观基础的。
另一方面,与此相应,儒家价值系统是潜存、浸润于广大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的,不过由圣人整理成系统而已。正如余英时先生所强调的,钱先生把章学诚“圣人学于众人”的观念具体化、历史化了,因此着力研究两千年来随着社会生活客观现实的变化发展而不断更新的儒家文化及其价值系统。
钱穆肯定心性学说是中国学术的“大宗纲”,治平事业是中国学术的“大厚本”。他说,中国历史的传统理想是由政治领导社会,由学术领导政治,而学术起于社会下层,不受政府控制。如前所述,这种以人为主,重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的人本主义精神,蕴含有宗教精神并代替了宗教的功能。中国学术可分为两大纲。“一是心性之学,一是治平之学。心性之学亦可说是德性之学,即正心、诚意之学,此属人生修养性情、陶冶人格方面”;“治平之学,亦可称为史学,这与心性之学同样是一种实践之学。但我们也可说心性学是属于修养的,史学与治平之学则是属于实践的。具备了某项心理修养,便得投入人群中求实践。亦贵能投入人群中去实践,来作心性修养工夫。此两大纲,交相为用,可分而不可分”[28]。
钱穆认为,儒学的真生命、真精神,是推动我们民族及其历史文化发展壮大,克服黑暗,走上光明的原动力,即“生力”。“五四”以来,很多人把“生力”视为“阻力”、视为“包袱”。他批评了毁谤传统儒学精神的思潮是“过激主义”或“过激思想”,认为此一思潮“失其正趋”,“愈易传播流行,愈易趋向极端”[29]。他屡屡驳斥这一思潮对本国历史的无知和歪曲。例如,笼统地以所谓“封建”概括中国传统社会,以“专制”概括古代政治体制,说“中国比西方落后一个历史阶段”云云,基本上是“袭取他人之格套,强我以必就其范围”,“蔑视文化之个性”。他又说:“汉武帝表彰六经,罢黜百家,从此学术定于一尊。此说若经细论,殊属非是。”“常有人以为,中国历代帝王利用儒家思想,作为其对人民专制统治的工具。此说更属荒谬。”[30]钱穆以历史事实驳斥了诸如此类似是而非之论。
儒家学说,不仅是天、地、人、物、我协调发展的理论,不仅有助于保护人类生存的生态环境,而且在人文沉沦的今天,有助于解决人的精神安顿与终极关怀的问题。现代人的心灵缺乏滋养,人们的生命缺乏寄托。而现代化的科技文明并不能代替现代人思考生命与死亡等等的意义和价值的问题。儒学,特别是仁与诚的形上本体论与宇宙论、心性论、人伦关系论、理想人格论、身心修养论、人生价值论等,可以扩大我们的精神空间,避免价值的单元化和平面化,避免西方“现代性”所预设的价值目标的片面性,批判工具理性的恶性膨胀。儒学的安身立命之道可以丰富我们的人生,提升我们的人格,活化性灵,解脱烦恼,缓冲内心的紧张,超越物欲的执著,复活人文理想的追求,使人真正过着人的生活。儒家精神对21世纪的社会和人生,肯定会起着愈来愈大的作用。
儒学的生命力仍在民间。儒学本来就具有平民性格,是民间学术。几千年来,它代表着社会的良知,担当着社会的道义,以道统,即以其“领导精神”,制约、指导着政统与治统。其依托或挂搭处则是民间自由讲学。随着我国工商现代化的发展,民间书院、民间研究所、民间同人刊物的兴盛已是必然的趋势。儒学一定能适应现代生活的发展,返回于民间,扎根于民间。今天,我们亦需要作类似于由五经传统向四书传统转移那样的努力。儒学精神的现代转化一定会取得成功。
儒学在现代社会的创造性转化有助于促进自然、社会、人生协调和谐地发展,克服民族及人类素质的贫弱化和族类本己性的消解。一个人,一个族类,必然有自己的精神根源与根据,必然有自己终极的信念信仰。儒学资源是21世纪中国与世界重要的精神食粮。
【注释】
[1]参见孔汉思等:《全球伦理》,台北雅歌出版社1996年版。
[2]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3卷,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337页。
[3]转引自颜泽贤:《耗散结构与系统演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7—108页。
[4]朱亚宗、王新荣:《中国古代科学与文化》,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本书作者提出了很多与似是而非的时论颇不相同的观点,是一部充满独到见解的专著。
[5]参见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下),《唐君毅全集》卷八,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版,第44—51页。
[6]钱穆:《民族与文化》,香港新亚书院1962年版,第7页。
[7]同上书,第66页。
[8]同上书,第79页。
[9]以上详见钱穆:《中国学术通义》,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版,第2—6页;《民族与文化》,第3、29、48页;《中国历史精神》,1964年香港增附三版,第136页;《中国文化史导论》,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影印本,第19、120页。
[10]钱穆:《中国思想史》,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版,第171页;《新亚遗铎》,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9年版,第417页。
[11]以上详见钱穆:《中国思想史》,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版,第86—110页。
[12]钱穆:《民族与文化》,香港新亚书院1962年版,第32页。
[13]同上书,第25页。
[14]同上。
[15]同上书,第29页。
[16]钱穆:《中国历史精神》,1964年香港增附三版,第104页。
[17]同上书,第136页。
[18]钱穆:《民族与文化》,香港新亚书院1962年版,第32—33页。
[19]同上书,第31页。
[20]钱穆:《中国学术通义》,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版,第13页。
[21]钱穆:《中华文化十二讲》,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7年三版,第9页。
[22]钱穆:《中华文化十二讲》,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7年三版,第12页。
[23]同上。
[24]同上书,第13页。
[25]钱穆:《中华文化十二讲》,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7年三版,第14页。
[26]详见钱穆:《中华文化十二讲》,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7年三版,第83—86页。
[27]钱穆:《宋明理学概述·自序》。
[28]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8年版,第72页。
[29]参见罗义俊:《钱穆对新文化运动的省察疏要》,《现代新儒学研究论集》(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30]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8年版,第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