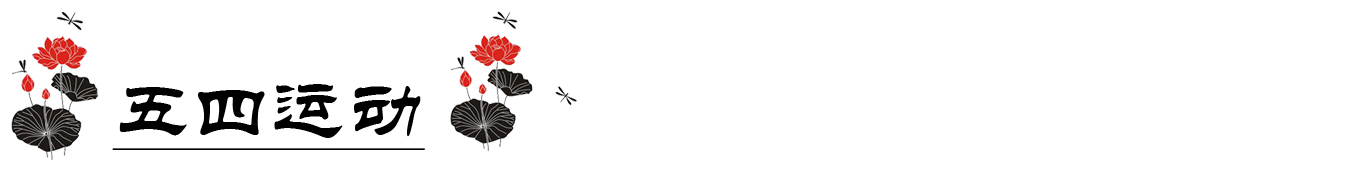
五四运动是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北京的一场以青年学生为主,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中下阶层共同参与的,通过示威游行、请愿、罢工、暴力对抗政府等多种形式进行的爱国运动,是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
从1918年11月的“公理战胜强权”庆典,到次年1月的巴黎会议,短短两个月时间,当时的中国充分诠释了“自古弱国无外交”的定律,所谓的“公理战胜强权”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童话。面对这样屈辱的局面,从5月1日开始,北京的学生纷纷罢课,组织演讲、宣传,随后天津、上海、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南的学生、工人也给予支持。
五四运动直接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党史一般将其定义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并以此运动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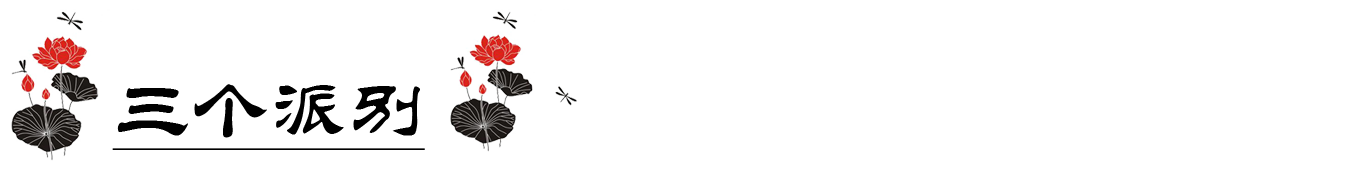
学衡派
学衡派是因在南京创办的《学衡》杂志而得名,是以《学衡》为中心﹐在思想文化界形成的一个文学复古﹑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流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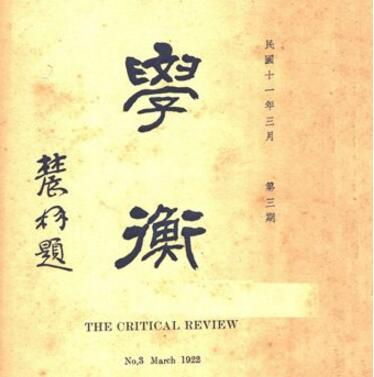
学派代表人物为当时国立东南大学(现南京大学)的教授梅光迪、吴宓、胡先骕。学派认为“昌明国粹﹐融化新知”,认为新文化运动为“模仿西人﹐仅得糟粕”﹔攻击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是诡辩家﹑模仿家﹑功名之士﹑政客。
学派反对新文学运动,认为文言优于白话,觉得白话是“以叙说高深之理想,最难剀切简明”,极力主张言文不能合一。以柳诒征为南雍双柱之一的东南大学,是现代儒学复兴的策源地;以其为国学支柱的学衡派,成为后世新儒家的学术滥觞。
文学思想
“文学是人生的表现”,这种观点构成了学衡派文学思想的基础。由是他们从中引出了三个值得重视的见解:其一,文学不可能脱离时代;其二,文学与政治相辅相成;其三,文学创作必然包含着主客观的因素。从为人生的文学出发,学衡派强调从事创作的作家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学素养或称文学的诸要素:社会责任感、善于观察与理解人生、文学艺术的修养。学衡派对于文学创作规律的探讨,也涉及接受美学的理论问题,认为成功的文学作品须有杰出的作家与聪明的读者两个条件,二者兼具作品才能流传。从总体上看,学衡派从两个层面上探讨过文学价值的判断问题:首先,从内容的分际上,探讨文学作品的久暂;其次,从作品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关系上,探讨道德标准与艺术标准的分际。学衡派的文学思想虽然存在着道德化的倾向,但又包含着合理的内核,即强调文学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学衡派与新文学运动的分歧,如文白之争、新旧诗之争,多属学理之争,得失互见,理有固然。后期学衡派的文学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肯定新文学,归趋于平实。斥学衡派为反对新文学的守旧派的传统论点,有失简单化。总之,我们应当肯定学衡派的文学思想本身就构成了新文学发展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史学思想
学衡派对于西方史学思想的变动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其一,关于史学的新观念。学衡派指出:考证史料仅仅是历史研究的第一步,“于此又需要第二步工作,即是解释史事之原因变化与结果之由来,以及与过去及未来之关系。其二,关于扩大史学研究范围的新观念。学衡派不赞成旧史学偏重政治史的弊端,认为它不足包括人类活动的全部,历史范围当无所不包。学衡派十分赞成新史学派的观点,强调史学的社会功能:一是明历史的因果关系,彰往而察来,助益社会进化;二是开拓人们的时空观念,以形成刚健笃实、勇于进取的精神,多识前言往行,增进道德情怀;三是见先贤功业,培养国民的爱国心。学衡派既肯定历史学认识的相对性,但是并不怀疑历史学的科学性。综上所述,学衡派的史学思想实现了从实证主义传统到新史学的转换,反映了他们得风气之先,对于中国史学发展趋势的总体把握富有前瞻性,包含着宏富的内涵与巨大的历史合理性。
教育思想
学衡派眼中的教育功能包括养成“治事治学之能力”和“修身之志趣与习惯”。二者并重,缺一不可。学衡派所谓教育的目的在于使受教育者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新时代的国民,而其中又突出了品德与爱国主义的教育。它不仅反映了对欧战的反省,而且反映了对国情的深思。学衡派突出能力培养。而要实现这一点,在教育思想与教育观念上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其一,注重宏通教育,避免学生的知识结构失之偏狭。其二,“适应学生个性”,即课程结构、人才培养的规格不能模式化,而是因材施教,人尽其才。其三,注重教学方法和学生的科研训练。学衡派提出“国民教育职业化”的构想。这就是说,初等教育除了教书外,还应当增加谋生的技能。高等教育必须进一步提高水准。大学教育,既贵专精,尤贵宏通,学生应有更多自由讲习研求的机会。为此,专业设置不能太多。学衡派从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健全的人格,即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国民这一根本的教育理念出发,强调学校教育应突出学生的能力培养,并进而提出了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改革现有的学校课程结构,注重文理渗透,开拓学生的视野,优化知识结构等主张。在今天看来,也不乏借鉴的意义。当然,学衡派的教育思想也存在对其时的政治变动过于漠视,不免就教育谈教育,故其强调培养健全的人格虽不乏合理性,但难以实现。
道德思想
学衡派的文化思想的核心是其伦理道德,即“道德为体,科学为用”的主张,着意强调人类在物质文明日进的情况下,当守护精神价值,怀有追求至善境界的精神家园和终极关怀的重要命题。不论人们赞成与否,学衡派的道德思想在其时毕竟成一家之言,尤其是他们所倡导的抽象道德理念和道德的宗教信仰,以及以此为鹄的的君子精神,有力地彰显了时人对于人文精神的诉求。学衡派的道德思想是欧战后出现的世界范围反思现代主义和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新思潮涌动的产物,虽因时代的落差,就当时的中国国情而言,不免过于理想主义,但它毕竟有着合理的内核,历久而弥彰。
学衡派文化思想不仅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的重要课题,而且更是深入研究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思潮变动所必需的,它开拓了人们的眼界,丰富和推动了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发展。不仅如此,学衡派所反复强调的,在人类社会追求进步与发展的过程中不容轻忽人文关怀的重要命题,无疑又具有可贵的前瞻性。在人们诉求人性和人文精神的呼声日高的今天,其内在的合理性愈加明显。
自由派
谈及中国现代文学,自然绕不开胡适这一灵魂式的人物,其一呼百应程度足以与迅哥相提并论。所谓“胡适派”的一群,是中国较为早期的自由主义与现代派学者,生于乱世,因理想而集结。
承上启下的过渡时代,往往因为混乱而迷人。“自由主义”以炫酷的名字和巨大的影响力登上历史舞台,同样承载了复杂性的内涵,无论是西方以韦伯为驱动的现代性自由“已知量”的面目模糊,还是以严复、梁启超所开启的中国“自由”主义概念与中国古汉语之“自由”差异甚笃。再加之以“原则”、“学说”为内核的“主义”风潮当时刚刚兴起,尚无更多可鉴之传统。正如作者章清所言,在自由主义这一概念上,并“没有提供明晰的‘思想光谱’。”但尽管难以界定清晰,毋容置疑的是,这群团结在胡适周围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中国文化史上闪闪发光的存在。

在自由派兴盛之初,是由胡适为代表定位为的“监督舆论的政论家”。他们充满了精英政治思想,其成员承续了五四时期的批判精神,试图重建社会秩序,充满了文人的理想主义,并试图超然独立于政党之外:只认国家,不认党派;只有政见,没有党见。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终于被自己的抱负卷入了政治的漩涡之中,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徘徊。于是,古史辨同样成为政治战场,他们以“批判的姿态”、“科学的方法”对旧学术宣战,整理国故,继续扩散新文化运动所带来的对于思想的解放力量。由于自由派学者的优厚教育背景,他们对于文化建设同样采取了激进的态度,努力重振北大,并试图让教育成为建国的力量。这些“反思传统”、“谋中国学术之发展”的努力自然值得鼓励,然而由于背负的理想与政治息息相关,胡适派自由主义者的枷锁与束缚亦日趋加重。
激进派
辛亥革命前,维新派和革命派没有彻底批判封建思想;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所用封建思想禁锢人们的头脑;一战期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要求实现民主政治。
代表人物: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

主张:追求民主与科学;反对专制和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化,新文学,反对旧文化,旧文学。
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发起的新文化运动是用资产阶级思想批判腐朽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斗争,它猛烈地抨击了封建专制的理论基石——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旧道德、旧文化,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为以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开辟了道路。局限性表现在对东西方文化的全盘否定或肯定,同时也没有同群众运动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