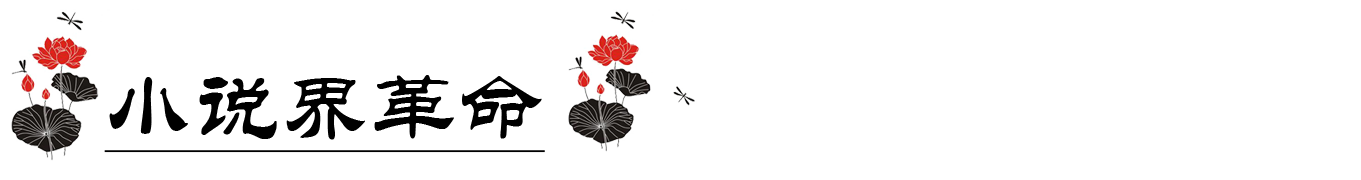
光绪二十八年十月,《新小说》杂志在日本横滨创刊。1902年11月,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提出了"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的口号,这是"小说界革命"的开始。 首先,梁启超强调了小说对于社会改革和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将其地位提高到经史、语录、律例之上,打破了千百年来鄙薄小说的传统偏见。 其次,提倡小说界革命,将小说创作纳入资本主义社会改革的轨道,并为小说作出新的分类,为新小说的创作题材揭示了广泛而现实的内容范围 第三,揭示了小说具有"浅而易解"、"乐而多趣"的艺术特点,分析了小说具有"支配人道"的"熏"、"浸"、"刺"、"提"四种艺术感染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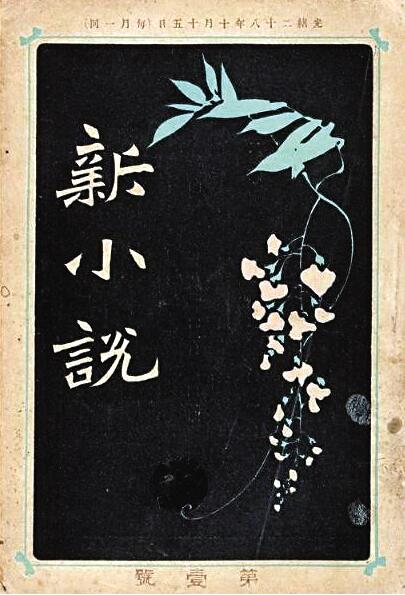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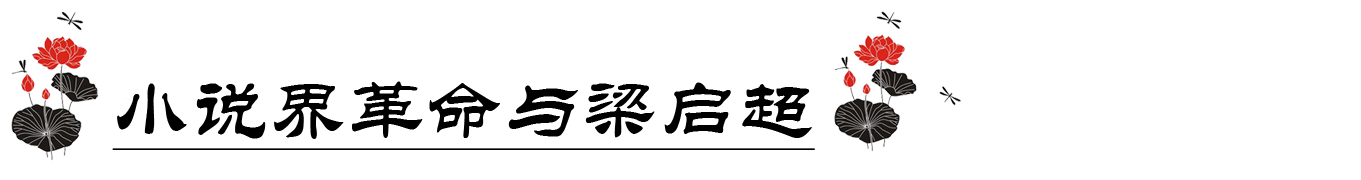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政治宣传家,“戊戌变法”遭通缉流亡日本。1902年,他在自己创办的《新小说》杂志上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关系》一文。他将变法失败的症结归为“民智不开”,并认为中国要完成维新大业,必须改良群治,即让老百姓了解“身外之身,世界之外世界”,也就是西方的社会与政治状况。此时,他认为小说是开民智最有力的武器。为了让国民重视小说,他夸张地宣称“小说是文学之最上乘”,它与人生息息相关,“如空气,如菽麦,欲避不得避,欲屏不得屏,而日日相与呼吸之餐嚼之矣”。他偏激地宣称,我国的古典小说,因华坛商贾制造状元宰相、才子佳人、江湖盗贼、妖恶狐鬼思想,都与腐败的封建观念相联系,必须抛弃。而“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梁启超在这篇呐喊“小说界革命”的文章,文胜于理,激情掩盖了创造性的缺乏。他不仅对“群治”、“新民”、“新小说”等当年时尚语汇未及仔细说明,而且把小说推到了云端之中,让其承担了无法充当的社会角色。 然而,在当年的上海,梁启超此言一出,如平地一声响雷,它震撼了无数知识分子的心灵,并很快激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别士、楚卿、松岑、陶佑曾等人纷纷发表文章,他们除了赞同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观点外,沿着“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思路,鼓吹“新小说”,强调小说改造社会功用和价值。 当理论成为一种风气时,它常常有意想不到的神力。20世纪初“新小说”理论影响就是如此。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口号在上海广泛传播后,当年一批知名的作家和翻译家相继站出来表态,以示跟随时代前进。李伯元在主办《游戏报》时,曾公开声称“觉世之一道”是“游戏”,他推崇玩世不恭的情感,倡导游戏人生。但是,1902年在《编印<绣像小说>缘起》一文中,李伯元突然换了个模样,他称“欧美化民,多由小说,搏桑崛起,推波助澜”,“于是纠合同志,首辑此编”,此时他强调自己编发小说的目标是“或对人群积弊而下砭,或为国家危险而立鉴”。这些话几乎是梁启超语言的一种翻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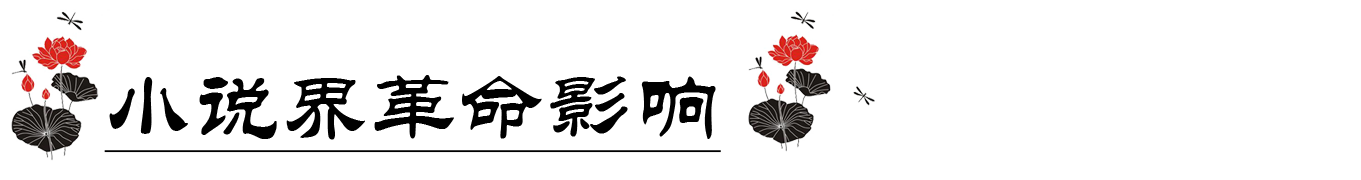
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号召产生了巨大影响,可是被他视为核心内容的政治小说数量既不多,且只行时了二三年,半个多世纪来小说发展各要素的长期准备难道只是为了这短暂的辉煌?而且,梁启超涉足小说界也是纯为维新变法的短暂客串,故而念念不忘的是“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他赏识的作品文学意味甚淡薄,甚至归入小说都很牵强。梁启超亲自撰写了《新中国未来记》,该篇勾勒理想中的将来中国图景,又被列为创刊号的重头之作,可算是“小说界革命”的创作典范。可是梁启超自己承认,该篇“往往多载法律、章程、演说、论文等,连篇累牍,毫无趣味”,文体“似说部非说部,似裨(稗)史非裨(稗)史,似论著非论著”,创刊号上借外国史实,鼓中国士气的《东欧女豪杰》、《洪水祸》等作,同样是政治呼喊多于文学意味。梁启超辩解道:“既欲发表政见,商榷国计,则其体自不能不与寻常说部稍殊。”小说从属于政治,而且只要具有政治性,是否具有小说的文体特征都已无所谓。于是有个问题油然而生:“小说界革命”与小说发展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

“小说界革命”的实践只维持了很短的一段时间,绝大多数的创作或翻译与改良群治“杳乎其不相涉也”。梁启超倡导的实践很快就销声匿迹,他极力推崇的《佳人奇遇》与《经国美谈》,对大众的吸引力根本无法与《巴黎茶花女遗事》或福尔摩斯侦探案相匹敌。另外还有些翻译小说,以及后来出版的《官场现形记》等小说的行销都远远超过了梁启超的得意之作。“小说界革命”实是提供了能量释放的契机,它很快成为被借以招徕读者的招牌。尽管吴趼人等对此局面不满,但这是小说本身的逻辑发展,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或改变,因为梁启超等人考虑的是谋取直接的政治功利,小说只是实现目的的工具,所谓“小说界革命”是政治的需要,并非小说发展过程中的内在要求,故而它只可能是短暂的存在。
不过,“小说界革命”的影响却相当深远,它对传统旧小说的批判深入人心,“新小说”取代旧小说已被认为是理应之事。在“小说界革命”的号召下,许多人投身于小说创作,尽管其创作宗旨与梁启超多不相同,作品面目也迥异,但都在努力地提供新式样的作品。“小说界革命”以磅礴之势扫除了新小说发展的障碍,直接促使了创作热潮的出现。总之,小说发展正面临着变革转折,而政治变革又以小说为最有力的宣传工具,两者的结合导致了“小说界革命”的发生,它使小说原先的渐进模式变成了突变式的飞跃,并又在相当程度上参与了后来小说发展态势的决定。因此,尽管“小说界革命”是基于政治态势的变化与政治人物的需要的外加因素,但它一旦发生,便又成为小说发展历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在近代小说史上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