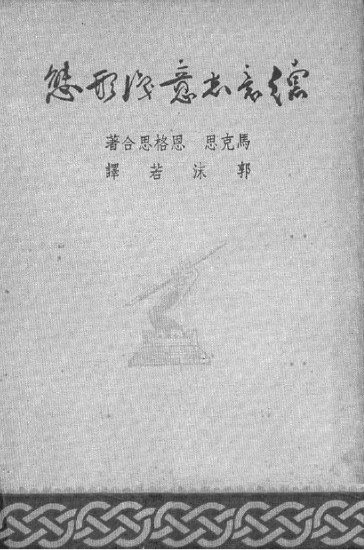四、对“真正的社会主义”中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批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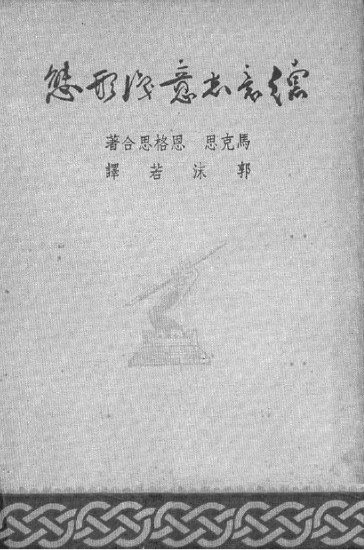
郭沫若翻译、群益出版社出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947年)封面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的标题为“对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该卷主要批判了当时在德国流行的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或“德国社会主义”,揭示了这种假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社会根源和阶级本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进行批判,是因为大部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不仅受到费尔巴哈思想的强烈影响,而且还赞同施蒂纳的无政府主义的观点,他们把费尔巴哈的人的“真正的”、真实的本质嫁接到法国社会主义上,认为自由的思想已经过时了,由此他们要求直接实现人的“真正的”本质,因此,他们拒绝参加任何为争取“资产阶级”权利的斗争。他们的集会包含许多道德化的和情感的东西,而这些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并不利于对历史进行合理的分析。[89]
在第二卷开始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指出,除德国共产主义者之外,还出现了许多著作家,他们接受了英国和法国的某些共产主义思想,把这些思想和自己的德国哲学前提混为一团。这些自称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认为外国的共产主义文献并不是一定的现实运动的表现和产物,而纯粹是一些理论的著作,这些著作完全像他们所设想的德国哲学体系的产生一样,是从“纯粹的思想”中产生的。他们把这一派中的某些著作家的幻想信以为真,似乎这些著作家所谈的是“最合理的”社会制度,而不是一定阶级和一定时代的需要。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没有看到,即使这些著作是在宣传某些体系,它们仍然是以实际的需要为基础,是以一定国家里的一定阶级的生活条件的总和为基础的。所以这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当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俘虏,因而看不清现实的关系。[90]
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指出,这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对“不科学的”法国人和英国人所采取的行动,就是指出他们只看到了社会发展的表面现象,属于“粗俗的”经验主义,因而首先激起德国读者们对他们的轻视,进而歌颂“德国科学”,认为只有“德国科学”才负有使命要向世界揭示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真理,揭示绝对的、“真正的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指出他们赋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那个“真理”,实际上就是企图用德国的特别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意识形态,来阐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献的思想。但是,由于他们把这类文献错误地理解为是从“纯粹的思想”中产生的,把这些共产主义体系以及批判性和论战性的共产主义著作同现实运动分裂开来,然后,又非常任意地把它们同德国哲学联系起来,把一定的、受历史条件制约的各生活领域的意识同这些领域本身割裂开来,并且用真正的、绝对的意识即德国哲学的意识的尺度来衡量这个意识。
由于“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固守“德意志意识形态”观念决定历史的思维范式,并以此去嫁接法国社会主义学说,把法国人的思想翻译成德国思想家的语言,任意捏造共产主义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也就形成了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比如他们始终把各个具体的一定的个人间的关系变为“人”的关系,他们这样来解释这些一定的个人关于他们自身关系的思想,好像这些思想是关于“人”的思想。他们离开实在的历史基础而转到思想基础上去,同时又由于他们不知道现实的关系,所以他们也就很容易用“绝对的”或者另外的思想方法虚构出幻想的联系。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种“真正的社会主义”不过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和英国、法国那些或多或少同它相近的党派在德国人的精神太空和德国人的心灵太空中的变形而已,它本身实际上是某种神秘的科学,它不是诉诸德国人的“思维着的精神”,而是诉诸德国人的“心灵”。因为它关心的既然已经不是实在的人而是“人”,所以它就丧失了一切革命热情,它就不是宣扬革命热情,而是宣扬对于人们的普遍的爱了。因此,在德国这样一个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很落后的国家,这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就不是向无产者,而是向德国人数最多的两类人即向抱有博爱幻想的小资产者以及这些小资产者的思想家——哲学家和哲学学徒呼吁。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正是由于不能摆脱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羁绊,他们才终生宣传这种“真正的社会主义”。[91]
在该卷第一章,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莱茵年鉴”(即“莱茵社会改革年鉴”)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哲学,着重分析了海尔曼·泽米希的论文《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以及“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鲁道夫·马特伊的文章《社会主义的建筑基石》。
(一)对海尔曼·泽米希唯心史观的批判
之所以在该章中首先批判海尔曼·泽米希的论文《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是因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这篇论文提出了以人道主义超越法国共产主义的粗陋性质以及费尔巴哈的哲学社会主义,因而十分自觉地、而且以强烈的自尊感表露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德国民族性质。海尔曼·泽米希认为,法国人通过政治走向共产主义,德国人通过最后变成人类学的形而上学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归根到底都消融在人道主义中了”[92],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海尔曼·泽米希在“驳倒了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后,就给我们揭示出两者的最高统一——人道主义。从这时起,我们进入了人的境地”。说什么“在人道主义中一切关于名称的争论都解决了。为什么要分什么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呢?我们都是人”[93]。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实际上是“把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变成了两种抽象的理论、两种原则以后,再给这两个对立面杜撰任何一种黑格尔式的统一,随便安上一个名称”[94]。以此来显示出一个醉心于思辨妙想的个人比法国人和德国人高明的地方。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像德国这样的国家里,由于没有其他民族所有的那种尖锐的阶级对立,许多世纪以来哲学词句都占有一定的势力,这表现在“德国人是sub specie aeterni[从永恒的观点]根据人的本质来判断一切的,而外国人却是从实际出发,根据实际存在的人们和关系来观察一切的。外国人思考和行动是为了自己所处的时代,而德国人思考和行动却是为了永恒”[95]。因而海尔曼·泽米希把“无条件的、无前提的自由”作为一种公设,然后指出,法国共产主义是同小店主国家利己主义瓦解现象的粗暴的对立,共产主义在法国没有超越这种政治上的对立,没有达到无条件的、无前提的自由。而要实现这种对立的超越,只需把这种对立想象成已被克服的就够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海尔曼·泽米希在共产主义的理解及其实现形式探求上的荒谬性,进一步指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海尔曼·泽米希虽然谈到了食利者(即工业资本家、小资本家以及游手好闲者)和无产者的对立,并在这种对立中看到了社会中存在的两极,指出:“现在我们这个社会如此野蛮化了,有些人(食利者)像野兽一样贪婪地向他人的劳动产品猛扑,让自己的固有本质由于游手好闲而腐化;这一情况的必然结果是:另一些人(无产者)被迫像机器一样地工作,他们的财产(他们固有的人的本质)之所以丧失,并不是由于游手好闲,而是由于过度的疲劳。”[96]但是他却“用神圣的哲学语言说出这种关于无产者和食利者对立的滥调,……用空洞抽象的词句表达这种幼稚的思想”,说什么其原因是食利者让自己的固有本质腐化,而这一原因又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如此野蛮化了,但为什么社会如此野蛮化了,那就得问上帝。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显然“它不是用普通的语言,而是用神圣的哲学语言说出这种关于无产者和食利者对立的滥调,不是用恰如其分的词句,而是用空洞抽象的词句表达这种幼稚的思想”[97]。
总之,“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在历史观问题上坚持了“概念、观念统治现实”的唯心主义观点,“这种真正的所有制的理论把至今存在着的一切现实的私有制只看成是一种假象,而把从这种现实的所有制中抽象出来的观念看成是这种假象的真理和现实。”[98]在他们那里“理论在这里被说成是‘生活的分裂’的原因”,认为“所有现实的分裂都是由概念的分裂所引起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既然他们充满了关于概念能够创造世界和毁灭世界这一哲学信念,他们当然也就会认为某一个人能够通过消灭某种概念而消灭生活的分裂。”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像所有德国的思想家一样,经常把文献的历史和现实的历史当作意义相同的东西混淆起来。因为他们把自己的始终非常丰富的幻想和现实等量齐观。[99]
(二)批判鲁道夫·马特伊的哲学神秘主义
在该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鲁道夫·马特伊的文章《社会主义的建筑基石》进行了批判,因为鲁道夫·马特伊在该文中提出了一个命题,认为幸福是过去几千年来的一切愿望、一切运动和一切坚持不懈的努力的最终目的,但人类的怀着自己一切愿望的心在彼岸世界找到了避难所;它把幸福移到了那里,因而带来了人间生活的一切灾难。针对这种把生活和幸福割裂开来、出现人的二重性的现象,鲁道夫·马特伊质问道:
“难道人不是像其他一切实体一样,也是来自太古世界,也是自然界的创造物吗?难道他不是由同样的物质构成的吗?不是天生就有同样的能使万物具有生活的普遍力量和特性吗?为什么他还在某个人间的彼岸世界中寻找自己的人间的幸福呢?”[100]
鲁道夫·马特伊认为,人与万物既具有“同样的普遍力量和特性”,具有统一性,同时也有着明显的区别,那就是:
“人认识自己,他具有自我意识。可是在其他生物那里,自然的本能和力量是零散地和无意识地出现的,而在人那里,这些本能和力量是结合在一起的,是具有意识的……人的本性是整个自然界的影子,自然界在这面镜子中可以认识自己。因而,如果自然界在我身上认识自己,那末我就在自然界中认识自身,在自然界的生命中认识我自己的生命,我们就是这样赋予自然界注入我们身上的东西以生命表现的。”[101]
马克思哲学认为,鲁道夫·马特伊的开场白是幼稚的哲学神秘主义的典型,他从必须消灭生活和幸福之间的二重性这样一种思想出发,而求助于自然界,并断言自然界中不存在这种二重性,人同样是自然界的物体因而人也不应当有这种二重性。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他实际上是“把自然界神秘化之后,又把人的意识神秘化,把人的意识变成被他们神秘化了的自然界的‘镜子’”[102]。
马克思和恩格斯接下来从三个方面批判了鲁道夫·马特伊所谓的社会主义的三块建筑基石。
第一,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鲁道夫·马特伊所谓的社会主义的第一块建筑基石表现为,他认同圣西门的观点,认为,“我毕生所追求的就是如何保证所有的人的天资得到最自由的发展”,为此,他首先指出人只能在总合生命的范围内,并通过总合的生命才能发展起来,并把自然界叫作“一切生命的基础”[103];其次,他把自觉的生命同不自觉的单个的生命相对立,把人类社会同自然界的普遍的生命相对立,指出:“按照自己的本性,只有在同其他人们的交往中并通过这种交往,我才能够达到自己生活的发展,才能达到对这生活的自觉的享受,才能够获得自己的幸福。”[104]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就这个建筑基石而言,他实际上把某些思想强加于自然界,想在人类社会中看到这些思想的实现。以前单个人被宣布为自然界的镜子,而现在则是整个社会被宣布为自然界的镜子,因此他满足于这种空洞的类比,却没有深入去考察社会历史的发展,把社会看成自然界的镜象,因此得出结论说,在迄今存在过的一切社会形态(也包括现代社会)中,这些生命的表现获得了充分的发展和对其合理性的承认。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因为社会毕竟还是不符合自己的原型,不符合自然界,所以“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就“要求”社会依据自然界来安排自己,并用植物来举例,说什么植物没有向自然界提出生存条件,但自然界却有着它所赖以生长的气候和地理条件,因此认为自己有权把他的个人的“独自性”作为社会机构的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上面所谈到的那种单个人对社会的要求是由形而上学的两面即个别性和普遍性的虚构的相互关系引申出来的,而不是由社会的现实发展所产生的。为此,只需要把个人宣布为个别性的代表、它的体现,而把社会宣布为普遍性的体现,整个戏法也就变成了。”[105]
第二,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了鲁道夫·马特伊所谓的社会主义的第二块建筑基石,即“宇宙的躯体就是所有的个体总合起来的无限的多样性”。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仍是关于单个的生命和总合的生命的谬论。作者就个别性和普遍性的拙劣观点,表现在他首先把这两个极端空洞的抽象概念当作两个绝对的原则摆出来,由此得出一个结论:现实中应当又有同一种关系再现。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在鲁道夫·马特伊所谓的社会主义的第二块建筑基石中,又出现了个人以及体现为社会的同个人对立的普遍物这种在第一块建筑基石中所出现的情况,但这一次却表现为个人本身分裂为特殊的本性和普遍的本性。因此,一切人所共有的关系在这里成了“人的本质”的产物、人的本性的产物,而实际上,这些关系像对于平等的意识一样是历史的产物。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现在的社会是依靠“外界的强制”的,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所理解的“外界的强制”,也不是一定的个人的带限制性的物质生活条件,而只是国家的强制,即刺刀、警察、大炮,而这些东西绝对不是社会的基础,只不过是社会本身分裂的结果而已。特别是,和现在的、“以外界的强制为基础”的社会相反,“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标榜一种“以对内在人类本性的意识即理性为基础”的理想的真正社会。因而,这种社会是以意识的意识、思维的思维为基础的。显然这在表述方法上陷入了哲学家的抽象。而实际上,不管是人们的“内在本性”,或者是人们的对这种本性的“意识”,“即”他们的“理性”,向来都是历史的产物;甚至当人们的社会在他看来是以“外界的强制”为基础的时候,他们的“内在本性”也是与这种“外界的强制”相适应的。[106]
第三,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分析了鲁道夫·马特伊所谓的社会主义的第三块建筑基石。针对鲁道夫·马特伊的如下观点:“人和自然界的斗争是以两极的对立、以我的特殊生命和自然界的普遍生命的相互作用为基础的。当这一斗争表现为自觉活动的时候,就叫作劳动。”[107]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这实际上是“先从事实得出一个抽象概念,然后宣称这个事实是以这个抽象概念为基础的”。“人和自然界的斗争被作者用这种方法神秘化了以后,人对自然界的自觉的活动也被他神秘化了,他把这种活动看成是这一现实斗争的纯粹抽象观念的表现”[108]。在结尾,劳动这个普通的字眼就被他偷用来作为这全部神秘化把戏的结果,而这个字眼一开始就在我们这位“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舌头上打转,但是只是在他给以相当的论证以后才敢于把它说出口来。劳动在这里是从关于人和自然界的纯粹抽象的观念中构想出来的。
(三)对卡尔·格律恩的批判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该卷第四章中主要围绕“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卡尔·格律恩的著作《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书信和研究》,对其思想进行了批判,因为卡尔·格律恩在该著作中把德国社会主义作为对法国社会主义的批判来加以颂扬,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只有人道主义的世界观才可能开辟通向人类未来生活的道路”。[109]因此他一方面追随费尔巴哈,认为“纯粹的、真正的人”似乎是世界历史的最终目的,宗教是异化了的人的本质,人的本质是人的本质和万物的尺度;另一方面赞同德国社会主义的其他真理,认为货币、雇佣劳动等等是人的本质的异化,认为德国社会主义是德国哲学的实现,是外国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理论真理。[110]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卡尔·格律恩的许多思想是对赫斯等人的抄袭和转述,甚至十分忠实地抄录了赫斯的明显的错误,例如赫斯认为理论体系构成实践运动的“社会背景”和“理论基础”,格律恩就写道:“18世纪政治问题的社会背景同时也是两种哲学派别的产物——感觉论者和自然神论者的产物。”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格律恩这里所蕴涵的思想是:“只要把费尔巴哈和实践联系起来,把他的学说运用到社会生活中去,就可以对现存社会进行全面的批判了。”[111]
在该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别论述了卡尔·格律恩论述圣西门主义、傅立叶主义、卡贝、蒲鲁东等人的地方所存在的对罗·施泰因等人的抄袭现象,特别论述了格律恩思想中的错误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格律恩在对圣西门主义的理解上,没有遵循年代的顺序,没有连贯地叙述事件的进程,而是把来自施泰因和雷博的所有的材料搅成一团,省略了最必要的东西,比如圣西门主义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即对现存制度的批判,就在格律恩先生的笔下完全消失了。[112]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格律恩在批判傅立叶主义的地方,大部分也是施泰因早已经较详细地叙述过的东西。在对傅立叶的批判中,格律恩首先采用了“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原理,然后又把这些原理加以夸张和歪曲,针对傅立叶所坚持的关于资本、天才和劳动之间的区分,格律恩完全不根据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现实关系来批判这种区分,因而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对于“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来说,重要的只是把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悄悄塞给每个人,并且把社会主义的各种阶段变为人的本质的各种哲学概念。这种非历史主义的抽象迫使格律恩先生宣布:内部的和外部的之间的任何差别归于消灭,从而使人的本质的继续存在受到威胁。[113]
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指出,格律恩不理解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复杂的相互关系,而是陷入了“生产和消费一致性”的庸俗的理解。说什么“消费和生产从经济学上来说应当彼此抵消,不应当有超过直接消费需要的剩余产品,如有这样情况,显然一切运动都会停止”[114]。“当他生产的时候他也在消费,即消费原料和一切生产费用;一句话,不能无中生有,人需要材料。”[115]这正好迎合了一切贵族、僧侣、食利者等等所自古以来就是这样证明说他们是生产的。其次,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格律恩看不到生产的历史发展,不了解现在生产面包是用蒸汽磨,而从前是用风力磨和水力磨,更早的时候是用手推磨;生产面包的这些不同的方式完全不取决于他吃面包这一简单的行为。格律恩甚至也没有想到,随着这些不同的生产阶段产生的还有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各种关系,以及二者之间的各种矛盾;他没有想到,如果不研究这些生产方式中的每一种方式和以此为基础的整个社会制度,就不可能了解这些矛盾,而这些矛盾只有通过这种生产方式和这种制度的实际改变,才能得到解决。[116]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为了利用需求和供给这两个概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格律恩删去了其中必要的中间环节,从而把它们变为纯粹的幻想。可见,所有这一切的中心思想仅仅是要不学无术地和空想式地把现存制度神圣化。
针对格律恩指责傅立叶以生产过剩破坏生产和消费的一致性,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他忘记了,生产过剩只是由于它影响产品的交换价值才引起危机,然而不仅在傅立叶那里,就是在格律恩所建立的那个十全十美的世界中也看不见这种交换价值。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在竞争的范围内,每个人的消费或多或少地是以一切人的不断消费为前提的,正如每个人的生产以一切人的生产为前提一样。问题只在于,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怎样发生的。格律恩仅仅用关于人的消费、关于对“消费的真正本质”的认识的道德公设来回答这个问题。由于他对于生产和消费的真实关系一无所知,所以他只好躲到“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最后避难所——人的本质——中去。因此他必然不以生产为出发点,而以消费为出发点。如果从生产出发,那么就应当考虑生产的实际条件和人们的生产活动。如果从消费出发,那么可以满足于宣称现在人们不“像人一样地”消费,满足于关于“人的消费”、关于用真正消费的精神进行教育的公设以及诸如此类的空洞词句,而丝毫不去考虑人们的现实的生活关系和他们的活动。[117]马克思和恩格斯实际上批评格律恩没有抓住法国社会主义者的本质之处(甚至在剽窃他们的时候也是如此),而是专注于一些“人的”消费的模糊不清的概念,以此反对研究真正的生产关系。[118]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以《“目光短浅的卡贝老头”和格律恩先生》为标题,从格律恩对卡贝的批评分析了格律恩思想的唯心主义实质。众所周知,卡贝是法国科学社会主义者,在他1840年发表的《伊加利亚旅行记》中,鼓吹“和平共产主义”,虽然引用了一些新旧权威人士所发表的有利于共产主义的言论,但他的目的决不在于描绘整个的历史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他是“最有声望然而也是最肤浅的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119]。格律恩虽然也看到了卡贝的目光短浅,认为他的使命早已完成,但却赋予卡贝以新的使命,从“生产性的”读书开始,用一些任意摘录的引文为格律恩式的德国18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史制造一个法国的“背景”。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格律恩实际上是用抄袭卡贝的手段,用瞎扯历史的方法,唤起法国的劳动组织者对自己的本质的意识,并且按照分而治之的原则行动。
在该章的最后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指出了,在谈到蒲鲁东的地方,格律恩只是逐字抄录了《神圣家族》中对蒲鲁东所提出的批评意见。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蒲鲁东的系列辩证法,实际上是试图提供一种思维方法,这种方法将以思维的过程来代替各个单独的思想,实际上是从法国人的观点出发,寻求和黑格尔所提出的辩证法相似的方法。但格律恩并没有去批判蒲鲁东的辩证法,而是宣布蒲鲁东及其整个的系列辩证法只不过是假装学者,因而未能抓住蒲鲁东思想的本质。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提到格律恩时,称他为“德国哲学的一位教师,有一个超过我的优点,即他本人对德国哲学一无所知”[120]。
(四)对唯灵论的骗子——库尔曼博士的批判
应该说明的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第五章《“霍尔施坦的格奥尔格·库尔曼博士”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预言》是由魏德迈手抄的,在最后标有“莫·赫斯”的记号。大概这一章是赫斯起草的,魏德迈抄写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校订的。
在这一章中,作者认为替天行道的库尔曼博士根本不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而是一个唯灵论的骗子,一个笃信宗教的骗子,一个神秘主义的滑头,“一个冒牌的弥赛亚式的共产主义的瑞士传教士”[121]。作者在该章中还明确指出了一切唯心主义者的特征:“一切唯心主义者,不论是哲学上的还是宗教上的,不论是旧的还是新的,都相信灵感、启示、救世主、奇迹创造者,至于这种信仰是采取粗野的、宗教的形式还是文明的哲学的形式,这仅仅取决于他们的教育程度。”[122]作者指出实际上对唯心主义者来说,“现实不过是现实事件的理论抽象,不过是这些事件的观念象征,而现实事件只不过是‘旧世界走向灭亡的象征’”[123]。因而在唯心主义者看来,任何改造世界的运动只存在于某个上帝特选的人的头脑中,整个历史发展都归结为历史发展进程在“当代所有的哲学家和理论家”的“头脑”中形成的理论抽象,既然不可能为了“议论和表决”而把这些“头脑”“集合在一起”,那么就必须有一个作为所有这些哲学家和神学家的头脑的顶峰、这些头脑的锋芒的神圣的头脑,这个顶峰的、锐利的头脑就是各个愚钝的头脑的思辨的统一,就是救世主。[124]
作者认为,库尔曼博士始终坚持“观念的社会是世界。而这些观念的统一支配和统治着世界”[125],这是他毫不费力地克服了一切现实的障碍,把一切现实的物变成了观念,并宣布自己是它们的思辨的统一,因此他才有能力“统治和支配”它们的结果。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最后,还附有恩格斯的著作《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它作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的直接继续。恩格斯在该著中主要批评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如下三个支派:其一是威斯特伐利亚社会主义派,该派以海尔曼·克利盖、尤利乌斯·海尔米希、鲁道夫·雷姆佩尔、尤里乌斯·迈耶尔、约瑟夫·魏德迈、奥托·吕宁等为代表;其二是萨克森派,该派以泽米希、阿尔弗勒德·迈斯纳、卡尔·穆尔、摩里茨·哈特曼等为代表;其三是柏林派,以恩斯特·德朗克、德里希·扎斯为代表。该部分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真正的社会主义》这一章的重新修改和增订,因为1847年初“真正的社会主义”在总流派范围内发展成了各种派别,根据形势的需要恩格斯才打算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各个派别。该部分约写于1847年1月至4月,从流传下来的该部分手稿来判断,这部著作属于未完成稿。[126]关于这一部分的写作背景,恩格斯曾经写道:从写好上述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评论到现在,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了。在此期间,过去只是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零星出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已经蓬勃地发展起来。它在祖国的每一个角落都有自己的代表,甚至一跃而成为文坛上有一定影响的流派。而且现在它本身已分裂成许多支派,虽然各个支派被德国人的诚恳和科学精神的共同纽带,被共同的意向和共同的目的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彼此仍有显著的不同,因为各派具有各自独特的个性。因此,用格律恩先生风雅的语言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一团混乱的光”变成了“井然有序的光”;这一团光凝聚成了星星和星座,在它们柔和的光辉里,德国市民可以无忧无虑地沉溺于他们那种正直获得小量财产的计划,沉溺于他们希望国民中各下层阶级的地位有所提高的幻想。[127]恩格斯正是为了与上述“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各个最发达的支派真正分手,才对上述各个流派预先进行仔细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