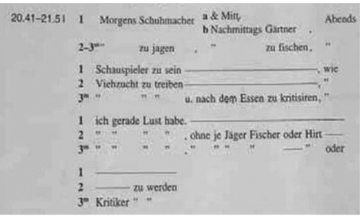三、对布鲁诺·鲍威尔和麦克斯·施蒂纳观点的逐条批判
如前所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的直接原因,就是因为1845年在莱比锡出版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杂志《维干德季刊》第3卷上,发表了布鲁诺·鲍威尔和麦克斯·施蒂纳反驳费尔巴哈、赫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正面阐述之后,对青年黑格尔派中的布鲁诺·鲍威尔和麦克斯·施蒂纳的观点进行逐条批判,在此过程中进一步揭露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实质,彰显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一)对布鲁诺·鲍威尔的批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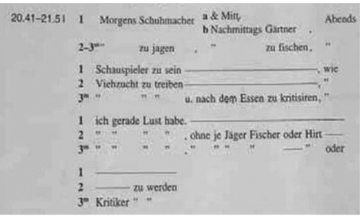
《德意志意识形态》新MEGA先行版第17页手稿对修改过程的记录
在第一卷第二章“圣布鲁诺”中,马克思分别从(1)“征讨”费尔巴哈;(2)圣布鲁诺对费尔巴哈和施蒂纳之间的斗争的思考;(3)圣布鲁诺反对“神圣家族”的作者;(4)与“莫·赫斯”的诀别等四个部分,批判了布鲁诺·鲍威尔的唯心主义观点。
(1)在关于布鲁诺“征讨”费尔巴哈这部分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黑格尔以歪曲的形式反映现实冲突的那种抽象的和神秘的词句,在布鲁诺·鲍威尔看来就是现实冲突本身,因而他接受了思辨的矛盾,并把这个矛盾的一部分同另一部分对立起来。他还抄袭费尔巴哈关于哲学的定义,认为“哲学总不外是还原为自己的最一般的形式、最合理的表达方式的神学”。布鲁诺的“哲学”就是“要求”“人消融”于他的一种“偶性”的观念,即消融于作为“实体”的自我意识的观念之中,因而布鲁诺·鲍威尔并没有离开思辨的基地来解决思辨的矛盾。这突出表现在:由于在他看来,关于现实问题的哲学词句就是现实问题本身。因此,他认为:“一方面,现实的人以及他们对于从外表上看是独立在外而和他们对立的他们自己的社会关系的现实意识都非实有,实有的只是自我意识这种赤裸裸的抽象词句,正如现实的生产都非实有,实有的只是这种自我意识的已经独立化的活动一样;另一方面,现实的自然界和现实存在的社会关系都非实有,实有的只是这些关系的一切哲学范畴或名称归结而成的赤裸裸的哲学词句,即实体”[61]。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布鲁诺实际上同所有哲学家和思想家一起,错误地把思想、观念、现存世界在思想上的独立化了的表现当作这个现存世界的基础,用这两个已变得毫无意义和毫无内容的抽象,他就能够变各式各样的戏法,而对现实的人及其各种关系则一无所知。
针对布鲁诺·鲍威尔对费尔巴哈的批判,马克思分别从如下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并指出了布鲁诺·鲍威尔的唯心主义错误实质:
其一,针对布鲁诺·鲍威尔把费尔巴哈所说的类和黑格尔的绝对等同起来,认为它同样是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的。马克思认为布鲁诺实际上是使个人的现实关系依赖于对这些关系的哲学解释。
其二,布鲁诺·鲍威尔认为费尔巴哈用来把理性、爱和意志所构成的上帝的三位一体变成某种“在个人之中并统治着个人”的东西,指出这种异端邪说是极其丑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费尔巴哈的错误不在于他说出了这一事实,而在于他以唯心主义的方式使之独立化了,没有把它看作是历史发展的一定的、暂时的阶段的产物。
其三,布鲁诺·鲍威尔反对费尔巴哈的“感性”,认为感性就是色欲、肉欲和傲慢,特别是按照《圣经》上的解释,肉欲的事情就是通奸、奸淫、污秽、淫乱、偶像崇拜、迷惑、敌视、争吵、嫉妒、愤怒、纠纷、不睦、成群结党、仇恨、谋杀、酗酒、饕餮等等。布鲁诺认为,肉欲的思念就是死亡,而精神的思念就是生命与和平;肉欲的思念是对批判的敌视,而一切肉欲的东西都是从尘世产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思念神灵而又憎恶肉欲的罪恶外衣的布鲁诺认为费尔巴哈把人这个词变成空洞的字眼,不是制造和创造完整的人,而是把全人类奉为绝对,指责费尔巴哈不是把人类而是把感觉说成是绝对物的器官,认为感性的事物,是绝对的、毋庸置疑的、完全确实的东西,因此诅咒费尔巴哈,认为他是暴徒的首领,将他摈于门外,使之与恶犬、妖术者、通奸者和杀人犯为伍,但布鲁诺完全不是反对费尔巴哈用以承认感性的那种极端有限的方法。
布鲁诺·鲍威尔认为费尔巴哈既是一个被人道主义鼓舞又败坏了的唯物主义者,也就是忍受不住尘世以及尘世的存在但想化为精神而升天的唯物主义者;又是这样一个不能思考也不能建立精神世界,而被唯物主义所累的人道主义者。布鲁诺·鲍威尔认为人道主义就在于“思考”和“建立精神世界”,而唯物主义者“只承认当前现实的东西,即物质,承认它是积极地展示自己并实现自己的多样性的东西,是自然”。[62]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布鲁诺·鲍威尔错误地把一些唯物主义者关于物质的哲学词句当作他们世界观的真实的核心和内容了。
(2)在关于圣布鲁诺对费尔巴哈和施蒂纳之间的斗争的思考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布鲁诺为了驳倒费尔巴哈和施蒂纳,采用了分而治之的办法,让他们自己发生争执,使费尔巴哈的人和施蒂纳对立,又使施蒂纳的唯一者和费尔巴哈对立,然后宣布势不两立的双方把对方消灭的剩余部分为实体,进而认为它应当永远受诅咒。
(3)在圣布鲁诺反对《神圣家族》的作者部分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圣布鲁诺把《神圣家族》序言中所找到的“真正的人道主义”这个用语,作为了自身假设的主要根据。
(4)在与“莫·赫斯”的诀别部分中,圣布鲁诺指责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完成对施蒂纳的批判,而赫斯却正在完成这项工作,但又同时指责赫斯在某些地方没有了解费尔巴哈,且由于使用了“联合的”和“发展”这两个字眼,因此抄袭了黑格尔。马克思认为圣布鲁诺对费尔巴哈和施蒂纳的批判,是“通过自身、在自身中并与自身一起”完成的,因为他就是“他自身”,此外,他“通过自身、在自身中并与自身一起”“永远是最伟大的并且能是最伟大的”。
(二)对麦克斯·施蒂纳的批判
在该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结合麦克斯·施蒂纳的著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对施蒂纳的唯心主义进行了批判。施蒂纳在其著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采用了任意编造的手法,宣扬对精神力量的信仰,大量引用《圣经》中有关精神统治世界的无稽之谈。所以,在该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本书看成和《圣经》一样的东西,在批判过程中用“旧约”、“新约”、“创世记”、“启示录”、“所罗门的雅歌”等等《圣经》上的标题来称呼该书的相应部分,而且也引用许多《圣经》里的话来讽刺和嘲笑施蒂纳。[63]
施蒂纳在其著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大力宣扬利己主义,宣称“我就是我的一切,这个我就是唯一者”,主张超越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唯一者”——“自我”是世界的本源,是唯一的实在,而宗教、国家、道德、财产乃至整个世界及其历史都是“自我”的产物,说什么“神的事”、“人类的事”都是“纯粹利己主义的事”;无论是“神”或“人类”,都只关心自己的事;“真理、自由、人道、正义”“只关心自己,不关心我们,只关心自己的福利,不关心我们的福利”,进而指出:“从我这方面来说,我由此取得教训,我不再为这些伟大的利己主义者服务了,最好自己成为利己主义者吧!”[64]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使施蒂纳转向利己主义的动机,不是现世的财物,不是会被虫子咬坏或锈坏的财宝,不是他的唯一者同道们的资产,而是天上的宝物、神的资产、真理、自由、人类等等。施蒂纳和“神”、“真理”相竞争,他依靠的是自己——“我,这个我完全和神一样是一切他物的无,这个我就是我的一切,这个我就是唯一者……我是空洞无物意义上的无,而是创造性的无,是作为创造者的我自己所赖以创造一切的这个无。”[65]
他将世界作为他心目中的世界,把世界当作自己关于世界的观念来把握,把所有这一切表达为一句无与伦比的话:“我把一切都归于我。”认为除他之外任何世俗力量都没有力量驾驭精神,精神是世上的最高力量,而他却征服了这万能的精神。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施蒂纳所摧毁的只是“青年”头颅中的“祖国”等等思想所具有的幻想的怪影般的形象,他根本还没有触及这些思想,因为这些思想是表达现实关系的。[66]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一部分“人的生活”中包含着唯一者的全部家政的萌芽,它向我们提供了直到最后时刻、世界末日来临之际的整个后来发展的原型:唯一者的全部历史围绕着儿童、青年和成人这三个阶段兜圈子,这三个阶段又具有“各种转变”,兜着愈来愈大的圈子,最后直到事物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全部历史被归结为“儿童、青年和成人”为止。施蒂纳对历史的发展阶段作了如下命名:儿童依赖于事物,其基础是唯实主义;青年依赖于思想,其基础是唯心主义;成人则是否定的统一,统一为利己主义。他指出,唯实主义的利己主义者是通常理解的利己主义者,其表现是儿童和黑人;唯心主义的利己主义者是自我牺牲者,其表现是青年和蒙古人;而真正的利己主义者是唯一者,其表现是成人和高加索人。[67]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施蒂纳的这种编造历史的方法是最幼稚的、最简单的,表现在作为儿童、青年和成人而出现于我们之前的三个简单范畴,即唯实主义、唯心主义和作为两者的统一的绝对否定(这里称为“利己主义”),被当作全部历史的基础,并挂上各种各样的历史招牌;这些范畴和它们的恭顺的随员即辅助范畴一起,构成所描绘的一切伪历史的阶段的内容。[68]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这种唯心史观的根源在于,正如德国的哲学的历史观,实际上在施蒂纳这里“思辨的观念、抽象的观点变成了历史的动力,因此历史也就变成了单纯的哲学史。这种哲学史不是根据现有材料所载的真实面貌来理解的,历史便成为单纯的先入之见的历史,成为关于精神和怪影的神话,而构成这些神话的基础的真实的经验的历史,却仅仅被利用来赋予这些怪影以形体,从中借用一些必要的名称来把这些怪影装点得仿佛真有实在性似的”[69]。
马克思着重指出了施蒂纳在对观念、意志与现实生活和现实关系之关系上的颠倒。
其一,在对宗教产生原因的分析上,施蒂纳仅仅从宗教的自身原因去加以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使人们满足于精神史的观点本身就是宗教的观点,因而应当从经验条件去解释宗教,重要的是要说明:“一定的工业关系和交往关系如何必然地和一定的社会形式,从而和一定的国家形式以及一定的宗教意识形式相联系。”[70]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宗教本身既无本质也无王国。在宗教中,人们把自己的经验世界变成一种只是在思想中的、想象中的本质,这个本质作为某种异物与人们对立着。这决不是又可以用其他概念,用‘自我意识’以及诸如此类的胡言乱语来解释的,而是应该用一向存在的生产和交往的方式来解释的。这种生产和交往的方式也是不以纯粹概念为转移的,就像自动纺机的发明和铁路的使用不以黑格尔哲学为转移一样。如果他真的想谈宗教的‘本质’即谈这一虚构的本质的物质基础,那么,他就应该既不在‘人的本质’中,也不在上帝的宾词中去寻找这个本质,而只有到宗教的每个发展阶段的现成物质世界中去寻找这个本质。”[71]
其二,马克思指出了施蒂纳关于下列命题的错误。这个命题是:“由人这个概念得出的真理,被神圣地奉为这一概念的启示”;“这个神圣概念的启示”,即使“在靠这一概念揭示出来的真理被取消时,也不会失去自己的神圣性”。针对上述命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实际上决不是人这个神圣概念,而是处在现实交往中的现实的人创造了经验关系,只是在后来,在事后,人们才把这些关系虚构、描绘、想象、肯定、确认为“人”这一概念的启示。[72]
特别是针对施蒂纳所始终坚持的“改变现存的关系仅仅取决于人们的善良意志,现存的关系就是一些观念”的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哲学家们那样当作职业,也就是当作行业来从事的那种与现存关系脱节了的意识的变化,其本身就是现存条件的产物,是和现存条件不可分离的。这种在观念上的超出世界而奋起的情形就是哲学家们面对世界的无能为力在思想上的表现。他们的思想上的吹牛每天都被实践所揭穿。”[73]
其三,在上述分析基础上指出了施蒂纳在人的解放途径上的荒谬性。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施蒂纳真正相信意识形态的各种抽象思想统治着现代世界,深信他在其反对“宾词”、反对概念的斗争中攻击的已不是幻想,而是统治世界的现实力量。[74]说什么“在他对其他人的全部关系中,重要的并不是现实的关系,重要的是每个人能把自己想象为什么和在自己的反思中是什么”[75]。因而人们由于现实的生活条件而与自身或他人发生的冲突,在施蒂纳看来就是人们同关于“人”的生活的观念之间的冲突。[76]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施蒂纳对法的全部批判只限于把法律关系的文明的表现和文明的分工说成是“固定观念”、圣物的果实,对于他来说,全部问题只在于名称;至于问题本身他丝毫没有接触到,因为他不知道法的这些不同形式所赖以产生的现实关系,因为他只是把阶级关系在法律上的表现看作是过去野蛮关系观念化了的名称。[77]
施蒂纳“宣称合法的财产是私有财产的基础,而法的概念又是合法的财产的基础,于是他就可以把他的全部批判局限于宣称法的概念是概念,是怪影”[78]。因此在人的解放的途径上,由于施蒂纳幻想人们仅仅由于观念和概念占着统治地位而迄今仍旧坠入灾难的深渊,所以他认为“只要把某些观念从头脑中挤出去,……就可以把现在已被认为非人的那些现实关系消灭掉,至于‘非人的’这个宾词是与自身的关系相矛盾的个人所具有的判断,还是占统治地位的现存社会对该社会范围以外的被统治阶级的判断,这都是没有区别的。”[79]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要消灭关系对个人的独立化、个性对偶然性的屈从、个人的私人关系对共同的阶级关系的屈从等等,归根到底都要取决于分工的消灭。”[80]而这要通过现实的力量,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手段才能得以实现。
总之,通过逐条批判布鲁诺·鲍威尔和麦克斯·施蒂纳的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在《维干德季刊》1845年第3卷中发生的这场圣战,不是为了关税、宪法、马铃薯病,不是为了银行事务和铁路等这些现实问题,而是为了精神的最神圣的利益,为了“实体”、“自我意识”、“批判”、“唯一者”和“真正的人”。其中,布鲁诺·鲍威尔披着“自我意识”的法衣,睥睨世界的万物。他以最高的自我意识的名义肆意摆布“实体”概念,摧毁了完整的宗教和具有各种表现的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他是精神的“拿破仑”,他仅仅在精神上是“拿破仑”。而麦克斯·施蒂纳用了将近六百页的篇幅来确定和证明了他与自身的同一,说什么“我就是一切,而且是高于一切的某物。我是这种无的一切,也是这种一切的无”[81]。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他们都陷入了精神哲学和意识哲学的泥淖。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分析了青年黑格尔派意识哲学产生的根源,指出由于“黑格尔哲学把一切变为思想、圣物、幽灵、精神、精灵、怪影”[82]。历史在黑格尔看来是诸精神的历史,他把精神的概念作为基础,然后指出历史是精神本身的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凡是照黑格尔这样理解历史的人,到最后都不得不达到作为全部以往历史的结果的、在思辨哲学中才完成和就绪的诸精神王国。[83]特别是“人们在其中生产自己生活的并且不以他们为转移的条件,与这些条件相联系的必然的交往形式以及由这一切所决定的个人的关系和社会的关系,当它们以思想表现出来的时候,就不能不采取观念条件和必然关系的形式,即在意识中表现为从一般人的概念中、从人的本质中、从人的本性中、从人自身中产生的规定。人们是什么,人们的关系是什么,这种情况反映在意识中就是关于人自身、关于人的生存方式或关于人的最切近的逻辑规定的观念。于是,在思想家们假定观念和思想支配着迄今的历史,假定这些观念和思想的历史就是迄今存在的唯一的历史之后,在他们设想现实的关系要顺应人自身及其观念的关系,亦即顺应逻辑规定之后,在他们根本把人们关于自身的意识的历史变为人们的现实的历史的基础之后,——在所有这一切之后,把意识、观念、圣物、固定观念的历史称为‘人’的历史并用这种历史来偷换现实的历史,这是最容易不过的了”[84]。
青年黑格尔派忽视了历史的现实基础,看不到实践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基础作用,“错误地把思想、观念、现存世界在思想上的独立化了的表现当作这个现存世界的基础”[85],因而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就此而言,马克思哲学指出,就黑格尔以歪曲的形式反映现实冲突的那种抽象的和神秘的词句,在布鲁诺·鲍威尔看来就是现实冲突本身,认为关于现实问题的哲学词句就是现实问题本身,历史是精神本身的过程,这必然使得他对现实的人及其各种关系一无所知,导致他们未能离开思辨的基地来解决思辨的矛盾。[86]
因为对于施蒂纳来说,“在他对其他人的全部关系中,重要的并不是现实的关系,重要的是每个人能把自己想象为什么和在自己的反思中是什么”[87]。因此在如何实现人的解放的问题上,施蒂纳认为,人们摆脱这些力量是靠人们把关于这些力量的观念,正确些说,把对于这些观念的哲学的和宗教的歪曲从自己的头脑中挤出去——或用同源词的办法(【能力、资产】和【有能力、有资产】),或用道德公设(例如,但愿你们每个人都成为万能的“我”),或用各色鬼脸怪相以及诙谐的夸张来反对“圣物”的办法。[88]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显然对现实的人的解放不会产生任何实质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