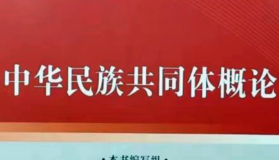发生于755年至763年的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正如陈寅恪所说:“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格局,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安史之乱后,唐朝包容开放的“天下观”有所收缩内敛。这对此后中国宋代思想文化产生了影响。然而,盛唐的恢宏气象与灿烂文化所造就的盛世记忆却难以磨灭,成为文化基因,融入周边族群的血液之中,其流风余韵继续在周边族群散播、发挥影响。周边族群继续沿用唐朝的制度、语言文字与风俗文化,使盛唐文明在边疆地区深入扎根,为辽宋夏金时期边疆地区中华文化的深度发展与族群交融打下坚实的基础。
从开元之治到天宝时期,唐朝内部出现威胁政权稳定的暗流,朝廷内外奢靡腐败,均田制和租庸调制逐渐崩坏,边疆军事体制出现“内轻外重”的问题。为应对周边强大的部族,边疆节度使手握强兵、盘踞一方。“猛将精兵,皆聚于西北”,中央(京畿)的防守力量严重不足。唐玄宗以募兵制代替府兵制,士兵们只知道地方将帅,不知道皇帝和朝廷。在此情况之下,唐朝不得不倚重胡人蕃将充任边防大将,借重军事力量强大的胡人部族军队维护边疆地区稳定。
开元初(713)以后,粟特人从河西走廊一带迁徙到东突厥政权所处的漠北,再从漠北进入营州地区。由此,在开元、天宝前后,该地区形成一个相当规模的粟特聚落。唐朝正是要利用这些善战的粟特胡人,防范契丹与奚这两个强蕃。安禄山是粟特和突厥的混血儿,他在和东北两蕃的战斗中成长起来。为应对愈加严峻的边疆危机,唐朝在边疆地区开始任命胡人出身的将领出任节度使以震慑边疆诸族,即所谓“欲以方镇御四夷”。安禄山、史思明等蕃将受到重用。
安禄山发现朝廷的腐败与京畿防守的空虚后,萌生叛乱野心,以胡将代替汉将,招募和网罗奚、契丹、同罗等部族壮士8000人作为义子。其密友史思明既是同乡,也出身杂胡(粟特人)。安禄山于天宝十四载(755)在范阳起兵,史思明配合,安史之乱爆发。天下太平已久,百姓累世不识兵戈.忽然遭逢如此强力冲击,一些州县不战而败。叛军一路攻破洛阳,打破潼关占领长安。
唐肃宗率唐军开始反攻,逐渐收复洛阳和长安。为平息安史之乱,郭子仪建议唐肃宗向回纥借兵。回纥出兵助唐前后共四次.其中三次直接与叛军交战,对平定叛乱起到重要作用。
叛乱虽然被平定,却遗留下了藩镇割据的问题。位于河朔地带的河北三镇不仅不朝贡,甚至拥兵独立实行内部自擅,主要由原安史旧将控制,具有非常强的独立性,是真正割据型的藩镇,俨然化外之地。其中也有一些汉人藩镇,它们的形成过程与职能不同于“河朔型”藩镇(即河北三镇等),主要包括承担防御河北三镇、护卫唐廷安全、保护东南漕运责任的“中原防遏型”藩镇,为防御吐蕃、西南西北少数族群而设立的“边疆御边型”藩镇与为唐朝提供赋税来源的“东南财源型”藩镇。这些藩镇均由唐玄宗时期设置的节度使转化而来,或者是因平叛有功或自立为王而被唐朝封为节度使。于是“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但也正是因为有其他三类藩镇的存在,唐朝才能在安史之乱后,依然延续约150年。
对于安史之乱的成因,从古至今讨论不断。由于安、史二人的胡人身份以及叛军队伍中的边疆诸族成分,一些意见将其归结为族群矛盾与河北地区胡化问题,认为是“羯胡乱常”。安史之乱中确实存在一定的族群因素,但更多是不合理的政治军事因素。一方面,虽然安禄山、史思明来自边疆诸族,但其阵营中也有不少汉人,如严庄、高尚、张通儒。另一方面,保卫唐朝与安史作战的名将很多也是胡人,如高句丽人高仙芝、突厥突骑施人哥舒翰、契丹人李光弼、铁勒人仆固怀恩;在前线奋勇杀敌的唐军士兵也来自诸族。在平叛过程中,还有于阗王尉迟胜亲率五千于阅子弟不远万里“助国讨贼”的故事,传为佳话。再从更长时段观察,安史之乱后割据的藩镇势力既有胡人也有汉人,如田承嗣、田悦、朱滔、刘悟、李纳等都是汉人。所以单独以族群划分阵营是错误的,安史之乱真正揭示出中华民族发展的一条基本规律:当大一统体制破败、中央政权紊乱时,各种类型的反叛都可能出现,只是时间早晚而已。要实现民族不可散,首先要实现国家不可乱;要实现国家不可乱,首要是维护大一统体制不可变。
安史之乱给唐朝造成了文化创伤和心理阴影,唐后期对唐前中期的“文化开放、民族开放”政策出现反思和质疑。无论是士大夫群体还是民间百姓,“严夷夏之防”心理开始冒头。一方面,士大夫群体开始重新强调边疆诸族的差异性,白居易、元稹等诗人的作品流露出盛世难再的恐慌与防范异族的忧思,如“天宝欲末胡欲乱,胡人献女能胡旋。旋得明王不觉迷,妖胡奄到长生殿”。另一方面,文化精英对外来宗教的包容度下降。唐初,儒家并不占主导地位,佛教、道教赢得了重要的文化地位。安史之乱后,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士大夫发动唐代古文运动,希望借此“尊王攘夷”。韩愈更是高倡儒家道统论,视佛教为夷狄之法而排斥。晚唐一度出现了灭佛运动,随之消失的还有景教、袄教等外来宗教。这些都暂时使中华文化呈内向收缩态势,但持续一段时间后“华夷一体”思潮仍又重新回归主流。这之中的教训与启示是:稳定的大一统体制是多元文化繁荣的保障;一旦大一统体制受到破坏,社会就会失去开放包容的空间,多元文化势必受到损害。无论哪个族群,无论哪种文化,都要首先维护好大一统体制,然后才能实现自身的发展与繁荣。
唐朝末年,宦官专权,政治腐败,藩镇割据。在自然灾害和沉重的徭役赋税双重压迫下,爆发了黄巢起义,给了唐王朝最后致命一击,五代十国时期开始。
五代十国是唐代藩镇割据向统一局面发展的过渡期,诸多制度体系仍旧延续了唐代遗风。各政权在建立、发展的过程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接受并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包括政治文化、礼仪制度等。如出身沙陀族的后唐庄宗李存勖即位后曾明确宣布:“盖前王之令典,为历代之通规。必按旧章,以令多士”,表明继承唐朝;后晋高祖石敬瑭在依照后唐体制的基础上,“御文明殿受朝贺,用唐礼乐”,对唐王朝的礼乐加以承袭。
北方政权多吸收中央与地方官制设置,如沿用三省六部制,只是在“三省”长官上稍有变化。在经济制度上,仍旧以取代租庸调制的“两税法”为主;在选官制度上,继承了唐代科举制。在社会文化上,北方出现胡汉语境“消解”的局面,族群差异淡化。为了继承唐朝政治遗产,沙陀人李存勖直接采用大唐国号,史称“后唐”,甚至使用李唐年号。与北方相比,南方社会环境较为稳定,社会文化发展较为迅速,如吴越、南唐,文艺盛极一时。为了追求正统,南唐李界自称为唐宪宗之后,仍旧以“唐”为国号。
唐作为政治实体消亡了,但作为文化共同体,给周边族群留下了永恒的文化印记。西州回鹘、党项等政权在交通水利、建筑设计、医药文化等方面仍旧沿袭着唐代风范。唐五代时期,孔子已在藏文化中成为重要“神灵”。在苯教文献中,孔子被改造成“圣、神、王”三位一体的“贡则楚吉杰布”,是苯教的四大护法师之一,也是苯教教主的岳父。藏传佛教则把贡则楚吉杰布看作文殊菩萨化身或弟子。虽然与孔子的本来有差距,但反映了藏人对孔子的尊崇,是汉藏人民共享的文化符号。
五代初期,为躲避战争,中原汉人北迁进入契丹境内,对契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契丹在政治制度上学习中原汉制,为安抚北迁汉人,专门设立“汉儿司”,同时在韩延徽等汉人帮助下,兴建城郭、开垦土地。在丧葬、建筑、绘画上,也有唐代遗风。
文字是文明的载体,作为聚合东亚的重要纽带,汉字在唐朝崩溃后仍在周边各族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唐朝时期,契丹人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契丹与唐朝交往使用的是汉字。契丹立国后才在辽神册五年(920),参照汉字,在汉字的基础上添加笔画创制契丹大字3000余字。汉字在南诏是通行文字,这可见于现存的
唐袁滋题记摩崖石刻等。南诏的通用语言是与唐代中原汉语无大差别的白语,仅“名物或与汉不同”(例如白语“震旦”“元”“昶”即汉语的“天子”“朕”“臣”)。唐人樊绰认为“言语音白蛮最正”,即与唐代中原语音最接近。南诏还参照汉字创造了记录白蛮语言的文字(借用汉字或参考汉字结构自造新字),称为“白文”。所谓白文就是用汉字写白语、读白音、解白义。唐朝灭亡后,高昌回鹘完好地保存了吐鲁番盆地的唐朝文化遗产。其名称回鹘文“Qocho”即对汉语“高昌”的音译。又如回鹊文中的墨(maka)、笔(bir)、卷(kuin)都是来自汉语的借词;回鹘人将和尚称为“toyin”,这是对汉语“道人”的音转;回鹘王在节日里坐的精致台座叫“tauchang”,这是对汉语“道场”的音转。
小结
隋唐王朝将疆域从农耕区扩展至游牧区,将边疆之地成功纳入中华一体的秩序,使更大范围的周边族群对中央王朝产生了向心力与认同感。这一时期,各族交往交流交融在政治上主要表现为天下共主、农牧一体、华夷一家和胡汉无差,呈现出“多族群大一统”的特征。同时,由于大一统王朝疆域的空前扩大,不同区域和族群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加速了中原与周边社会的发展。大唐王朝以极为自信的态度主动吸纳域外文化,除旧布新,将自身的成就无所保留地展现在世人眼前,这一时期的绚烂文化是各族人民共同书写的精彩华章。
然而,唐朝后期中央政府权力衰落,各族群贵族和地方豪强趁机崛起,各自拥兵自重,民不聊生,进而造成大规模农民起义。907年,唐朝在动乱中灭亡了,中原地区继之而起的是五代十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转入低谷,但社会中仍保持着隋唐以来各族融合的基调。之后,是赵宋建政中原,周边的契丹、党项、女真、高昌回鹘诸族同样建立了多个政权与之并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