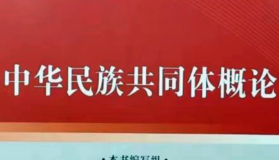-
1 授课视频
-
2 章节测验
人类社会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也正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随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已经越来越难以应对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国际局势,改革已是大势所趋。
近代世界体系的突出特征是民族国家的主权建构与帝国化演变,由此逐步形成西方所谓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这一秩序以所谓“普世文明”标准自居,实际上奉行西方中心主义,歧视其他文明及其秩序模式并凌驾其上,企图建构和维系一种霸权性质的全球治理秩序。世界体系的现代史,一定程度上就是民族国家的形成史与扩张史,其中包含了民族国家与帝国之间的“互嵌式建构”过程。
从15世纪末开始的“地理大发现”以来的历史,是西方崛起的历史。在约五个世纪的历史时段里,先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崛起,后是由英国、美国建立全球霸权秩序。1648年,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各交战国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开创了近代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的先河,逐步形成了基督教文明内部相互承认主权的法理体系。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及其现代性制度创制,逐步孕育出“英格兰现代性”,此后英国通过一系列殖民战争,一度成为现代世界的普遍知识和制度样本。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打破了欧洲均势,以法国思想为代表的欧洲大陆的现代性思想,与以英国思想为代表的有海洋背景的现代性思想构成竞争互动关系,整体提升了西方式现代化的思想内涵与制度创造力。法国战败后由战胜国建立和维持的1815年“维也纳体系”,是一个由少数大国操纵的强权政治体系。大国协调与列强共治成为19世纪国际政治的主流。
20世纪前半段,全球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本质上是列强支配体系,中国的主权权益得不到国际法的有效保护,世界诸多民族仍处于殖民统治之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雅尔塔体系及联合国国际法框架,在主权平等、安全治理与人权保护方面有重要进步,但冷战加剧了两极对峙的紧张状态,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威胁人类和平与发展,地缘政治冲突此起彼伏。冷战结束后,美国加速推进全球战略,努力建立起单极独霸地位;世界出现多极化趋势,倡导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新思想和新运动不断涌现。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力量对比。2022年,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总值总量,按现价美元计算,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约为42.55%,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则占比为58.26%,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2010年以来,中国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经济总量和发展质量上进一步接近美国,实现了十几亿人口规模的全面小康,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从长时段的世界史看,东西方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主导国际社会的西方霸权秩序日益衰落,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西方国家将中国视为“主要对手”,实行所谓的“脱钩断链”“去风险化”,全球治理面临挑战,人类文明发展呼唤新思维和新路径。
西方民族国家建构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设,具有文明和历史逻辑层面的重要区别,展现出了不同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从政党治理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彰显了一种协商合作型的政党文明新形态。立党为公与协商于民、协商为民的政党文明精神,凸显中国政党制度的优越性。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代表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引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根植于中国古典的天下为公理念和贤能政治传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发展成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西方政党是特权阶层或利益集团的代表,服务于部分人的利益,其推动的立法和政策偏向于更强势的利益集团,不能成为公共利益的可靠代表和受托人。西方的选举受到资本和舆论的严重操纵和引导,民众的真实意见与利益诉求被遮蔽甚至扭曲。
从民主治理看,中国实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民主过程各要素、各环节的充分理性沟通,最广泛地反映民意,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识,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包含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在内的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始终面向人民的公共意志,真正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西方实行票决民主,选民意愿和利益在选举之外被隔离和消声,民主变成了“金主”操控和代理人游戏。当代西方社会还出现了显著的选举疲劳症、低投票率等现象,弱势群体与分散群体的政治疏离感和失败感不断增加。
从法治实践看,中国实行依法治国,探索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有机融贯,注重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一致,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推崇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注重法律系统与政治、道德、社会诸系统的伦理协调与功能互济,追求整体化的治理效果和人民的认同。西方实行分权制衡和司法独立,法治运行高度形式化,法律制度越来越复杂,律师集团越来越庞大,诉讼成本越来越高昂,普通民众与司法正义的距离越来越遥远。西方的法治与司法甚至成为西方霸权滥施“长臂管辖”的制度帮凶,出现了双重标准现象和法治公信力的下滑趋势。
从社会治理看,中国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继承发展了“家国同构”传统,西方民族国家以原子化的市民社会为结构特征。因此,中国社会更为妥善地平衡个性发展与集体团结,更加重视合作协同;西方民族国家极端推崇个人至上,更加强调独立竞争。中国社会始终重视责任伦理;西方民族国家片面强调个人权利。中国社会更加强调族群多元基础上的社会有机整合;西方民族国家更加倾向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二元对立。
从宗教治理看,中华文明早就形成了礼乐文化和世俗秩序。中国历史上实行政主教从、多元通和,宗教中国化成为宗教治理的主导趋势,不同信仰的族群得以和平共处、和谐共生,从未发生过真正意义上的宗教战争。西方文明则从古希腊哲学走向了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在罗马帝国崩溃基础上催生了基督教的一神体系及其无所不包的教义规范与教会组织体系,造成西方政教关系的数千年冲突以及不同教派间的政治冲突,甚至频频诉诸战争手段。
从对外政策看,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华文明有着和平发展的基因,有着与外部不同文明及民族和平互动的历史经验,从根本原则上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不接受霸权也不输出霸权。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西方国家竭力维护基于霸权规则的国际秩序,顽固维护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遏制和打压多边主义和文明多样性,对人类和平发展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成挑战。
特别是在民族和族群治理领域,中西治理差异尤其显著。在历史上,中华民族共同体经历了从多民族区域性统一到多民族全国性统一这种从“分”到“合”的历史进程,各民族都对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作出了独特贡献。西方现代民族国家从古罗马帝国体系和基督教神权政治中分化裂变而来,在整体上表现出从“合”到“分”的历史趋向。中国历代王朝塑造天下大同秩序、构建多元一体格局,推进不同族群深入交往交流交融,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融聚发展。西方民族国家继承中世纪封建制传统,热衷于在地域上插上种族标签,通过各种政治与文化手段,强力塑造出高度同质化的现代“民族”观念和身份。在现实制度实践上,新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将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相结合,将民族特色与共同体共性相结合,解决了单一制国家内部的民族整合问题。在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中,民族平等是第一原则。西方民族国家无论是对少数民族和外来移民实行同化和压制政策,还是实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都没有真正化解多民族社会治理问题;一些看似民主的公投程序进一步带来社会的撕裂与对抗,反而造成了更加严重的“认同政治”问题。
中西民族治理的差异还深刻体现在以民族学为代表的学科和知识生产的不同演变轨迹上。西方民族国家在对外扩张中,建构起以人种学、人类学和民族学为主体的知识体系,主要研究被他们称作“野蛮人”的非西方群体,突出少数族群的特殊性,带有浓重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和殖民歧视色彩。近代以来,在“西学东渐”背景下,民族学进入中国,虽然中国学者努力对其本土化,为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尝试提供理论支持和知识基础,但还是潜藏从西方人类学视角研究民族特殊性与差异性的传统路径依赖。因此,进入新时代以来,着眼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构建包括民族学在内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国理论政策界和知识界开始力图摆脱西方概念和话语的影响,探索建立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为核心的中国特色民族理论和话语体系。
欧美民族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是很多国家模仿学习的“范本”。然而,当前欧美的种族与族裔矛盾不断加剧,国家认同基础遭受冲击,民族国家范式与国家认同建设面临深层困境。
西方民族国家的族群分化日渐明显。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受新自由主义影响,不少西方国家政府不断减少对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控制与服务,导致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财富向少数人积聚,中产阶级持续萎缩,阶层日益固化,民粹主义、种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思潮泛滥。各种基于次国家身份、亚文化认同的群体间对立持续发酵,其中种族与族裔矛盾尤为尖锐。例如在美国,少数富人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主要收益据为己有,中下层白人从经济全球化中得到的好处寥寥,却要承受失业、收入下降等后果,他们迁怒于有色人种和少数族裔,指责其抢了自己的饭碗。
西方民族国家的社会撕裂日渐明显。随着贫富分化的加剧,欧美国家政治极化和社会撕裂愈演愈烈。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的政治分歧日趋扩大,敌意持续加深,攻讦不断升级,严重侵蚀其所谓的民主政治。2021年1月,大批美国人拒绝接受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结果,包围并袭击国会大厦,威胁伤害政要人士,导致多人死亡与重伤。这一震惊世界的美国国会山骚乱事件,是美国政治极化与社会撕裂的缩影。2022年一项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美利坚民族的身份认同程度堪忧,67%的美国人不再对身为美国人感到骄傲。在欧洲,其政治光谱的极化现象同样明显,极右翼和极左翼政党兴起,呈现出强烈的反精英反建制的政治异化与极化色彩。
现代国家的认同困境日渐明显。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是多民族国家。各国不同程度存在着各自的民族问题。在美国,民族问题主要涉及土著民族、非洲裔以及拉丁裔、亚裔等族裔;在欧洲,民族问题主要包括移民与难民问题;在非洲,民族问题主要呈现为部族冲突;在印度,民族问题主要表现为教派矛盾与种姓制度问题。因此,世界各地区各国家都面临着增强国家认同的共同任务。对于如何建设现代民族国家,欧美国家主要提出了族裔民族主义和公民民族主义两种思路,相应采取同化与多元文化主义等具体政策,以应对种族与族裔多样性。但这些措施并没有真正解决现代国家认同困境,同质化的熔炉政策和极端多元化的族群治理模式皆无法真正奏效。
欧美社会面临的现代国家认同困境和国家层面的民族认同困境,既反映出西方民族国家范式造成的内部民族治理危机,也反映出西方帝国主义通过殖民主义和全球化网络造成的全球性民族治理危机。但一些西方国家却采取双重标准,对自身和盟友的问题视而不见、百般开脱,对其他国家却吹毛求疵,甚至不惜歪曲历史与现实,意图通过打民族牌、宗教牌、人权牌的方式,实现遏制他国发展、破坏他国形象、干涉他国事务的目的。
相较于西方社会陷入国家认同困境与族群撕裂困境,中国在新时代明确提出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塑造了与西方迥然不同的民族治理与国家认同之路。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作为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一以贯之的核心主旨,具体政策措施可以变,但核心主旨不会变。中国共产党始终推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以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基本内容,不断调整形成适合中国国情与民族实际的治理体系。中国共产党始终与时俱进优化民族治理理念,将民族因素、区域因素、文明因素、国家利益因素、全人类共同价值融会贯通,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包容化解民族多元张力和内外挑战压力,推动建设更高质量融聚发展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处理民族问题,提升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出发,对内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对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支持。
总之,西方民族国家及其制度安排,无法真正破解国家认同困境与全球性族群治理难题。中国的民族治理理念和制度实践,根植于中华文明特性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具体实践,实现了各民族和谐共处,破解了政治认同与族群撕裂困境,彰显了以共同体原则和方法超越西方民族国家范式的独特优势,能够为开创全球治理新局面提供重要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