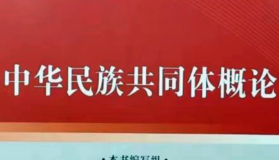-
1 授课视频
-
2 章节测验
近代以来,为了寻求救亡图存之道,中国人不断“开眼看世界”,寻找摆脱危机的方案。其中,近代西方民族国家学说以明治时代的日本为中介,逐渐在中国
传播开来。中国的政治文化精英一方面尝试以西方民族国家为模板来改造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与社会结构,另一方面又不断思考批判西方民族国家本身所蕴含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要素,这使得建构现代中国的理论与实践从一开始就具有中国自身的特征。
近现代中国认同的生成与加强,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由自在走向自觉的重要思想动力。1689年,清政府在与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时,首次将“中国”作为正式国家名称使用,但其应用范围在很长时间内主要限于外交领域。鸦片战争后,在共御外侮的时代背景下,清朝疆域内的汉人、满人、蒙古人等,共同参与了中国认同的塑造过程。
为应对统治危机,维系大一统,有识之士开始关注中国的边疆事务和边疆问题,对边疆史地的考察成为潮流。一时间,姚莹、吴大激、许景澄、薛福成等人皆为国家筹边谋防,所发论述大多突破了传统的华夷之辨,代之以对近代国际关系的现实认知,为现代中国国家意识的形成提供了思想资源。
在民族危机和近现代主权国家体系的影响下,“主权中国”的国家叙事日益增强,“中国”转化成具有近现代意义的国家称谓。1909年,清政府颁布《大清国籍条例》,除标题中有“大清”二字外,正文内容全都以“中国”取代“大清”。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颁布的政令、法令等,均普遍使用“中国”作为国名。这基本奠定了“中国”作为国家名称的合法性,也初步奠定了包含汉、满、蒙古、回、藏等各族人民在内的“中国人”作为国民身份认同的政治基础。
通过反抗列强的侵略和压迫,中国各族人民强化了自我的国家认同。他们逐渐联合起来,共同维护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反对各种形式的民族分裂。辛亥革命爆发后,英、俄等国利用中国政局混乱之机,在蒙古、西藏等地制造民族分裂活动,遭到了各族人民的坚决抵制。西蒙古王公通电全国,表示“汉蒙久成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公开宣告蒙古族属于中华民族,表达了共同守护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强烈愿望。新疆、云南、广西等边疆地区的军政首脑也都公开支持政权统一,坚守住了民族大义的底线。
民国初年,作为近现代国家主权的象征,国旗成为各族共享的国家认同符号。带有浓厚国家意味的徽章、护照等,也逐渐在中国社会传播并流行起来。
西盟王公招待处编:《西盟会议始末记》,商务印书馆1913年版,第43页。
随着西方民族国家学说的输入,西方带有严重种族偏见的“黄祸论”与“文明等级论”,不仅冲击着中国传统的族群认知,也刺激着中国知识精英对“民族”的含义进行深入思考。在此背景下,“中华民族”一词作为现代族称,经历了概念的多重衍化。
20世纪初,康有为、梁启超等主张改良的立宪派与孙中山、章太炎等主张推翻封建专制的革命派就“中国向何处去”展开论战。1905—1907年,双方论战达到高潮,立宪派和革命派分别以《新民丛报》和《民报》作为主要阵地,带动大量报刊投入以“民族”与“国家”为主题的大讨论。“满汉之界”成为争论焦点,不同类型的民族主义思潮开始涌现。
梁启超敏锐地察觉到狭隘民族主义存在风险隐患。1900年,他指出,“因满人主国,而满汉分界,因满汉分界,而国民遂互相猜忌,久之而将见分裂之兆也”。“民族分裂”的忧患意识促使他对中华民族的整体特性进行深入思考。
1902年,梁启超正式提出“中华民族”概念。当时,中国许多民族已经被西方学者称为“民族”,如“蒙古民族”“满洲民族”“汉民族”“藏民族”等已被普遍接受。1903年,梁启超指出:“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1905年,梁启超从族群历史演化的视角对华族、蜀族、吴越族等中国古代族群作出定位,认为这些都是自有史以来即居于中国的群体,都属于“中华民族”。在总结历史上各民族互动交融的过程后,他指出,“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中华民族”具有古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多元一体”属性。
与此同时,一批留日的满族、蒙古族同胞,在东京和北京创办《大同报》《北京大同日报》《大同白话报》,自觉倡导满汉人民平等,号召“统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大国民”,与国家兴亡同其福祸;提出中国人民都是同民族、异种族的国民的论断,表现出“民族大同”的强烈自觉。
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革命党人抛弃了此前狭隘的“排满革命”“驱除鞑虏”观念。1906年,孙中山已注意区分满族百姓与满族统治者,指出民族主义并不是遇到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辛亥革命爆发前夕,代理同盟会总理职务的刘揆一强调,要联合五族革命志士,共同组成革命团体,推翻清朝统治。
革命党人之所以要立志推翻清政府,归根结底是强烈的反帝国主义思想。他们批判清政府由于不能抵抗外敌而让中国沦为“欧美之陪隶”。武昌起义爆发不久,章太炎即致信留学日本的满族学生,劝他们不必因此感到恐慌,强调革命成功之后,“君等满族,亦是中国人民,农商之业,任所欲为,选举之权,一切平等”?。这表明清末革命运动中的“中华民族”认同,已经超越了各族之间的身份差异,转而进入塑造“国民”、建构新的“民族国家”的理想追求中。
中华民国成立后,“五族共和”理念促进了“中华民族”一词的广泛传播。现代报刊的蓬勃发展,极大拓展了“中华民族”概念的传播范围,甚至在蒙古文、藏文里也出现了“中华民族”的对应词语或表述。以“中华”为名称的团体纷纷成立(如中华自治协会、中华教育改进会等),积极促进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以“中华”命名的新式报刊,如《中华杂志》《中华日报》《新中华报》《中华新报》《大中华自治公报》等大量涌现,成为传播中华民族意识和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民国初年颁布的多版国歌也都以“中华”作为主频词,如1919年《尽力中华歌》数次叠用“中华”,一度流传广泛。各族人民同属“中华民族”越发成为国人的共识,成为中华民族自我觉醒的重要标志。
近代中国的国家建设是在复杂的内外环境中展开的。如何继承清朝以来形成的疆域版图,并在此基础上整合中原与边疆地区,保证主权完整、国家统一及边疆稳定;如何建立现代国家的组织、动员、汲取机制;如何摆脱经济命脉被控制,国家被瓜分的局面,发展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是国家转型的重要问题。
“中华民族”的内涵演变,与时代主题相伴而行。1901年,梁启超发表《灭国新法论》,借由叙述埃及、印度、波兰、菲律宾等地的亡国史来提醒国人,西方列强的对外扩张早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攻城略地、抢占地盘,而是会充分运用经济、金融、教育等方式来控制非西方国家。要想摆脱被“灭国”的命运,要想在时代危机下实现新生,就需要有针对性地进行一系列政治架构与政治制度上的变革。章太炎认为,近代中国的政治建设,首先应以凝聚、动员全国人民的力量来实现救亡图存为首要目标,建设现代国家需要超越过去基于家族的、地域的、族群的界限,使所有中国人具有共同的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一起致力于摆脱中华民族近代以来面临的危机。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社会主义学说开始进入中国。早在1873年,王韬在其编撰的《普法战纪》中,就已简要叙述法国巴黎公社的武装斗争。来华传教士所办报刊也刊载过关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学说的介绍。邓实在1903年提出,“社会主义者,思想最高尚之主义”。1905年5月,孙中山赴布鲁塞尔,与第二国际负责人进行了交流,表示革命成功之后的中国将实行工业化,但应避免出现类似于近代西方的剥削制度。革命党人认为,清末革命除了要推翻清王朝统治,还应改造不合理的社会结构,社会革命应当与政治革命并行。
大多数革命党人在思想渊源上、教育经历上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面对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经济剥削与贫富不均,他们很难在价值层面表示认同。儒家传统主张“责任伦理”,强调每一个人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中,要对周围的人有一种休戚与共之感,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使整个社会成为一个具有紧密联系的共同体,而非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个人主义,单纯以利害关系相结合。凡此种种,都是清末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深层文化基础。
尽管清末革命党人开始思考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的可能性,可由于他们与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缺乏有机联系,其思考不免流于空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