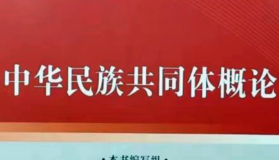-
1 授课视频
-
2 章节测验
清前中期,在星罗棋布的八旗驻防区内外,汉、满、蒙古等族逐渐拆去藩篱,彼此交流,走向融合。广泛存在的联姻现象,使各族之间水乳交融。清朝大规模移民活动屡见不鲜,汉人由中原迁至边疆四至,同时周边族群或南下或北上而进入中原地区,基本上形成了汉人与其他各族纵横交错的分布格局。
有清一代,中原等地因人口激增而地力有限,民众背井离乡,远赴蒙古、东北等边疆地区谋生,“走西口”“跑口外”“闯关东”是其中主要途径。
“口”本指明长城的关口。顺治年间,清政府允许民众在各边口内的空地治田营生,但禁止到口外游牧开垦。然而,令已出而禁未止。陕北延安、榆林等地农民,靠近伊克昭盟(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因地近沙漠,迫于生计,不得不租借口外蒙古人的土地耕种,春出秋归,岁以为常,被称为“雁行客”。康熙年间,绿营军驻防内蒙古,推行“开边制”,招汉人耕种。山西、陕西、甘肃等地贫民蜂拥而至,经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张家口、杀虎口及陕西边外关口等,迁往内蒙古西部。伊克昭盟七旗境内,凡邻黄河、长城处,皆有汉人足迹。雍正以后,内地农民前往后套(今内蒙古巴彦淖尔狼山、乌拉山麓南部平原)开垦者渐多。随着移民不断涌入,口外逐渐形成小规模汉人聚落,不断吸引内地无地少地的贫民前往,或投亲靠友,或另辟新村,久之则落地生根,融入本地。经过长时间的“走西口”,内地汉人形成以鄂尔多斯地区为中心的定居圈,集中分布在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巴彦淖尔盟和阿拉善盟,向北辐射至库伦。
东北是清朝的“龙兴之地”,康熙朝废除“辽东招垦令”历行封禁。但辽东土地肥沃,地广人稀,又邻近直隶(今河北)、山东,故偷越关口者始终不绝。乾隆年间,直隶、山东农民已深入东北腹地。其中一部分在进入吉林乌拉(今吉林吉林)、伯都讷(今吉林松原)地区的同时,还沿辽河和柳条边墙北上,进入内蒙古东部的哲里木盟(今吉林通辽)垦种。嘉庆、道光年间,移民沿嫩江进入黑龙江西部,成为郭尔罗斯后旗(今黑龙江肇源)、杜尔伯特旗等地蒙古王公的佃户。这些关内移民在当地多以贸易、狩猎、淘金、采药、垦荒等业务为生,和当地人逐渐融合。
在清朝大规模移民运动中,还有一个感人的西迁故事,即锡伯族万里戍边。清廷平定准噶尔叛乱之后,刚被收复的伊犁地区历经数十年战乱,地荒牧调,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边防空虚。彼时沙俄步步东扩,时时觊觎。乾隆二十七年(1762),清廷在新疆设立伊犁将军,驻扎伊犁惠远城(今新疆霍城南),统辖全疆军政事务。1764年,清廷从盛京各处调遣年富力强的锡伯族士兵1000名,防御、骁骑校20名,连同眷属3275名,西迁伊犁(图11-2)。生活在白山黑水间的锡伯人彪悍忠义,善骑射,能打仗。严酷的自然地理、寒冷的气候条件、多次生业方式的转变以及百年戌马生涯的锻炼,培养了锡伯人豪爽强悍、兼容并蓄、吃苦耐劳和坚忍不拔的民族品格和心态。
锡伯族军民赶着牛车、驼队,带上行装,一路上风餐露宿,其间数次断粮,靠野菜果腹。乾隆帝原本给了3年的行军期限,他们却只用了1年3个月,就抵达伊犁霍城一带。抵达次年(1766),他们被安排到察布查尔地区组建锡伯营。作为集军事、行政、生产于一体的组织,锡伯营在当地挖渠垦荒、扩大生产,同时数次参加平叛斗争,为促进边疆发展、维护祖国统一和新疆安定作出了突出贡献。
大规模移民使得不同人群错落杂居,族群融合的趋势难以阻挡。清初,实行“旗民有别”的政策。顺治初年,将汉官及商贾民人尽徙北京南城居住,北京内城为八旗所居;在近畿则推行圈地、投充、拨补等政策、强征良田,设立屯庄,分给旗人,或作为皇庄、王庄。各地驻防八旗另建“满城”居住,与当地民众隔离,去世或致仕须归京。加上旗人的种种政治、经济特权,这些构成清初满、蒙古、汉旗民同普通民众之间的珍域。
但后来,北京内城居住空间紧张,满蒙旗人迁居外城,与民人杂处,语言习俗相互浸染。旗人社区功能从以族群血缘和政治军事需求为主,转向以经济文化生活为主。畿辅旗屯由于频繁的土地交易,与普通村庄渐无差别。驻防八旗所在各地的民众,通过做奴仆、雇佣、抱养等渗入旗人社会,有的养子甚至承袭旗人身份。乾隆五年(1740),西安将军绰尔多奏报,西安驻防兵额仅8600余名,仆人却达到80000名。
在蒙古,随着内地移民不断涌入以及八旗驻防、屯垦、经商等活动影响,土默特地区有蒙古、汉、满、回、藏等族聚集生息,村落也由单一的蒙古族聚居演变为蒙古、汉、满、回等多民族杂居。鄂尔多斯一带,乾隆中期以后,汉民在该地中部呈点状分布;道光、咸丰时期,汉人移民激增,分布于该地东部长城沿边一带。道光中期,伊克昭盟蒙汉人口结构发生极大变化,渐渐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
在甘青宁地区,随着移民垦殖和商贸流寓人口增多,当地汉人从明朝的集中于屯田、卫所等据点,发展为广泛而分散的面状分布,与回、藏人群杂居。康熙二十年(1681),在河湟地区,“卫之辐辕殷繁,不但河西莫及,虽秦塞犹多让焉。自汉人、土人而外,有黑番……有西夷……而番回特众”。乾隆初年,大通卫各堡寨均为汉、回、土民杂居,如新庄堡“土人什之六,回民什之三,汉人什之一”百胜堡“土汉民各半,间有回民”,河州堡“回民、汉人间有”。
在新疆,清前中期移民进一步使当地族群结构多样化。察哈尔蒙古西迁后,与属蒙古的厄鲁特部及邻近的锡伯、绿营(汉人为主)、塔兰奇(维吾尔)、哈萨克、布鲁特等,发生不同程度的交往。他们畜养的马牛羊有相当部分供给绿营等作为军粮。新疆各族交错居住的格局基本形成。
西南地区经历了同样的历史进程。以往滇东南以壮、彝、瑶、傣等族民众为主。随着改土归流的推行,滇铜滇钱外输,便利了交通往来,当地汉人逐渐增多。雍正年间,云南普洱府便有大批汉人移入,“客籍之商民于各属地,或开垦田土,或通商贸易而流寓焉”,道光时已是“风俗人情,居然中土”。同时,本地原有的族群界限被冲破,逐步扩散。很多单一族群聚居的村寨大部变为多族群杂居。据《开化府志》,该府八里共辖村寨1203个,其中汉人聚居的只有25个,汉夷杂居的则有110个,其余多为壮、彝、傣族各支系的人所居住。
族际通婚是清前中期族群融合的突出特征。从社会上层来看,清朝将联姻作为巩固统治的重要手段。其中,满蒙联姻是清朝长期推行的一项国策。人关前,清朝便已与科尔沁、杜尔伯特、敖汉、土默特等大部分蒙古归属部落建立联姻关系。入关后,更是形成了以“指婚制”为核心,包含婚礼、陪嫁、额驸及格格等人封号、省亲、丧葬等内容为一体的联姻制度。嘉庆后,满蒙王公自行通婚。满蒙联姻持续300年,清皇室通婚近600人次。在满蒙联姻的背景下,蒙古诸部对清朝普遍忠诚。清朝满蒙联姻的意义远超往代“和亲”,不但维系了满蒙亲谊,巩固了对蒙古的统治,也使蒙古成为巩固边疆的重要力量。不少蒙古额驸或出任各类官职,或主动请缨征战,为维护统一立下汗马功劳。
满汉上层的通婚亦时有发生。贝勒岳托于天聪六年(1632)上《善抚人民奏》,建议满汉联姻。皇太极接受建议,安排岳托娶汉人佟养性之女为妻,后又分赐“大凌河官员及副将十五员娶妻”之礼,由此大开汉满联姻之风。清初八旗内部的满、蒙古、汉人联姻,不受旗分限制。顺治帝有四位妃子是汉军八旗女子,康熙帝娶汉军八旗女子更多,而清朝公主下嫁汉军旗人的亦不少。
各族间的通婚亦很普遍。顺治五年(1648),曾颁行满汉通婚条例。清廷又很快转向禁止满汉间的通婚,严格地说是禁止八旗内外的通婚。但满汉民众通婚非常普遍,道光年间,这种情况引起清廷恐慌,乃明发禁令。为了规避禁令,有人用“顶名”的办法先转为汉军旗人身份,再通婚。驻防八旗虽然与当地民众有着更为严格的隔离,但也不乏通婚。汉军旗人娶民人之女的情况就更为普遍。
汉人移民草原使蒙汉通婚增多。满蒙联姻时,不少汉人仆役随嫁而来,定居蒙古。法库县四家子乡蒙古人李姓,昌图县东嘎乡四家子乡的金、王、李、赵、贾、孟、何、高“八姓蒙古”,都是雍正年间随端柔公主出嫁,从直隶滦州迁来的。
随嫁的仆人、匠人、守陵户与蒙古人杂居、通婚.“穿蒙服、说蒙语、姓蒙姓、叫蒙古名”,渐渐融入。在甘青宁地区,蒙古、藏、汉、回等人群间的通婚、融合非常普遍。蒙藏民众信仰一致,生活方式相似,通婚较多。康熙年间,今青海省黄南州河南蒙旗地区的亲王与拉卜楞寺结成供施关系,蒙藏民众交流更趋密切。历代河南亲王中有4人具有藏族血统,其部众与藏人之间的通婚也非常普遍。
西南地区改土归流后,随着大规模的移民开发,各族群众之间通婚现象普遍,当地少数族群受汉文化的影响也较多。乾隆年间,贵州巡抚爱必达按照接受“教化”的程度,把黎平府的村寨分为几种。其中,“洞苗”“向化已久”,男子耕读,女子穿汉装、缠足,与汉民通婚;“花衣苗”“白衣苗”“黑脚水西苗”能薤发、读书应试,然而妇女的服饰未改;“黑苗”则固守旧俗,“鲜知文字”。雍正元年(1723),云南丽江改土归流设流官知府后,清廷设置以汉军绿营把守的关、哨、汛、塘等军事、交通据点。这些军人或彼此通婚,或娶“夷妇”,形成杂居在丽江关渠山隘间的汉民村落。他们的后代则普遍同当地民众通婚,部分随俗融合于纳西等族。丽江等地往来的商人,也多有娶妻生子者,往往经过一二代后融人纳西族。
清前中期,康雍乾三帝通过经筵日讲、编篡书籍、册封孔子等,将“道统”与“治统”合于一身,极大影响了清朝学术,增进了国家认同。同文之治是清朝文化的另一特色,以多语文为特征的多族群文化共存于大一统实践之中,“和而不同”文化理念逐渐彰显,“精忠无二”的政治伦理广为推崇,汉、满、蒙古等各族人民在语言、生活方式、精神领域、社会活动等层面深入互动交融,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创新发展。
为统治文化发达的中原地区,特别是规模庞大的士人群体,康雍乾三帝创造性地改造了儒学传统,力图实现“道统”与“政统”的合一,维系大一统的政治观。从皇太极、顺治帝,到康熙、雍正、乾隆三帝,都崇德尚学,通过“经筵日讲”、解释经典等活动,把自己塑造成符合儒家理想标准的帝王形象,确立“圣君”地位。此外,他们通过编纂大型类书、官修史籍等手段,引导民众思想,塑造了天下读书人对清朝统治的认同。
清前中期尊崇孔子,顺洽帝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康熙帝对孔子行三跪九叩之礼,御书“万世师表”。清帝垄断孔庙礼仪,来表达“治教合一”。雍正帝即位之初,颁布《谕封孔子五代王爵》谕旨,首次以官方形式明确规定“天地君亲师”的次序。
儒家文化历来强调“政”“道”分离,儒家门生握有道统,教化民众,皇权拥有政统,负责行政治理。但是,康雍乾三帝却刻意打造“圣君”形象,独占道统,最终实现二者汇聚于皇权之下。以“经筵日讲”为例,清帝一方面借此塑造自身符合儒家“圣君”标准的勤学形象,另一方面又对其进行改造。康熙十四年(1675),增加皇帝“复讲”环节;两年后,“复讲”提前,由皇帝先讲。这一角色调转,使经筵日讲成为皇帝训示臣子的手段。
清帝屡屡亲自参与论辩、清整经说、编纂经书,引领治学风尚,形成清朝独具特色的“帝王经学”。顺、康二帝汉宋兼采而尊朱子,雍、乾二帝重实效,侧重“经”的政教功能,“经世”之业,惟帝王所独行。康熙年间官修《易》《书》《诗》《春秋》四部经书的注本,乾隆初年官修《三礼义疏》、均反映了清朝官方的经学思想。特别是自康熙至乾隆时期,陆续纂修的《钦定春秋传说汇纂》《日讲春秋解义》《御纂春秋直解》等解经之作,以“尊王”为中心构建解释体系,消弭其间的华夷之辨。乾隆帝还亲自操控史事评鉴,设定褒贬标准。
规模宏大的《四库全书》的编纂,寓纂修与查禁于一体,重新梳理知识资源,重建价值体系、学术范式,以此来强化江南士大夫对清政权的文化认同。
这一系列举措促使清朝文人主动将道统归于政统。如陈廷敬说:“我皇上以圣德而居天位,天下大治,生民又安,故知道统之传果在上而不在下也。”此外,清前中期诸帝极为看重官员化民成俗的责任,通过乡约、社学、巡历乡村等举措深入基层。《圣谕广训》的广泛传播、教导和流传、便是例证。道光年间的古壮文典籍《顿造忙(创世经)》中,也记录了广西镇安府土司向当地传播诗书和书籍的情况。
与大一统相表里的“同文”是清朝君臣描述盛治时最常使用的语汇,“同文”之治跨越语言与族群的界域而具有超轶前朝的治理效力。
多语文书并非清朝首创,元、明皆有。但清朝的多语合璧文书却成为定制,规模较大,在边疆治理、礼仪实践、认同塑造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其功能和范围与前朝不可同日而语。
入关前,清朝官方文书使用满、蒙古、汉三种文字。顺治年间,蒙古文地位下降,公开文书以满汉合璧为主。后来,越来越多的文字进入敕谕、碑刻、钱币等合璧文书体系之中。乾隆二十八年(1763)修成的《钦定西域同文志》,确立了满、汉、蒙古、藏、托忒、察合台六体合璧格局。书中注释一律用汉文,以便“凡识汉字者莫不通其文、解其意”。这说明满文虽有特殊地位,但汉文作为通用文字的地位趋于稳固,其传达的教化理念是“同文”的核心。
清廷编纂了大量多语种辞书。如乾隆年间在康熙满文《御制清文鉴》的基础上,先后添加汉文、蒙古文、藏文和察合台文,增纂各语种清文鉴。《钦定西域同文志》是清朝第一部关于新疆、青海、西藏地名、人名的多语种大型辞典。清朝还系统翻译各族各类典籍,入关前后,以满文翻译《辽史》《金史》《元史》《明实录》《明史》等史书;乾隆年间以满文重新翻译“四书五经”,以满汉文合璧形式雕版印刷;民间以满文翻译刊印了《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小学》等汉文蒙学书籍;还将卷帙浩繁的《甘珠尔》《丹珠尔》两部大藏经翻译成满文、蒙古文。清朝特别设置翻译科,为多语人才进身之阶,又设蒙古学、唐古式学、回子官学(后改为回缅官学)、托忒学等,以培育人才。
虽然入关前清朝统治者便将“国语骑射”作为立国之本,但旗人子弟“渐习汉语”“沾染汉习”的现象仍不可逆转。康熙年间,因各满洲官员已通晓汉语,裁去部院及各地衙门中的翻译人员——“通事”。嘉庆年间,八旗子弟的满语口语生疏,甚至已不识满文。骑射习俗也未能保持。雍正以后,清帝屡屡为此怒斥八旗官兵。八旗子弟开始仿效汉人服饰风俗,出现取汉姓及字号、以行字界定辈分等汉化现象。这反映出满汉文化交融,渐呈一轨同风之象。
“同文”之治便利了各族在语言、服饰、文学、艺术等方面的互渗交融。
在语言方面,首先,作为现代普通话语言基础的北京官话,吸收了以满语音译词为代表的大量满语词汇,如耷拉、磨蹭、马虎、猫儿腻、挺(很)、萨其玛以及“宁古塔”“松花江”等地名。其次,新生了一些满、汉复合词,如“档案”一词,由汉语的“档”,加满语后缀而成;“车把式”由汉语的“车”和满语“把式”复合而成。最后,出现了因满人风俗而创造的满式汉语词汇,如剃头、抓辫子、捕娄子、旗袍、下嫁、收养等。
在服饰方面,旗袍即源起于满人上下一体的长袍。在饮食方面,满汉全席,亦满亦汉,非满非汉,是满汉饮食文化融合的典范。在建筑方面,北京紫禁城在建筑群体布局、空间序列设计上,传承了轴线布局、中心对称、前朝后寝等中国传统宫城文化元素,而其宫内的佛堂建筑等,又汲取了丰富的多民族文化特性,见证了满、汉、蒙古、藏等族在建筑艺术上的融汇与交流。
在文学创作方面,满汉文化更是深度交融。清朝入关后,满汉文士交游渐趋密切,加之科举助推,吟诗作画等风雅渐次流行于满人精英之中。而这些满人笔下的诗文画作,又呈现出满汉深度交融的特色,纳兰性德即为突出代表。又如,道咸时期女作家沈善宝所著《名媛诗话》中,展现出当时京师满汉女性交游对文学创作的深广影响。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巅峰《红楼梦》,同样反映了满汉文化的深度融合。曹雪芹在书中将道家的无为思想、佛教的因果轮回、儒家的纲常名教等融为一体,将旗人的京腔汉语发挥得炉火纯青,不仅有“嬷嬷”等大量具有满语特色的词汇,还有“把莺儿不理”等满式汉语句式。
在戏曲方面,作为国粹的京剧是满汉文化交融的产物,诞生后又在满汉交流中起到媒介作用。清朝的舞蹈等艺术,往往也体现出满汉文化的融合,如河北保定地区的国家级“非遗”舞蹈《摆字龙灯》,源自承德行宫的宫廷龙舞,后演化为清西陵守陵人的祭典舞蹈,它融合了汉人的图腾崇拜、精神象征以及满人的丧葬、陵寝文化,生动阐释着“满汉一家亲”。
满汉之外,各族文化交流也日渐频繁。入关后,满蒙人群间的语言文字交流进一步深入。满文本来创自蒙古文,但满蒙长期联姻、使后者语系受满语影响,本有的一些圆唇短元音开始消失,塞擦音亦与满语发音相同。受新满文的影响,蒙古族用蒙古文书写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时,一般也加上圈点,以避一字多音之弊。原本习用蒙古语的达斡尔族,后来习用满文者很多,甚有以满文记录达斡尔语,或以满语作为交际语言者。
蒙古族也受到汉文化影响。汉族移民的方言和词汇,融入蒙古语汇之中。如晋北移民较多使用的土默特方言中,即夹杂较浓重的晋北土语。许多地名也体现出蒙汉文化的共同影响。大量的汉族文学作品、民间传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演义》等,在蒙古地区以汉文广泛传播。同时,蒙古族文人也将汉族文学作品大量译成蒙古文,如蒙古族文学家哈斯宝所译《红楼梦》风行蒙地。蒙汉文人交友亦非常密切,建立起同学、同仕、同游之谊。比如,翁方纲与蒙古族博明的“十同”情谊,堪称典型。
清前中期,内地与新疆的文化交融更加密切。在汉人中流行的歌舞、杂技、戏曲、祭祀等,在迪化、伊犁、巴里坤等地随处可见。剪纸和年画传入新疆后,维吾尔、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等族民众多以剪纸图案来装饰建筑、服饰、地毯、刺绣等。喀什香妃墓的廊柱纹饰中的生命之树、莲花、石榴纹、“喜相逢”等图案,体现了中华文化对维吾尔雕刻艺术的影响。在建筑技艺上,出现蒙汉混合式、汉藏混合式建筑。而起源于吐鲁番盆地的“纳孜尔库姆”是维吾尔人别具一格的民间乐舞,吸收了汉人鼓点的节奏和跨腿跳转技巧,融合了蒙古舞的抖肩等。
在西南,儒家文化广泛传播。以保靖彭氏为代表的家训、族规中,包含重教养、齐家政、尚友爱、睦宗族、励勤俭等内容。许多乡规民约也已按照清廷“圣谕”的指导而撰写。汉人纪念屈原的端午节也传到西南。苗、布依、侗、土家、仡佬等族民众吸收了汉人的傩活动,发展为各有特色的傩戏。嘉道年间,布依族聚居地开始表演以汉人民歌小调为基础的花灯剧。侗戏也把中原的一些民间故事改编为表演内容。董永卖身葬母等“二十四孝”故事传入西南,并在人名、地名、情节上呈现出本地化特征,出现诸多彝文抄本。
藏传佛教诸教派中,清朝对格鲁派活佛系统的权力、地位予以正式认定,将寺庙和宗教领袖纳入地方行政体系,体现了清统治者对藏传佛教的有效治理。首先,无论是“黄教四圣”还是各个等级的呼图克图,清廷始终掌握对其的封赠和废黜权。驻藏大臣主管藏政,独揽向中央奏事权力,达赖无权向中央单独奏事。其次,推动形成达赖管前藏、班禅管后藏、哲布尊丹巴管漠北蒙古、章嘉管漠南蒙古和驻京呼图克图的局面。最后,由理藩院和地方各级官吏管理藏传佛教事务,规定寺庙额缺,限制寺庙规模,建立和规范年班朝觐制度,制定喇嘛禁令,将藏传佛教事务置于中央王朝的皇权之下,约束教权。
将入侵后藏的廓尔喀人驱逐后,清朝还发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作为治藏政策准则,其中第一条即为金瓶掣签制度,之后成为藏传佛教最为重要的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1792年乾隆帝定制金奔巴瓶(即金瓶)送至拉萨,并御制“喇嘛说碑”,刻有满、汉、蒙古、藏四种文字碑文。金瓶掣签制度既兼顾了活佛转世的宗教传统,又将活佛转世制度纳入中央王朝设定的律法轨道。
此外,清廷敕令修建的内地和藩部的一系列藏系庙宇,也成为代表“国家存在”的特殊政治场所。清朝统治者通过皇家元素的植入和对救建庙宇的“官衙化”改造,使得这些庙宇兼具治理蒙藏边疆地区的机构职能的同时,也成为藩部首领表达政治认同的场所。蒙古、京师、五台山等地的许多寺院,都将西藏宗教建筑艺术与中原宫殿建筑艺术熔于一炉。北京的雍和宫,原系雍正即帝位前的府邸,乾隆时改建为藏传佛教寺庙,成为融汇汉、满、蒙古、藏各族文化艺术的结晶。
在这一时期,蒙古高僧、学者的藏文撰述也逐渐增多,其中不少是历史著作。蒙藏地区学者所撰的藏文史书《汉区佛教源流记》和《如意宝树史》,叙述了从三皇五帝直至元明清的历史,并将“传国玉玺”传说贯穿其中,说明其对中原王朝系谱的认可。这与清中期以后藏传佛教高僧获任各级官职,在北京等地长期驻锡有关。
清政府致力于推崇“忠义”精神。康熙年间修《明史》,将明末清初变节而帮清朝打天下的降臣,如洪承畴等,打入《贰臣传》。在清政府主持编纂的《胜朝殉节诸臣录》一书中,对众多明朝忠臣义士,包括曾经抵抗清军的明朝英烈,如卢象升、刘宗周、史可法、袁崇焕等予以表彰。
“关帝”崇拜,是清朝大一统成功推动各族人民精神领域深度融合的显例。康熙四年(1665),清朝尊关羽为夫子,与孔子并称。关羽集忠、义、仁、勇、礼、智、信于一身,这些对生活于任何地区、信奉任何宗教的人而言都是令人敬仰的精神品格。关帝庙在清朝遍及东亚各地,证明了中华文明的教化之远。北京城里专祀关帝和以祭祀关帝为主的庙宇有百余座,在台湾岛也多达上百座。在西藏与甘青川藏族聚居区及蒙古族聚居地区,关帝庙被称作“格萨尔拉康”或“格萨尔庙”。在里塘,“自汉人寄贾其间,始建武庙在城南门外,番人也知畏服”。西藏拉萨、昌都、山南、日喀则、定日等地都有关帝庙;蒙古地区关帝庙也不少,以归化城土默特地区为例,地方志记载有15座关帝庙,其中仅绥远(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一地就有7座。在新疆,关帝庙随处可见。据嘉庆初年流放伊犁的洪亮吉说,他从嘉峪关向西直到惠远城,途经的人口聚居之处无不祭祀关公。在西南地区,瑶、壮、苗、白、土家、纳西、彝、羌、侗、水、布依等族民众也有供奉关帝的传统。羌人的“白石崇拜”中的五颗石头中有一颗即“关圣帝君”;云南的彝人和汉人一样出入关圣庙;苗民中流传着关帝是“火德星君”的传说;仫佬族过年有贴关羽像的习俗,并书以“秉烛达旦,忠义春秋”。不仅如此,关帝信仰还成为海外华人维系文化认同的重要精神纽带。
清朝“忠”“义”精神既来源于汉人传统的“忠君体国”观念,也来源于满蒙传统的“事主之忠”理念。蒙古、西藏等地关帝庙,与本土之格萨尔、藏传佛教大神等相结合,这表明关帝信仰蕴含的精神价值已然超越了族群身份,成为中华民族共同尊奉的伦理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