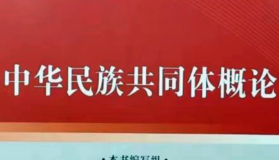-
1 授课视频
-
2 章节测验
“混一南北,胡汉一家”是时人对元朝统一中国的共识性评价。当时南方书贾在翻刻南宋日用类书《事林广记》时,为了更加契合时代背景,特地在该书地理部分新增“大元皇帝,奄有天下,混一南北”的文字,并在旁边配绘一幅《大元混一图》,昭示元朝统一之后疆域空前辽阔。随着这一历史认知在社会上扩散,《事林广记》配图的绘制者进一步标示,元的“混一”不仅包括了对原属宋、金统治下的区域的统合,还涵盖了东西向地理轴线下对应的广袤草原—绿洲地域。全国统一之后,忽必烈派人在各地广采舆图志书,组织人力编纂内容全新的全国性地理总志,这就是元成宗时期完成的《大元大一统志》。此书的命名彰显出时人对元朝开创大一统局面的体认。明、清两代受其影响,官方组织编纂了《大明一统志》和《大清一统志》。对元朝实现统一的历史功绩,朱元璋评价道,“昔者二百年前,华夷异统,势分南北”的局面一变而为“混一南北”。可见,即使像朱元璋这样一位推翻元朝统治的新王朝建立者,也积极肯定北方游牧族群对于中国统一所作的重大贡献。回顾中国历史,每当出现大一统盛况时,往往是强调华夷之辨观念的社会思潮消解式微的时期。对此一个生动的例证是,通常用于书面语的“华夷”一词在元代已经完全口语化,并且衍生出“国土江山”的全新义项。由此可见,在元人的政治观念中,唯有华夷两者相统合才算是完整的国土疆域。
元顺帝时期,朝廷为辽、宋、金三朝编修正史,将上述三朝皆视为正统,这一开明做法,平息了是否独尊宋统的争论。在这样的政治环境熏染下,南方士人心态渐趋开放,如元代最能凸显北方游牧族群特色,并直接反映草原生活面貌的“番马画”等题材,即广受原南宋统治区域内南方汉人画家群体的青睐。这些南人文士在画作中题咏的各类诗文,更是直接折射出作者对国家统一政治局面的认同。
在元朝大一统政治环境之下,跨族交往交流日趋常态化,各族群间的关系逐渐向更深的交融层次发展,族际通婚现象更为普遍。元朝政府对族际通婚不但一贯持相对开明的允准立场,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主动推动蒙古与色目上层贵胄之间的联姻。朝廷将皇室公主出嫁到高昌畏兀儿统治家族内;色目人中著名的钦察贵族土土哈家族曾连续三代娶皇室之女;元朝皇室男性成员的婚配对象也包括不少色目贵族女性,如元顺帝的生母为西北边部哈刺鲁部君长的后裔。
元代汉人与其他族群通婚比较普遍。开国功勋赤老温的四世孙脱帖穆耳定居江南,娶汉女高氏、朱氏。中书右丞相史天泽先后迎要了两位汉人女子、一位女真女子和一位蒙古女子。中书参知政事许有壬的继室赵氏是汪古人中书平章政事赵世延的女儿,而赵世延之妻亦为汉人。在元代,还存在不少回回男子迎要汉女的情况,这也是后来回族中包含汉人成分的一个原因。
随着畏兀儿人的内迁,许多族际婚姻出现,进一步推动了民族交融的发展。如廉希宪的母亲石抹氏就是完全“华化”的契丹后裔,属于元朝社会中广义的汉人成员。后来他又迎娶了畏兀儿人孟速思之女和女真人海撒之女、她们与廉希宪的子女中,三个女儿嫁给汉人官员。当时的另一位著名畏兀儿文臣阿鲁浑萨理的祖母张氏、母亲李氏和妻子郜氏均为汉人。元初参与灭宋之役的畏兀儿名将阿里海牙除原配夫人之外,续娶的诸妻也均为汉人,且其家族的女裔后辈成员中不乏嫁与汉人的实例。不仅如此,阿里海牙的孙子贯云石迎娶了汉人名臣石天麟之女为妻,而贯云石的生父贯只哥也是阿里海牙的一位汉妻所生。元代书法家鲜于枢的女儿嫁入畏兀儿官宦世家,元末孔子后裔孔瀛迎娶的继室是畏兀儿人。这表明,元代各民族并没有因为族属差异而产生文化上的隔阂,反而由于姻亲关系彼此变得更加紧密。
上述事例尤其反映出元代的西北诸族中,畏兀儿群体在与中原地区汉人的通婚联姻上显得最为积极。
由于大量蒙古、色目军人累世驻扎在各族之间,民间族际通婚更为普遍,如由特定蒙古部落的男性组成的探马赤军屯驻内地,常常从驻地周边的汉人社会中迎要民女为妻。久而久之,这些祖上出自塞外草原的探马赤军成员,最终融入驻地周边的汉人社会。有元一代,内迁的各类人群大多融合于汉人之中,也有不少繁衍至今,成为现今的少数民族。一般认为,今天西北地区的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均系色目人与当地的蒙汉诸族通婚融合形成的本土民族。
然而,元朝的族群治理存在明显局限,最为突出的就是“四等人”的划分及区别对待,将蒙古人与色目人擢升为享受统治特权的地位优越集团,尤以辅佐成吉思汗统一草原的蒙古显贵家族的后裔子弟为尊,而大多数汉人和南人屈居下位。不同族群等级之间的社会地位差异主要体现在仕途、法律等方面。以选官为例,中央及行省官署中的重要职位,多由蒙古贵族垄断,色目人中也有部分人士可以充任,而汉人担任要职者显著少于色目人,南人入仕的机会更是微乎其微。至于路以下的地方僚属机构中,最重要的长官达鲁花赤原则上均由蒙古人出任,汉人只是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才可能破例担任此职务。在司法领域,元朝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同类违法行为处罚结果因族群差异而轻重有别的情况。大体上,蒙古人和色目人可以享受较为宽大的处置待遇,而汉人和南人在违法后受到的处罚则更为严苛。同时为了防范汉人和南人反抗,朝廷还严厉禁止他们持有兵器,相反,蒙古人、色目人在这方面受到的法律限制明显较少。这些公开的歧视性做法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族群边界,妨碍了不同人群间的交流融合,而且使得族群矛盾始终时隐时现地存在于社会中,最终成为元末全国性民众起义的重要诱因。
元朝人口迁移的常态化打破了自然地理界限,既有为数众多的汉人移民开发边疆,又有大量边疆族群徙居中原,彰显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各族群相互杂居,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口分布特征。
虽然边疆乃至外来人群迁居中原在之前各个朝代屡见不鲜,但像元朝这样为数众多,又来源多元的边疆族群大举定居中原地区的现象很少。例如,不少原居住地相对偏远的色目人群体迁入中原地区并与汉人杂处交往,一些西北边疆的哈刺鲁人(唐代称为葛逻禄部)则集体移居至河南南阳、湖北襄阳等地,还有源自南西伯利亚的乞儿吉思人(今柯尔克孜族的祖先)远迁山东与辽东落户安家。
畏兀儿人的大量内迁是元代各族群跨地域分布杂居的典型代表。元初西北藩王叛乱,原本居住在哈刺火州和别失八里的畏兀儿人不愿受其统治,纷纷内徙,其分布范围遍及今西北、中原甚至东南各地。以大都为例,今北京海淀的魏公村即得名于元代畏兀儿人聚居的村落。这些定居大都的畏兀儿人中,既有在中央机构出任职务的官宦阶层,也有以僧人、工匠等其他职业身份移居于此的平民大众。内迁到大都以外的畏兀儿人中,在地方出仕为官者,一般担任路、府、州、县的达鲁花赤或同知,秩满后大多不返原籍,而是留居此地继续生活。鉴于畏兀儿人内迁数量较大,居住地比较分散,为便于管理,元朝政府专门颁布法律规定了有关畏兀儿、哈迷里人的民事诉讼程序,这反映出西域各族群众移居中原和族群杂居现象不断发展的趋势。
元代,因蒙古西征被签发来的回回人越来越多。当时从事农业生产的回回人主要分布在甘肃、河南、山东等地,从事商业贸易的回回人则大多活动在杭州、泉州和广州一带。东南地区的回回商人在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元初供职于泉州市舶司的蒲寿庚及其蒲氏家族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陕西和云南也有较多回回人居住,著名的回回人云南平章政事赛典赤父子,曾在云南兴修水利、推广屯田,受到当地各族爱戴,他们的子孙也留在那里繁衍生息。
在大批边疆族群移居中原的同时,还有不少汉人被安置于边疆各地。他们往往以士兵、农民和工匠的身份屯田务农或者从事手工业生产,将中原相对先进的生产技术传入当地,使边疆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有元一代大批汉人迁往漠南及漠北草原定居,因此较之以往的朝代,蒙古大漠南北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各族聚居的新兴城镇:
成吉思汗早在西征之前,就派遣田镇海率领汉人在阿不罕山北侧屯田,并建立了镇海城(又作“称海城”,在今蒙古国科布多东南)。和林是漠北的政治中心,也是大量汉人移居之地,窝阔台汗曾命刘敏主持修建和林城以及宫殿苑囿。忽必烈早在即位之前就积极地学习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传统和统治方式,他任用汉人刘秉忠在漠南草原上选址并建造了一座新的城市,即开平府。忽必烈即位后,将开平府升为都城,定名上都(图9-2),与大都合称“两都”。在上都路内,不仅有大量来自中原的农业人口,也集中了一批工匠、猎户和商人。两都制度确立之后,元朝皇帝每年都要北巡上都,并且在这里停留长达半年,花费多取自当地人民所纳钱粮,可见当时上都地区的经济开发已初具规模。此外,根据《元史》记载,元朝在今昌吉、伊犁、和田、吐鲁番等地驻军,数量从一两千人到几万人不等。同时,元朝在今阿勒泰、昌吉、伊犁、和田等地屯田,派遣官员管理。在位于塔里木盆地南缘车尔臣河流域的且末县的一处元代古遗迹中,集中出土过一批至元年间的与元代汉人驻军有关的文书遗物。这不仅反映出元初将大批汉军征发至南疆各地承担军事戍守任务的史实,而且其中所出的一件文书被鉴定为至今稀见的元人手抄金代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之一阙,凸显出中原文化通过汉人驻军在西域地区广为传播的事实。总之,人口迁徙的这种双向流动性及其对南北自然地理界限的彻底突破,以及由此在文化交流领域中产生的促进效应,均为元代族群交融的生动写照。
中央政府为加强对云南的统治,调遣主要由北方游牧士兵组成的镇戍军队长期戍守西南边陲。云南行省驻屯着两支万户以上的蒙古军和探马赤军,以及为数不少的畏兀儿军、汉军和新附军等。经年累月,这一军人群体与本地民众逐渐融合,其后代一直生活在今天的云南多地。今保山市施甸县是被称为“本人”的契丹后裔最集中的聚居地。今大理、保山的部分回族相传是随赛典赤入滇的回回军人后裔。今天生活在云南省安宁市、蒙自市以及石林彝族自治县等地的蒙古族自认为是元代蒙古移民的后裔,而玉溪市通海县曾是蒙古都元帅府驻地,元代蒙古军士的后裔大多居住于此。
总之,尽管元朝在政策层面上实行了族群等级政策,但它没能阻隔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的民族大融合主流而最终消亡。
元朝上承宋金以来的文化传统,采取开明的包容政策,有助于各族相互学习借鉴彼此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有益于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广采外来文化的精华优长。各族人民通过密切的交流互动,在相互学习过程中,共同创造着中华民族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
在科学技术方面,畏兀儿农学家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在农学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此书仿照前代《四民月令》的体例,按月记载农事操作和各项准备工作,对于指导具体的农业生产活动颇有助益。它与《农桑辑要》《农书》共同体现了有元一代农学的最高发展水平。
在天文地理方面,元世祖时期来华的回回天文学家札马鲁丁成就斐然,其制作的地球仪首次以直观的方式将大地球形说等科学地理观念传入中国。他还利用其掌握的广博西域舆图知识,积极参与为《大元大一统志》绘制全国总图的工作,最终成功绘制出一幅在当时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天下地理总图》,弥补了此前宋金时期的《华夷图》系列往往忽略西北边疆地区的缺陷。
在传统的手工业生产领域,元初江南松江(今上海)人黄道婆将从居住在今海南岛的黎人群众那里学到的先进纺织技术及其生产工具传回家乡,使得松江一带的棉纺织产业得到迅速发展,代表性商品如“乌泥泾波”名闻天下。由黄道婆改良的先进纺织技术又从江南各地逐渐被推广于全国,对我国古代纺织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与此同时,北方游牧族群的语言文化也对汉人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这首先体现在当时流行的北方口语(元人称之为“汉儿言语”)在语法表达上受到蒙古语的影响,往往具有一些蒙古语语法的特征,如倾向于将全句的判断动词“有”置于句末的位置,从而显示出与传统汉语表述习惯的不同。其次,在各族艺术家广泛参与的使用汉语口语来表演的戏曲创作中,出现了数量可观的音译蒙古语词汇。而且,元代戏曲作者在构思植入蒙古语词汇的具体语言场景时,一般都会设法使它们和艺术角色的文化背景相契合。例如、“元曲四大家”之一马致远在《汉宫秋》中,将说出“把都儿”(蒙古语“勇士、英雄”)一词的角色赋予身份相当于匈奴单于的番王。同样,元本《琵琶记》中一个为官员提供服务的驿站人员角色直接以“兀刺赤”的名称出现,与蒙古语中该词所具有的“马匹照料人员”的基本含义高度契合。从上述词例来看,元曲作者对其词义是了然于胸的,而当时的普通观众同样也大体知晓其义,这样蒙古语词汇在戏曲表演中的出现才能起到为原作增色的艺术效果而不致产生晦涩生硬的问题。这种非汉语词汇在大众化的文学作品中频频出现的情况,在唐诗宋词中是难以见到的,由此可见,元代族群接触交融的深度和广度确实超过了此前的其他时段。
个别见于元曲的这类词汇甚至一直沿用至今,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驿站的“站”。汉语的“站”原本只是动词“站立”的意思,并无类似今天车站之类的名词性义项。而在元代,蒙古语表示车马驿站的“jam”直接以借词的形态进入汉语,被音译为“站”,仍旧表示驿站等名词性义项。这类渗入汉语中的蒙古语词汇,丰富了自古以来即作为全国通用语言的汉语的词汇,增强了汉语的表达能力及形象性,是各族文化交流融合现象的生动见证。
在文学创作领域,边疆文士群体对中华文明的发展繁荣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王士祯在《池北偶谈》里说:“元名臣文士,如移刺楚才,东丹王突欲孙也;廉希宪、贯云石,畏吾人也;赵世延、马祖常,雍古部人也;孛术鲁种,女直人也;遒贤,葛逻禄人也;萨都刺,色目人也;郝天挺,朵鲁别族也;余阙,唐兀氏也;颜宗道,哈刺鲁氏也;瞻思,大食国人也;辛文房,西域人也。”
当时,西域人的诗歌创作风气之盛、题材之广、作品之多、成就之大,堪称空前。有的诗作描绘了草原生活,填补了中原诗歌中草原文化题材的空白,如遒贤的《塞上曲》。有的则体现了对中原儒释道观念的吸收,反映了边疆族群“华化”程度的加深,如洒贤的《送道士袁九霄归金坡道院》。有的表达了对农耕生活的喜爱,反映了边疆族群对中原耕读传家理念的吸收和接纳,如贯云石的元曲《双调·水仙子·田家》、色目诗人泰不华的《衡门有馀乐》。有的则是对忠勇爱国行为的赞扬,反映了边疆族群对儒家忠孝治国理念的内化与信念,如伯颜(子中)的《挽余廷心·义重身先死》、遒贤的《送慈上人归雪窦追挽浙东完者》。
此外,元末明初的蒙古人作家杨景贤将之前流行的唐僧取经故事改写并创作出篇幅更长的《西游记》杂剧,首次将该故事的重心从叙述唐僧的事迹转移到对孙悟空形象的塑造上。这一作品对后世的章回体小说《西游记》的构思写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元代多民族文化的交融不仅体现在前述南北地理轴线上汉人与蒙古人之间的深度互动方面,而且体现在东西方向上汉人与西域畏兀儿人、青藏高原藏人的互通有无上。例如,居于北庭(别失八里)的安藏,五岁开始学习汉文经书,幼年时即达到“一目十行、日记万言”的娴习程度,他还系统学习佛经,最终成长为儒释兼通的文化人才。忽必烈即位不久,安藏曾进《宝藏论元演集》,令皇帝赞叹不已。安藏以儒家政治立场推崇君主当以亲习经史而知古今治乱之由,同时正心术以示天下向背之道。他曾奉诏参与将汉文典籍《尚书》《资治通鉴》《难经》《本草》翻译为相关诸族的语言;还曾亲自从事不同语言之间佛经的翻译工作,在元代多民族之间的宗教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媒介作用。又如河西僧人沙啰巴,以精通各种语言且译功深厚著称,他利用主持译经事业的契机,广交汉人名士,征引儒家经典阐释佛教教义,对增进儒释双方的文化互鉴及沟通贡献良多。
这一时期以宗教为纽带,体现汉藏文化交流的文物更是不胜枚举。在西藏流行的“过街塔”这种颇有地域特色的宗教建筑,开始出现在中原不少城市中,如北京的居庸关、镇江的西津渡等。而汉藏佛教文化交流交融的最佳例证,就是杭州飞来峰的元代石刻造像群。它同时吸纳了来自西夏、吐蕃、中原不同地域流派的多支佛教艺术元素,整个造像体系在艺术风格上呈现出高度的和谐与统一。
元代政治大一统的时代气象在汉藏等多民族佛教文化交流上最直观的体现,是元世祖在其统治后期组织各族僧俗学者共同编撰的佛经目录学巨著《至元法宝勘同总录》。该书综合收录了当时所见的汉文大藏经和藏文大藏经的各自详细目录,并对二者的异同加以对勘,从而使得此书足以代表元代中国大藏经目录的全貌,极大地推动了中原和吐蕃佛教界彼此取长补短、相互学习的进程。参加这一重大文化工程的学者半数是汉人,其他则来自吐蕃、畏兀儿、蒙古等,他们集思广益、通力协作,完成了这部可以视作文化交融里程碑的巨著。
很多全新的外来文化成分,在这一时期被中国文明所吸收。以元代杭州回回人墓地出土的波斯文墓碑为例,两方墓碑均刻有13世纪波斯伟大诗人萨迪的作品片段,它被伊朗学者鉴定为现存的在伊朗以外发现的年代最早的萨迪诗歌碑铭。这成为中伊两大文明对话交流的一段佳话,而那些来华定居的回回人士在这中间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这批元代杭州回回人墓碑上用于装饰碑面的刻纹图案多呈明显的汉式特征,反映出外来移民群体在保留自身文化传统的同时,还曾主动吸纳儒家文化的元素,并与汉人社会保持交往联系。因此,元朝也是中华民族主动吸收外来文化成分、壮大自身发展的重要时段。
小结
元朝彻底结束了中国持续数世纪之久的分裂局面,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地位,足以与秦朝和隋朝两次统一的历史意义相媲美,而这次统一在地理空间上覆盖的范围则显著超过了前两次。秦汉隋唐时期的匈奴、乌孙、突厥、南诏、吐蕃等边疆政权虽然与中原王朝保持着朝贡、册封、会盟、联姻等政治上的密切联系,但尚未直接隶属于中原王朝的统治,也没有系统地实行与中原接轨的政治制度。而元的大一统真正促使整个中原与辽阔的边疆地区在行政制度上联为一体。中央政府的典章号令遂畅通无阻地通行于整个中国,大大缩小了中原与边疆在治理上的差别。因此,元代后期的汉人文士许有壬才会用“六合同风、九州共贯”来评价元朝治绩的突出特征。这一评语凸显出元朝治理下的中原与边疆、汉人与其他族群的互动交融,在承袭历代以来民族融合成就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建树,终于达到新的历史高度。
相较于汉唐盛世,元朝虽然统合全国的时间较短,但相比此前同样结束了分裂局面的秦、隋两朝,已发生了质的飞跃。这也折射出第三次全国大一统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凝聚力越来越强。它所开创的这次规模空前的大一统,给后世留下了丰厚的政治遗产(诸如行政大区制度等),为继起的明、清两代的长期统一初步莫定了制度基石。
元朝最主要的政治改革和制度建设方面的成就基本完成于忽必烈统治时期。忽必烈实行文治,尊孔子、行汉法,重建汉唐式的中央集权体制,建立直达基层的郡县文官体制,并创造性地为大一统贡献了宣政院、行省制、土司制等制度设计,将边疆地区有机纳入中央集权的治理之下,以空前的大一统融合了各族群、各宗教与多元文化,从而消除了游牧分封制所带来的离心力,建立了完全中国式的正统王朝。
此后元朝诸帝的政绩大多乏善可陈,难以与世祖朝的政治成就比肩,尤其在积极引进汉制、移风易俗方面渐渐裹足不前。拥有受封藩地特权的守旧派宗王集团,不时利用朝廷未能确立相对稳定的新君继承办法等制度性缺陷干预朝政。元中期以后,本为外姓的掌握禁军兵权的钦察军事显贵集团也开始介入愈演愈烈的宫廷政争,终致在元文宗即位前夕,统治集团内部爆发严重破坏社会正常秩序的剧烈内战。
不仅如此,元朝在消除族群歧视等方面始终存在明显缺陷,公开违背一视同仁原则的划分“四等人”的做法一直延续至元末。特别是元顺帝前期,以伯颜为首的特权阶层还一度试图通过加剧族群压迫来转移各种社会矛盾,致使族群矛盾空前激化,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后来经历的“脱脱更化”也未能扭转这一趋势,直至社会危机激化为全国性的民众起义。
1368年明朝建立,元顺帝父子及其残余势力离开大都、撤回草原,并继续沿用故元国号,但因元朝对全国的统治业已宣告终结,史称“北元”。据传元顺帝在元明交替之际所作的蒙古文《怀念两都之歌》,直至17世纪依然流传在北方草原,表达了蒙古人对失去大都的无比哀伤和叹惋。显然,大都所代表的已不仅仅是政治上的繁华旧梦,更是与草原一样承载着历史记忆和情感归宿的故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