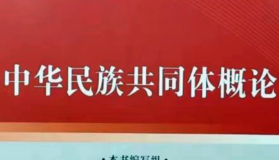-
1 授课视频
-
2 章节测验
13世纪初期,中华大地呈现多个政权相互对峙并存的状态,这些政权包括金、南宋、西夏、西辽、吐蕃、大理等,它们都不具备完全统合其他竞争对手的实力,呈现出分头并进的局面。终结这一分裂局面,最终再次实现大一统的,是由铁木真(1162—1227)奠定的蒙古汗国及其继承者忽必烈(1215—1294)缔造的元朝。
铁木真是游牧于漠北草原斡难河流域的蒙古部首领。一般认为,蒙古人主体来源于室韦,室韦的主要部分与早期拓跋鲜卑同源于东胡。自12世纪80年代始,铁木真开始了兼并草原其他各部的进程。其间,他还从统治中原与华北的金朝那里接受了相应官职。截至13世纪初期,通过军事征战与政治联合的双重手段,铁木真完成了对漠北草原诸部的统合,建立蒙古汗国,被尊为“成吉思汗”。后来,他停止对金朝称臣纳贡,成功争取了在漠南草原为金国戍守界壕边堡的汪古部的投奔归附。1211年,他以漠南地区作为跳板,径直南征金朝腹地华北平原,迫使其移都南京(今河南开封)。成吉思汗还积极向西北地区拓展,在1218年结束了西辽政权在西域近一个世纪的统治,在1227年彻底征服了西夏。1234年,蒙古军队联合南宋攻灭金朝,完全统治了中原地区。1247年,蒙古宗王阔端与吐蕃萨迦派高僧萨迦班智达举行凉州会盟,后者发出《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双方以和平协商方式完成了对吐蕃各部的招抚。蒙古军队于1254年攻灭大理;1258年,又兵分数路讨伐南宋,将宋蒙对峙的前线进一步推移至江淮之间。
不过,蒙古军队在征宋期间经历的挫折表明,如果要最终取得统一全国的成就,就需引汉制、行汉法,大力加强中央集权,以赢得广大汉人群体(包括那些定居内地的契丹人、女真人)的认同。
1260年,忽必烈即位后,取消了原先实际统治华北、中原的汉人世侯(即归附蒙古的地方势力)集团的政治特权,将地方统治权收归中央,以利于集中掌控中原的人力物力资源。同时,为避免统治集团内部保守派的掣肘,忽必烈采取渐进改革策略,先立年号,继而为大蒙古国的历代先君制定庙号,最后在1271年正式确立了汉式国号“大元”,取《易经》中“大哉乾元”之意,完成了与中华王朝正统性相接续的步骤,争取到了更多汉人士民的归附。
忽必烈时期,使者郝经在致南宋皇帝的书信中特别强调能行中国之道的君王才有资格成为中国之主。即便是激烈抗元、宁死不降的宋人文天祥,对忽必烈实现天下一统的大一统理念也表示认同。他拒绝降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坚守人臣“不仕二朝”的儒家忠义精神与“遗民”观念。忽必烈对此精神也加以肯定和欣赏,评价他“是好人也”。元朝所修的《宋史》并未因为文天祥不降而贬低他,反而大力褒扬其殉国亡身、舍生取义的孤忠大节:“观其从容伏质,就死如归,是其所欲有甚于生者,可不谓之‘仁’哉。”
至元十三年(1276),元军兵临临安城(今浙江杭州),宋朝幼帝及群臣携传国玺集体出降。至元十六年(1279),元军在崖山海战中击败了宋军余部,彻底终结了唐末五代以来长达数个世纪的南北分立局面,完成对全国的彻底统一。与秦朝统一六国的前221年、隋朝灭陈的589年一样,1279年是中国步入大一统时代的第三个关键性时间节点。元朝自觉接续中华正统,实行汉法,延续文官体制,定都大都(今北京)。“胡汉异统,势分南北”变为“混一南北,胡汉一家”。
元朝的大一统,终结了自唐朝后期藩镇割据以来中华大地陷入分裂的状态,极大深化了传统的大一统政治格局,全面开创了“混一南北、胡汉一家”的中华民族发展新局面。这首先体现在元朝借“统一”之机全面深入地调整了中央与地方的纵向关系,在制度层面巩固与深化了大一统成果。最突出的表现是元朝首次在全国版图内普遍建立起内“腹里”而外行省的行政大区制度。
“腹里”是指朝廷最高行政机关中书省直辖的特殊行政大区,大致涵盖了今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全境和内蒙古自治区的部分区域,管辖面积远超此前历代中央政府直属的京畿之地。这种相当于“大首都区”的全新行政区划设置,有助于朝廷最大限度地实现强干弱枝、控驭地方。这对明清时期长期存在的以首都为中心的直隶行政区域,有着直接的影响。
与中央直辖“腹里”相并行,元朝在地方上设立十大“行省”,即遍布南北各地的十个地方级行政大区。其中设置时间较晚的下辖和林路的岭北行省,专司治理漠北草原的相关地区,加上漠南草原的大部分地方已隶属于“腹里”区域,元朝成为中国历代王朝中唯一以相对完整的中原地区行政管理模式管辖草原牧区多地的政权。而之前的汉、唐、辽、金,之后的明、清两代,均未在漠北草原推行郡县制或府州县制等与中原地区接轨的行政管理体制。元朝在草原地区实行的这一体制,增强了北部边疆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向心力。
以和林路元代碑记上的官员题衔来看,当时这里的官署设置已与中原行省趋于一致。在具体的官吏任用方面,同样采取标准的蒙古人、色目人、汉人混用之制。尽管蒙古人或色目人出任高官的比例更高,但基层政务的日常运作与“腹里”地区及其他行省一样,皆由更加谙熟案牍文书起草工作的汉人吏员承担。数量可观的原籍中原的汉人官吏,任职于漠北腹地的基层僚属机构,这在中国以往的历史上实属罕见,甚至以后同样实现了政治大一统的清代也有所不及,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蒙汉群体在国家机器中的交融深度。漠北一带属于中国疆域的事实,也为当时国外多国人士所知晓。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旅行记中郑重记述了哈拉和林位于元朝境内的史实。这从非汉文史料的层面,具体批驳了那种声称蒙古草原始终游离于中国版图之外的荒谬观点。在东南海疆地区,福建行省下属的澎湖巡检司负责治理澎湖列岛与台湾一带,加强了朝廷对东南沿海的管理。
不仅如此,行省体制还具有统合西南各边疆人群的行政职能。朝廷主要在南方一些行省之下设置宣慰司这一特殊的地方机构,具体承担对当地人民的安抚治理。宣慰司之下又设宣抚司、安抚司等机构,构成了相对完备的土司管理体制和由本地族群首领担任官长的土官选任制度。这些制度的推行,使得此前常被视作“喉峒之民”的西南各族,也逐渐承担起向国家上缴少量税赋以及维护官方驿站等义务,逐渐改变了以往此类羁縻民众大多既不见于地方政府的户籍登记记录,也不缴纳赋税的松散管理旧况。
中央政府还在西域和吐蕃地区设立一系列管理机构,对其实行有效管辖。元朝时,西域大部分地区属于朝廷的藩属察合台汗国,但部分地区如吐鲁番盆地则长期由中央政府和察合台汗国共同治理。察合台汗国的政治中心阿力麻里(遗址在今新疆霍城)是元朝时闻名西域的繁华之城,14世纪的埃及史学家乌马里指出其属于中国。
在新疆地区,成吉思汗完成了对天山南北的政治统一。13世纪初,成吉思汗平定了西域诸城,并设立达鲁花赤(蒙古官名,意为镇守官)管辖。1251年蒙哥继承汗位,为加强对西域的军政管辖,他分别在别失八里、阿母河等处设立行尚书省事(蒙古国时期无尚书省,“行尚书省事”系沿用金朝官职称号)对畏兀儿及阿母河以西地区进行军政管辖。元朝建立后,曾在1275年设立阿力麻里行中书省,管辖伊犁河流域;1280年,将高昌亦都护王室东迁永昌,改“断事官”为北庭都护府;1283年分别在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哈刺火州(今新疆吐鲁番盆地)、斡端(于闻)设立宣慰司,分别统辖天山南北军政事务,与当时中原地区的行政建制相似;1295年,元朝设置北庭都元帅府和曲先塔林都元帅府,分别镇护天山南北各地,同年又设置西域卫亲军都指挥使司。这些军政机构的设置,使得新疆地区与中原等地的一体化程度显著加强。为进一步加强对新疆地区的管辖,除设置军政机构外,朝廷还采取了设置水、陆驿站,建交钞提举司、交钞库,设提刑按察司,设哈赞忽咱、哈刺火州(今新疆吐鲁番)总管府等机构的措施。以驿站为例,1274年,在天山以南的于阅(今新疆和田)和鸦儿看(今新疆莎车、叶城)两地设立13个水驿。元朝通过设立这一系列机构,对新疆地区进行了有效治理,使得新疆人民从草原游牧生活逐渐向农业定居生活转变,促进了新疆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中原文化也在新疆地区得到了广泛传播。
从元朝开始,西藏正式纳入中央政府行政管辖范围。元朝在中央设置总制院(后改称宣政院),统管西藏和全国佛教事务,由官列副一品的帝师统领;在西藏地方设立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即乌思藏宣慰司)来管理西藏地方,而在其他藏族聚居区分别设立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即朵甘思宣慰司)和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即脱思麻宣慰司)。元代藏文历史文献中称当时整个西藏地方被划分成三个“却喀”,它们指的就是元代划分的“吐蕃三道宣慰司”,“却喀”是蒙古语借词,它与汉语中的行政单位名称“路”“道”对应。古代藏文史学名著《汉藏史集》(图9-1)中记载,元世祖忽必烈时期,元朝共有十一个行省,吐蕃三却喀(三道宣慰司)虽然地方不足一个行省,但因为它们是佛法兴盛和帝师所居之地,所以也被算作一个行省。元朝的乌思藏宣慰司设治于萨思迦,其最高行政长官在藏文文献中被称为乌思藏“本钦”,他们都是由元中央政府直接委派的朝廷命官,管理其属下的乌思藏十三万户,代表元朝中央政府直接管理乌思(前藏)、藏(后藏)和纳里速古鲁孙(阿里三围)等三路的行政事务。通过中央的宣政院和地方的乌思藏宣慰司、乌思藏十三万户三级行政机构的设置,元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实施了十分有效的行政管理和统治。
为巩固大一统成果,元朝继创制蒙古文字后,又创制并推广适于音写蒙古语、汉语、藏语、畏兀儿语等各种不同语言的八思巴文,使国内人群共享同一套文字书写体系,在国土疆域空前辽阔的全新治理背景下,实现“书同文”的文化政策。八思巴文在音写汉语方面的应用,客观上成为世界上第一种尝试采用拼音字母书写汉语的可行性方案,在汉语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正式使用两种以上书面语言来处理行政事务的朝代,汉语、蒙古语、波斯语都是当时政府正式选用的公务语言。现存元朝官府督造的一些铜权上面就刻有上述不同语言所对应的文字,方便语言背景不同的各族群众共同理解与使用。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发掘的黑水城元朝路一级地方行政文书残叶,多件汉文文书的末尾位置有用八思巴文、蒙古文和波斯文添写的批复指示类词语,反映出公文中多语种交互并用的现象已经在元代统治的地方行政机构出现。
元朝官府机构还保持了一支人数可观的、专门从事不同语言互译工作的译吏队伍,在官方公文的书写方面刻意推广使用一种杂糅蒙汉双语语法特征的全新汉文硬译公牍文体,为蒙汉官员群体切实架起便于沟通交流的语文津梁。
这些措施产生的综合效应极大地促进了国内各族群之间在语言文化上的交往交流交融。以官员群体为例,降至元朝后期,蒙古人、色目人官吏中通晓汉语和汉人官吏中熟悉蒙古语者均有显著增长,随之出现了语言文化上的明显趋同现象。很多情况下,政府中不同族群官吏之间的书面或口语交流已经不必通过译吏而是可以选用汉语或蒙古语直接进行。
元朝皇帝对学习儒家经典普遍持积极态度。自元成宗以来,孔子后裔的政治待遇即呈现逐渐高升的趋势。在元成宗时期,孔子后裔得以享受正四品官员的优厚待遇;到元末顺帝时期,孔子后裔已经是朝廷正式授予的从二品高官。元武宗时期,为了表明对孔子的高度尊崇,更是径直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其享有的政治地位超过了以往历代。
从元朝中期的泰定帝时期开始,专门由汉人儒臣为皇帝讲授传统汉文经史著作的做法,也逐渐成为朝廷定制,并一直延续至元末,此即带有明显“亲儒”色彩的经筵制度。经筵的具体讲授任务固然是由汉人文士担当、但同时也有不少蒙古、色目儒士参与协助。这反映出元朝中后期、包括皇帝在内的蒙古上层人士学习儒家文化的态度更趋积极,在一定程度上从文治层面拉近了元朝与传统意义上的中原王朝之间的距离。上层人士学习儒家文化的热情也影响着边疆其他民族,如出身于西域高昌的畏兀儿人贯云石,就是被誉为中华文化史上“擅一代之长”的杰出人物。他的一首凭吊屈原的元曲名篇《殿前欢·楚怀王》被历代传颂。“楚怀王,忠臣跳入汨罗江。《离骚》读罢空惆怅,日月同光。伤心来笑一场,笑你个三闾强,为甚不身心放?沧浪污你,你污沧浪。”这首小令充分彰显了中华文明特有的忠臣孝子、家国情怀。
许多散居中原的蒙古人、色目人家庭,如畏兀儿人中的廉氏、俣氏等显赫世家,其男性成员均需集中精力学习儒家文化。廉氏家族自布鲁海牙起就注重后代教育,布鲁海牙为其子廉希宪诸兄弟延揽汉儒设教,使之从小就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常年研经习史让廉希宪成为一个廉孝兼具的儒臣,他以忠、孝闻名,享有“廉孟子”的美称。廉希宪在陕西任官时,修筑了藏书万卷的“读书堂”,其子廉恂、廉恒、廉惇在此学习,后来都成为一代名士。俣氏家族自岳璘帖穆尔时,便一直活跃在元朝政坛上,这与他们具有高深的儒家文化素养不无关系。元朝俱氏家族有名号可考者47人,其中有9人是进士;俱哲笃以儒业起家,在江西时兄弟五人同登进士第,一时传为美谈。元朝灭亡后,俱氏后裔便长寿、便斯分别作为高丽和明朝的使者往返两国,为加深双边友邻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与他们家族的儒家文化背景密切相关。
最能反映元代“儒治”取得重要进展的事件,是元仁宗正式恢复此前中断多年的科举取士制度。科举制使部分蒙古及色目军户子弟得以改变人生际遇,客观上促成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社会流动,也给社会地位整体下沉的汉人儒士阶层提供了向上流动的可能。而且,科举制下想要入仕客观上需要较长学习年限,这也推动了蒙古、色目青年子弟对儒家文化的深入研习。各族士子求学应试的过程,也深化了蒙古、色目士人与汉人老师、汉人同窗学侣之间的交往与友谊,最终通过科场应试建立了足以削弱族群藩篱的人际关系网络,淡化了原本存在的族群隔阂,培育了具有共同文化理念的多族群士人圈。如元朝后期著名的色目进士马祖常入仕后,即推荐同年汉人进士黄溍入京调任翰林应奉。因此,尽管元朝的科举制度本身存在着若干缺陷,但是科举依旧为家世出身不同却共同爱好儒家文化的各族文士提供了平等交往的基础和维系友谊的纽带。这也反映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在元朝随着国家大一统与科举制度的恢复,较前朝有了更加深入的发展。
除儒家外,元朝皇室还对释道文化加以包容礼遇,与释道两教的上层人士建立了密切联系。华北地区禅宗高僧海云的侍者刘乘忠,曾被忽必烈相中并留在身边。他在确定大元国号及规划元大都设计蓝图等重大事宜上发挥了关键作用。元朝对儒释道的开明态度推动了三教合流思想继续向前发展。
元朝还从政治层面大力推动汉文经典著作的蒙古文翻译工作。由朝廷正式出面组织翻译完成的此类著述,经部有《孝经》《大学衍义》及其节本以及《尚书》节本,史部更多一些,有《资治通鉴》《通鉴节要》《贞观政要》《帝范》《世祖圣训》《承华事略》等。《承华事略》最初是汉臣为忽必烈的皇太子真金撰写的,到元朝中期又由马祖常翻译润色。这种史书著作系统地被翻译为蒙古文的政治文化现象,折射出元朝统治者迫切期望从历代盛衰兴亡的史实中汲取经验教训,彰显了其始终以中国之主自居的认同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