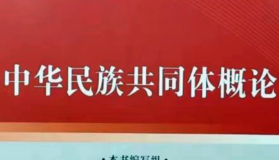-
1 授课视频
-
2 章节测验
大一统政治体制的重构,强化了不同区域间的经济联系,消弭了地理环境造成的族群区隔。各族群通过陆上及海上丝路贸易拉近距离,联系日益密切。具体表现为兼容内外的经济制度、全面开拓的贸易网络与共生共荣的商路贸易,呈现出“华夷共生”的特征。
隋末唐初,连年内乱导致人口锐减,经济凋敝。为恢复社会经济,唐武德七年(624),颁布了均田令和租庸调法,以促进生产及保证租税的收入。唐之均田令规定:“凡天下之田……度其肥瘠宽狭,以居其人。凡给田之制有差。”均田制承认农民对无主土地的合法占有,也使那些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可向国家请受荒田,进行耕种,推动了北方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租庸调法是一种以征收谷物、布匹以及为政府服劳役为主的赋役制度。
作为隋朝与唐前期的基本经济制度,均田制和租庸调制被沿用和发展,并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行,包括岭南与西域等边疆地区也能迅速实行。隋唐两代均在政治上追求华夷同轨、经济上力图海内为一,制度也随之继承并不断调适。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推行极大地推动了北方内迁各族从游牧向农耕转化。《唐律疏议》对于唐代的均田有详细的记述。敦煌吐鲁番文书有关于户口和受田、退田的记载,从这些文书所登记的“合受田”“应受田”数额来看,均与唐《田令》所规定的“狭乡”受田标准相符,可证明均田制在西域地区推行(唐朝平定期氏高昌之后设置西州,并颁布均田令)。同时,吐鲁番出土唐代户籍文书中每丁应输纳的租税数额与唐《赋役令》的规定一致,证明唐朝赋役令也在西域得到执行。
这一时期,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推动了南北之间的经济交融。秦汉时期,中华文明的政治和经济重心主要在北方黄河中下游流域。魏晋南北朝“五胡”入华时,中原人口逐步南移。隋朝统一江山后,政治军事重心仍旧在北方,而南方的经济地位日益显著。隋文帝为了解决关中粮食欠缺问题而开凿广通渠,引大兴城(今陕西西安)西北渭水东流至潼关入黄河,隋炀帝时改名为永通渠。为了统一陈朝的军事行动,隋朝还开凿了山阳渎。隋炀帝将通济渠、邗沟、江南河和永济渠凿通连为一体,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水系,形成历史上著名的隋唐大运河,成为名副其实的南北交通大动脉。修建大运河在隋代发挥的主要是政治与军事功能,但其客观上促进了南北经济交往,“商旅往还,船乘不绝”。运河两岸商业都市兴盛,为其后的商业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大运河连通了中华大地的几大水系,形成水运兴盛的空前景象,“且如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触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南北经济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加速。
在北方,“以木桶相连,汲于井中”的水车已经开始应用于农田灌溉。南方鱼米桑茶的水乡文化传入了北方和中原。北方草原游牧文化也对中原和南方产生了影响。原因在于,中原的农业手工业生产与北方的畜牧业有着强烈的互补性。中原稳定地产出粮食、布帛、茶叶以及各种手工业制品,但不适合大规模养马;草原则主要以牲畜产品为主。中原因军事、国家邮驿系统和民间交通的需要,使马匹成为农耕社会与游牧社会之间极为重要的交换商品。唐朝与回纥进行了大规模的绢马贸易。自乾元(758—760)之后,回纥“屡遣使以马和市(指官府向百姓议价购买货物)缯帛,仍岁来市,以马一匹易绢四十匹,动至数万马”。尽管大规模的绢马贸易给唐朝国家财政带来负担,却维护了唐、回纥、吐蕃三者关系的稳定以及北部边疆和平。除绢、马之外,茶也是各族人民交易的重要商品。唐代茶叶生产已经有了相当规模。饮茶之风盛行,可见陆羽撰写的《茶经》。《新唐书·陆羽传》载:“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五代时期,南唐曾与契丹进行过大规模贸易,938年,契丹“别持羊三万口、马二百匹来鬻,以其价市罗、纨、茶、药”。今四川地区的前蜀也在汶、黎、维、茂等多州购买吐蕃等部的蕃马。蜀中的茶饼还广销党项夏州(今陕西靖边县一带)等地,受到各族人民喜爱。
隋唐时期,周边政权通过朝贡贸易加强与中原政权的经济联系。唐朝时期,各族使者、商贾前往长安朝贡贸易者络绎不绝,深化了游牧经济与中原农耕经济的互融(图7-7)。全国经济贸易网络随之开拓,陆路与水路贸易并盛,隋唐社会经济一体化趋势大大增强。
646年,唐太宗北上举行了规模宏大的“灵州盛会”,会见了敕勒诸部首领及使者。唐太宗的真诚之举促使漠北各部主动内附,它们以能受到唐太宗册封为荣。灵州大会上,西北番邦请求尊奉唐太宗为“天可汗”,以表对唐太宗的尊称和拥戴。这表明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族群诸部在血缘、地缘、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上进一步交往交流交融,有助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进一步发展。
“参天可汗道”是由回纥等草原族群主动要求开辟的。“天可汗”制度是一个以唐朝为中心,以中央集权制为支撑,覆盖周边诸族、藩属与邻国的天下体系,实现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政治整合与社会交融,融华夷为一家,进而将整个东亚世界塑造为中华文化圈。“天可汗”不仅是一种称号,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治理秩序,是唐朝统领四海万邦的重要象征。唐朝皇帝通过册封、藩国入质、入觐、朝贡等方式实现对周边藩属政权的间接统治与羁縻控制。藩属与朝贡国的君主即位,必须得到“天可汗”的认可。
在这条道路上,唐朝共设置68个驿站,各驿站配备马匹和食物,方便驿使高效通往。《新唐书·地理志》明确记载了唐朝通往回鹘的若干线路:“中受降城正北如东八十里,有呼延谷,谷南口有呼延栅,谷北口有归唐栅,车道也,入回鹘使所经。又五百里至鹏鹑泉,又十里入碛,经腐鹿山、鹿耳山、错甲山,八百里至山燕子井。又西北经密粟山、达旦泊、野马泊、可汗泉、横岭、绵泉、镜泊,七百里至回鹘衙帐。”另外一条线路:“自鹏鹑泉北经公主城、眉间城、怛罗思山、赤崖、盐泊、浑义河、炉门山、木烛岭,千五百里亦至回鹘衙帐。”由此,位于今内蒙古草原北部的回纥(788年改称回鹘)等族群能够直达长安协商采买,也可以前往唐朝在河西地区和边地设立的马市直接交易。
7世纪初,居住在娑陵水侧的回纥联合仆固、同罗、拔野古等部族,摆脱突厥统治,逐渐强大起来。646年,回纥部首领吐迷度自称可汗,接受唐朝的管辖。唐在漠北设瀚海都护府,并将漠北诸游牧部落分置为六府、七州,受燕然都护府管辖。744年,回纥部首领骨力裴罗自立为可汗,后又受唐朝册封为怀仁可汗,建立漠北回纥汗国。840年前后,回鹘可汗被黠戛斯所杀,汗国瓦解,诸部离散,其中一部分南下降唐,其余西迁。西迁的一支到达河西走廊一带,称河西回鹊,又名甘州回鹘,后来与河西的族群相融合,发展成为今天的裕固族。西迁回鹘的主体则建立起了以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为中心,东抵伊州(今新疆哈密)、西至龟兹(今新疆库车)、南达于闻(今新疆塔里木盆地一带)、北越天山的西州回鹘政权。他们就是今天维吾尔族的先祖。
唐代经济的繁荣,赢得了整个东亚社会的关注。在唐朝近三个世纪的统治中,绝大部分亚洲国家都曾遣使入唐(图7-8)。
随着不同地区间经济贸易往来互动,边疆地区逐步形成诸多贸易点,如东北的幽州(今北京、河北一带),西北的凉州(今甘肃武威)、沙州(今甘肃敦煌)、西州(今新疆吐鲁番),西南的益州(今四川成都)等,均是连接中原与周边地区经济的重要枢纽。从“点状”贸易到多条商路的“线形”延伸,四通八达、纵横交错的道路网勾勒出隋唐丝绸之路的基本格局。在各族互动交往中,这些交通线路以中原腹地为中心,是唐朝与外部世界物质、文化、信息交流及传输的经脉。
在陆上丝绸之路通往中西亚的干道上,沙州、伊州、西州、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轮台(今新疆轮台)、弓月城(今新疆霍城西北)、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等成为主要贸易聚点。伊吾道、阳关道、莫贺延碛道、青海道等路线上,伴随边疆诸族的归附,远慕华风而奔赴者不可胜计。
在西南地区有五尺道和旄牛道,它们蜿蜒于西南的崇山峻岭之间,以蜀地的中心益州为起点,一东一西南下经云贵高原出缅甸、抵印度。汉唐以来,朝廷数次疏通与修筑、维护,动员巴蜀之民拓展了原有的民间路径,还开通千里官道。随着丝路的通行,夔、滇、离、夜郎、濮等西南族群更深地融入中华文化,学习和接受中原的生产技术、社会习俗。另外,唐朝还通过营州—渤海道连通东北各部,进而通往新罗、日本。
大运河的开凿不仅推动了南方社会经济发展,也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唐代海上丝路以东海和南海航线为主。东海航线主要连通东亚诸国。隋唐时期,日本多次派出使节团、留学生、留学僧等,均是从海路进入中国。南海航线主要是从广州出发,经南海、马六甲海峡、印度洋,抵达大食(今阿拉伯半岛)等地。伴随海路贸易的发展,岭南承接江南、西南、北方带来的货物、人力,并以优良的海港如广州港、泉州港、合浦港等,开展对外贸易,丝绸之路、瓷器之路、香料之路无不与之关联。
贯穿岭南的商路沿线出现大量僚市、马会,定期举行的通商活动,让当地的族群更多地接触和融入华风。各族商贾得到招徕与认可,移舟行船前来贸易,为海上丝路贸易注入活力。各族群的共同参与创造了岭南珍宝辐较、商贾云集的新面貌;丝路贸易的繁荣也推进了南方诸族的社会进步与经济飞跃。
隋唐五代时期,丝路贸易形式多样。丝路贸易从来不是由一个国家或某一个族群单独完成的,中华民族的成员如突厥、回纥、吐蕃等都曾参与了丝路贸易,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各族群通过丝路贸易拉近彼此距离,各区域间经济交流日益密切,呈现出“华夷共荣”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