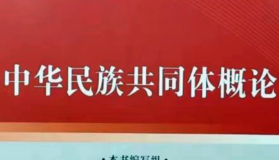-
1 授课视频
-
2 章节测验
“五胡”政权兴起与纷争导致了更大范围的大迁徙、大交融、大编户。随着社会组织重组和社会结构的大调整,人为的区隔被冲破,族群交融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
在北方,胡人南迁中原,带来了游牧族群的部落体制,深刻改变了北方社会的阶层结构与基层组织结构。胡人部落组织“落”逐渐遍布中国北方,其统帅被称为“部落大人”,逐渐转化为豪强酋帅。
汉末以降的乱世中,边郡汉人往往投奔胡人部落寻求庇护。鲜卑首领慕容庞将很多汉人士族吸纳到统治集团中,以河东裴疑、代郡鲁昌、北平阳耽为谋主。北方胡汉族群因各种经济政治需要,相互学习借鉴对方的制度和文化,形成胡汉交融的社会。
北魏实行了一项至关重要的“离散部落”政策,即解散部落组织。天兴元年(398),北魏攻打后燕取得大胜,在代地大范围解散部落民,使其“分土定居,不听迁徙”,部落大人“皆同编户”。拓跋珪在登国元年(386)改称魏王后不久,北魏就实行了“散诸部落,始同为编民”,后又数次针对不同群体实行了类似政策。这一政策试图使各部落大人与其部民(牧民)脱离关系,使牧民由部落成员转变成为国家的编户,定居、分得土地以从事农耕或定居牧放,不得随便迁徙。基于血缘的氏族转变为基于地缘的编户。由此,北魏加强了中央集权,开拓了财源和兵源,各族群胡人旧有的社会关系也被重组,使前秦苻坚那种一场战役失败后部将即各奔本族、独立称王的局面不复重演。
东汉末年以至南朝,各政权在其所经营区域不断推进“蛮夷”部落的郡县化与编户化。同时,“蛮人”酋帅官僚化的趋势也不断推进,带动了“蛮夷”部落风俗的华化与族群融合。
一方面,南方行政的一体化体现为南方“蛮夷”部落地区的郡县化、编户化与“蛮人”酋帅的官僚化。战国秦汉时期,“蛮夷獠越”广泛分布于江淮以南至岭南珠江流域。东汉时,朝廷曾强行将部分“蛮夷獠越”纳入郡县管理,增重赋税与兵役,引起武陵蛮长期反抗。三国时期,蜀国与吴国的统治范围深入“蛮夷”部落地区。诸葛亮经营南中(今贵州西部、四川西南部和云南大部),采取怀柔方式,将孟获等西南夷首领接到益州任职;将南中“蛮夷”编为部曲,颇多北移蜀地及汉中。东吴立国江东后,频频将收服的山越迁至平地,“强者为兵,赢者补户”,使山越由山中聚落转变为郡县编户下承担兵役和徭役的自耕农。此后,南朝继承这一政策,因地制宜,因俗而治,在“蛮夷”聚居地保持部分部落或聚落组织,任用其酋帅,设置宁蛮府、左郡左县、俚郡、僚郡等特殊政区进行管理。
南方族群实现编户化、郡县化,对推动“蛮户”与汉人文化融合、风俗教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推动了蛮、汉基层民众的社会交融。经长期交融,“蛮人”与汉人风俗文化已无别。以荆州蛮为例,“其与夏人杂居者,则与诸华不别”。郡县化又推动了“蛮人”酋帅的官僚化。东吴、东晋与南朝在“蛮人”聚居区所设州郡县的各级官吏,有相当多是由当地酋帅担任,每一个任官的酋帅都会建立与汉人豪强类似的记载家族组织与家族世系的族源叙事,谱写家族迁徙的历史,如《爨龙颜碑》(图6-4)所载家族信息。南方族群还与汉人进行频繁通婚,如高凉洗氏世为南越(俚人)诸部落首领,南朝萧梁大同(535—546)初年,罗州刺史冯融为其子高凉太守冯宝聘洗氏女为妻。在之后的梁、陈与隋朝,洗夫人为俚汉融合与南越开发,为在海南岛俚人地区设立中原郡县制起到重要作用。长期郡县管理促使蛮汉杂居交融。侯景之乱后,江南土豪酋帅作为新兴的政治势力登上历史舞台,成为支持南陈的力量之一,实现了与中国统一历史大势一致的融合。
另一方面,南方行政一体化还体现在侨州郡与本地州郡户籍的统一上。东汉末至东晋时,大量北方汉人为躲避中原战乱与饥疫,向南方迁徙。从西晋永嘉年间(307—312)至刘宋,南渡人口约有90万人,占刘宋编户人口的六分之一。他们或在世家大族的统率下迁往会稽等江浙地区;或在“行主”“流民帅”的带领下,去往江西、湖南。一旦定居,世家大族与“流民帅”就会转化为地方豪强,很多流民依附其下,成为荫户、私属与部曲。同时,南方族群的酋长,也会转化为地方领袖。凡此豪强大族的力量,与国家争夺人口与税源,造成国家行政的分割。
东晋南朝为了安置北方迁移过来的流民,在其定居之地按其原籍设立侨州郡,
给予赋役优惠,穿插于当地行政疆域之内。侨州郡分布在荆、襄、梁、益等地,与南方“蛮夷”部落交错杂居。但北来流民归属于“白籍”,不受所居住地方的行政管辖,与原来在此居住的人口(归属于“黄籍”)形成人为的区隔。东晋及南朝宋、齐、梁、陈各代多次推行土断政策,厘正户籍。所谓“土断”,就是将侨郡县的人口划归所居住地方的编户之下,打破“白籍”与“黄籍”的分割,统一户籍。土断政策清理出被大族荫庇的大量户口,削弱了世家大族的力量,也推动了外来移民、本地居民与南方族群的融合。
汉魏之际北方长期战乱,人口锐减,内迁胡人数量与分布范围持续扩大。曹魏幽州刺史册丘俭征伐高句丽后,将部分高句丽人迁到河南荥阳,“户落百数,子孙孳息,今以千计”。至西晋泰始年间,山西匈奴“户至数万,人口之盛,过于西戎”。西晋元康九年(299),作为氐羌重要内迁地的关中,胡汉人口比例已达到“戎狄居半”的程度。鲜卑各部从长城沿线向南迁徙,拓跋鲜卑占据漠南,向山西北部发展;慕容、段氏、宇文等东部鲜卑占辽西、辽东及河北北部;吐谷浑、秃发、乞伏鲜卑部迁到青海、河西、陇西等地。根据粗略统计,东汉到南北朝时期,包括“五胡”在内的南北方众多族群共计内迁1136万人。
“五胡”政权实行的人口政策,是更彻底的大迁徙、大融合、大编户。其大规模移民多达50余次,数量动辄百万,且都是在核心区域。匈奴之刘汉,迁徙了63万户汉、氐、羌人到首都(平阳、长安);羯人之后赵,迁徙了几百万汉、乌桓、鲜卑、巴、氐、羌等人口,将其安置在各个政治军事重镇。鲜卑之前燕,迁移了段氏、高句丽、宇文部等,人口由是激增。氐人之前秦,把远方的鲜卑、乌桓、丁零等大量人口迁至根据地关中,又将关中氐人15万户迁至关东“散居方镇”。羌人之后秦则将各地流人及雍、凉等边地人口迁往关中,达百万余口。
人口的迁移不是单向的胡人南下,北方汉人为躲避战乱灾疫,也大量北迁(如辽西、辽东)、西迁(如河西)与南迁。自东晋南朝以来,南方“蛮人”逐渐从山谷出居到江、汝、淮、颍之间,与汉人杂居。例如,豫州蛮从南郡迁至汉水下游,渐推移至庐江(今安徽庐江西南)。荆、雍州蛮原居于长沙、武陵(今湖南常德一带),后渐北上荆、雍州,分布于陆浑(今河南嵩县东北),逼近洛阳近畿等地,他们在与汉人的杂居交往中逐渐融合于汉人之中。
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导致各族群杂居错处,使得各族群日常生活相互影响,如汉人由席地而坐改为据案坐椅。族际通婚实现了胡汉、蛮汉的交融,北朝皇室与汉人士族、鲜卑上层贵族之间的频繁通婚尤为典型。1965年,大同发掘的北魏司马金龙夫妇合葬墓(图6-5)出土了三块墓志,提供了司马金龙家族与鲜卑勋贵三代通婚的证据。
北方胡人入主中原以后,无一例外地接受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原文化传统,并十分注重对西域地区的经营与治理。西域在加强“华化”的进程中,也对中原文化产生重大影响。
19世纪末以来,新疆地区陆续出土大量魏晋时期儒家经典与史书汉文写本残卷(图6-6),包括《诗经》《诗毛氏传》《尚书孔传》《礼记》《春秋左传》《孝经》《论语》《战国策》《三国志》《晋书》《千字文》等纸质写本残卷,印证了古代西域地区与中原地区密切的文化交流交融盛况。
新疆地区出土如此众多魏晋时期的汉文经典写本残卷,归因于十六国北朝时期中原王朝(如前秦)与河西地方政权(前凉、后凉、北凉、南凉、西凉)对西域的大力经营与有效治理。如《论语》《春秋左传》等儒家经典写本残卷的发现,印证了“五胡”政权在西域推进儒学教育的盛况;《千字文》写本残卷(图6-7)的发现,表明新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启蒙教育多有相似;《三国志》写本残卷的发现,表明它在成书不久后便被传抄到西域,彰显了中原文化影响的深度和广度。
西晋灭亡后,原属西晋的河西四郡转变为前凉,其由忠诚于西晋的凉州刺史张轨建立。在前凉经营之下,河西安定,吸引大批汉人士族前往避难,使河西保存了一脉魏晋文化。陈寅恪说:“西晋永嘉之乱,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至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输入于魏,其后北魏孝文、宣武两代所制定之典章制度深受其影响。”前凉于327年在今新疆吐鲁番地区设置高昌郡,这是中原的郡县制第一次在西域地区出现。楼兰古城出土的李柏文书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中国纸本书信实物(图6-8),证实了前凉经营西域的历史,也证实了郡县制在西域地区推行。前凉之后,后凉、西凉、北凉也先后在高昌设郡,尤其是西凉和北凉灭亡后,其遗民都把高昌作为避难之所,大批河西民众移民高昌。442年,北凉沮渠无讳率领万余家弃敦煌,西迁至高昌。在西迁的移民队伍中、有大量河西的汉人大族与官僚,如敦煌张氏、宋氏、索氏、夏侯氏等汉人大族望族。
5世纪中叶至7世纪中叶,新疆吐鲁番地区出现了四个汉人创建的政权,分别是阚氏高昌、张氏高昌、马氏高昌及魏氏高昌。高昌逐步成了汉人的聚居地,人口不断增加,农业生产和经济文化日益繁荣,族际通婚现象明显增多。高昌与中原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日益密切,且深受中原儒家文化影响。例如《北史·高昌传》记载:“(北魏)明帝遣假员外将军赵义等使于嘉(高昌王掬嘉)。嘉朝贡不绝,又遣使奉表,自以边遐,不习典诰,求借《五经》、诸史,并请国子助教刘燮以为博士。明帝许之。”“(高昌)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从已发现的汉晋时期的遗址来看,除去烽燧据点外,其他遗址如罗布泊遗址、尼雅遗址,都曾发现中原移民和当地人交错杂居的证据。
中原民众,包括到西域的汉人、屯田将士,他们的大量西迁带来了先进的农具、农作物和牛耕技术,西域的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同时,西域诸国大多能够自觉寻求和接受中央王朝的册封和赏赐,还“遣子入侍”,将王子派到中原学习先进的文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地区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中转站与战略要冲,成为佛教传播到中原的必经之地,也成为东西方文化交融荟萃的中心。不仅众多高僧大德经由西域到中原弘扬佛法,大量的佛经也是经由西域传译到中原地区的。而且,佛教从南亚、中亚等地传入西域后也已经开始本土化。西域地区成为佛教中国化的起始地,也是汉传佛教向中亚地区传播的中转站。在这一时期,龟兹、于闻、疏勒、高昌成为西域四大佛教中心。尤其是疏勒(今新疆喀什),连接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和波斯及地中海等文明,成为佛教东传的必经之地,是古代印度佛教东传中国的第一站。当时,疏勒佛教兴盛,盛行上座部佛教与汉传佛教,名僧云集,讲经说法,造塔建寺。莫尔寺就是此一时期佛寺的重要代表(图6-9)。
胡人统治者推崇儒学,也重视律学与法制建设。按照儒家的标准教育选拔人才,使大量汉人儒生自觉自愿地与这些胡人政权合作,促进了儒释道文化的交融。
十六国北朝胡人统治者“或亲临讲试,或建坛宫中,虽旦夕小朝,兵戈云扰,而文教之盛,转胜江东”。例如,后赵石勒称王后,建社稷,立宗庙,起明堂、辟雍,署汉人为经学祭酒、律学祭酒、史学祭酒,并且亲临各类学校,对学生进行测试,按成绩给予奖赏。苻坚“博学多才艺”,谙熟汉人历史典籍,每与群臣论对,常随口引用历史典故,曾巡视太学,“问难五经,博士多不能对”。后秦姚兴立律学于长安,“召郡县散吏以授之,其通明者还之郡县,论决刑狱”。他也经常亲临咨议堂“听断疑狱,于时号无冤滞”。孝文帝元宏在北魏诸皇帝中汉文化素养最高,史称其“雄才大略”“经纬天地”。据《魏书·高祖纪》载:“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老》,尤精释义。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领,任兴而作。有大文笔,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北周文帝宇文泰也崇尚儒术,对儒家治国要旨识见明睿。北周武帝宇文邕不仅精于儒学,还通佛、道经义,曾两次召集百僚和沙门、道士等,亲讲《礼记》。
在律学与法制上,魏晋实现了重大进展。汉律还存在着律令不分、礼律杂糅的问题,即刑律、行政法规和礼乐制度交错杂糅,在部类划分上界限不清。魏明帝时制成魏律18篇,将刑法条文内容尽数纳入其中,晋武帝时又制定了《泰始律》20篇,由此使“律”的内容集中于刑律,行政制度的内容另行置于“令”,即《晋令》40卷中。由此,“律”是刑法,“令”是行政法,二者性质被清晰界定。魏晋“律令分途”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然而,在法治思想上,北魏律也深受汉代以来儒法合流趋势之影响,遵循汉魏以来礼法结合的精神,具有鲜明的礼的色彩,符合魏晋儒家系统引礼入律之典型特征。如其所规定之存留养亲制度、以“不道”罪禁同姓为婚制度等,体现了法制建设上的胡汉交融。
佛教进入中国后在胡人政权中大为流行,同时与儒家忠孝伦理发生冲突,开启本土化、中国化的进程。佛教主动与本土儒家、道家思想相适应,借用道教“自然”“真人”“道”等术语翻译佛经概念(如“空”“佛”“菩提”等),造成此一时期“格义佛教”之发展。石勒、石虎对西域胡僧佛图澄倍加尊崇,佛图澄用异能方术与因果学说不断劝二石效“王者”行“德化”。鸠摩罗什是这一时期佛教中国化最为关键的人物。鸠摩罗什出身天竺望族,十几岁就已四处讲经,名闻西域诸国;20岁时受“比丘戒”,正式成为佛教僧侣。史载,鸠摩罗什“道流西域,声被东川”,声望远播中原与江南。401年,鸠摩罗什历经艰辛来到长安,建立译场,译佛经数百卷。他和南朝真谛、唐朝玄奘并称为我国佛教三大翻译家。谙熟汉语的鸠摩罗什开创了“质而不野,简而必诣”的意译方法,成为佛经汉译的典范,为佛教中国化初奠基础。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小水长流,则能穿石”,富含汉语典雅韵味。鸠摩罗什翻译的经典许多都成为佛教文学的精品,如《金刚经》等。
此一时期,南北政权隔江分治,但南北佛教交流从未中断。后赵灭亡后,佛图澄弟子道安一路弘法,南下襄阳,首次提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道安的弟子慧远南下庐山东林寺传法,慧远弟子道生又北上长安向鸠摩罗什求学。佛教各大宗派主要在这300年中创立,经过多番曲折,初步理顺了佛教与政权的关系,确立了“政主教从”;初步理顺了佛教观念与伦理观念的关系,从此因果与孝悌没有矛盾;初步理顺了佛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为日后禅学与理学的发展开启先声。
在与佛教竞争中,道教也吸收、借鉴了佛教在教义、仪式、僧团组织等方面的经验,结合道家哲学与民间信仰,形成了道教完整的体系。道教并非仅仅是汉人的宗教,其信众还包括胡人、“蛮人”族群。“南蛮”、氐、羌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道教影响。道教的初创和传播,与长江流域的“板栖蛮”“盘瓠蛮”“廪君蛮”有较大的关系。“汉末,张鲁居汉中,以鬼道教百姓,资人敬信巫现,多往奉之。”东汉顺帝时,张陵入巴蜀地区传教,在“板橘蛮”中传道,经张陵、张衡、张鲁祖孙三代经营,数十万“板橘蛮”皈依了道教,巴地成为五斗米道中心。建安二十年(215),曹操平定汉中,将资人迁徙关陇地区,五斗米道随之在更广大的范围内流播。道教在秦陇地区的氏、羌各族中也有广泛的传播.这可以《北魏荔非周欢道教造像碑》为证。碑文中出现的主要供养人题名多为荔非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活动在关中地区的羌族部落。
随着各族群交往的日益深入与密切、佛教、道教成为多族群共享的宗教信仰。宁夏固原出土的北魏墓葬漆棺画(图6-10)展现了儒教孝行图,汉人士族形象,东王父、西王母、天河等道教元素和佛教人物形象以及鲜卑人游牧狩猎图等儒释道多族群文化交融的场面。
当然,文化交流从来不是单向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汲取、相互涵化的。鲜卑入主中原,将粗朴的草原文化带入中原农耕文化圈,两种文化激荡碰撞、互相汲取。在文学领域,魏晋南北朝时期诞生了族群文化融合的结晶《敕勒歌》和《木兰辞》等千古绝唱。民歌《敕勒歌》赞美了漠北阴山草原景色与游牧生活。现可见的歌辞文本乃东魏时敕勒人斛律金奉高欢之命而唱。“其歌本鲜卑语,易为齐言,故其句长短不齐”,是用汉语译写北方胡人诗歌较早的优秀作品,流传极广。脍炙人口的《木兰辞》,作为汉语五言长诗,是孝文帝迁都洛阳实行改革,研究正音,锐情文学,在族群交融的土壤上开放的一朵奇葩。其风格刚健,气概豪迈,词兼胡汉(“天子”“可汗”并用),反映了北方各族妇女的英雄气概。北方民歌以其质朴刚劲之风对文学影响深远,促进了隋唐北方粗犷豪迈、雄奇刚健与现实主义的诗风的发展。
在乐舞方面,“戎华兼采”,胡乐对中原地区影响深远。胡笳、羌笛、琵琶、竖箜篌、羯鼓等胡乐器及胡曲在中原民间广泛流行。晋室南迁后,清商乐发生变化,形成“陈梁旧乐,杂用吴楚之音,周齐旧乐,多涉胡乐之伎”的现象。龟兹乐和西凉乐对我国北方音乐影响很大。皇亲贵族都酷爱龟兹乐舞,北齐文宣帝高洋在演奏龟兹乐时,甚至亲自击鼓伴奏。北齐的《兰陵王入阵曲》与北周的《城舞》是北方族群融合的艺术结晶,对后世戏剧等产生了一定影响。此外,胡舞、胡戏等对中原文化的影响也很明显。
在语言方面,南北汉人日常用语中时而杂有胡语或夷越之音。在书法方面,魏碑上承汉隶传统、下启唐楷新风,为现代汉字的结体与笔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雕刻和绘画艺术上,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敦煌莫高窟等佛教塑像、壁画与北朝胡人墓葬壁画等,融合了中原儒道文化、中原建筑风格、青绿山水画
风与游牧生活场景、佛教信仰等多种元素。如云冈石窟即为多种文化融合的典范,先是凉州僧匠带来西域风格的佛教造像艺术,之后是县曜建议征集全国各地宝像于京师,最后是徐州僧匠北上主持云冈佛事,各族群共同创造出云冈石窟这座旷世无双的佛教艺术殿堂。而云冈石窟的佛教造像艺术融汇了鲜卑、汉以及中亚文化的精髓,成为各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晶。
此外,北朝胡人墓葬壁画也鲜明生动地反映了中西文化交融、多族群文化交融的盛况。陕西西安发现北周大象元年(579)去世的同州萨保安伽墓,出土有安伽的墓志和一套完整的围屏石榻,围屏上刻画着12幅贴金彩绘图像(图6-11)。墓主人安伽是从凉州武威迁到关中的安国粟特人(安姓为昭武九姓之一),他最后官至同州(今陕西大荔)萨保。萨保即商队与聚落的首领、兼任宗教领袖。安伽的墓志与墓葬壁画反映出他已经高度本地化与“华化”,如《安伽墓志》载“其先黄帝之苗裔,分族因居命氏”,显示他已自认为黄帝子孙。此外,还有北周史君墓、北周康业墓等来华粟特人的墓葬信息也显示了当时多族群文化交融的盛况。
魏晋以来,大量北方族群南迁,深入中原地区,突破了“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地理珍域,打破了“裔不谋夏,夷不乱华”的中心与边缘的分布格局。为解决“自古无胡人为天子者”这一根深蒂固的观念,掌握政权之后的胡人君主主动认同华夏祖源,确立了脉络清晰的“夷夏同源”历史叙事。
建立“汉国”的匈奴后裔刘渊,以汉室之冑自居,建国号为“汉”,祭祀的祖先是自汉高祖以下的“三祖五宗”。同为匈奴后商且与刘渊同族的赫连勃勃自认为夏后氏,“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而称为“大禹之后”,立国号为“大夏”,宣称要“应运而兴,复大禹之业”。慕容鲜卑自称“有熊氏之苗裔”。拓跋鲜卑追认祖源为黄帝之子昌意,“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建立前秦政权的氐人苻氏自称为“有扈氏之苗裔”,而有扈氏乃大禹之后。建立后秦政权的羌人姚氏自称“有虞氏之苗裔”,而有虞氏则为“舜少子”。北周宇文氏自谓出于炎帝神农氏,只不过神农氏被黄帝打败之后,其子孙只好遁居北方草原地区。东魏时期,柔然王室后裔在族源认同上自诩为轩皇苗裔,认同是黄帝轩辕氏后裔华夏一员。除北方胡人外,南方“蛮夷”也主动认同炎黄后裔,书写其族群起源历史。《华阳国志》记载“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表明蜀与巴均认黄帝为祖先。在该书《蜀志》之末,常球在对蜀地之赞词中称“故上圣则大禹生其乡,媾姻则黄帝婚其族”,更反映了此时代的蜀人认同中,黄帝、大禹都是值得骄傲的历史记忆。
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内迁族群通过族源寻根,将本族起源追溯至炎黄,展现了接续中华文明正统、融入中华文明大家庭的自觉与认同。夷夏同源的历史叙述,也有效地弥合了内迁族群与本地族群之间的界线,使得中华文明容纳的族群范围进一步扩大,天下一家的文明气魄更为恢廓,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不仅如此,胡人所建政权在史书撰写方面,也多承中原王朝修史传统,体例包括“记”“录”“起居注”“国志”“国记”等。最重要的著作是北魏崔鸿撰写的《十六国春秋》。崔鸿在十六国政权各自撰写的国史和起居注等基础上,辨析真伪、去粗取精、除繁补缺,最终写成一部记载十六个政权历史的史书。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曾命邓渊修史撰《国记》十余卷、未成,太武帝拓跋焘又命崔浩、邓颖等续修,成《国书》三十卷,孝文帝拓跋宏也命李彪、崔光修史……这些修史活动为后来魏收等编撰《魏书》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这些政权不仅继承了王朝修史传统,也通过国史书写,将自身政权与中华政制相接续。在这种历史叙述下,胡人、“蛮人”实现了华夏身份的自我认同与共祖追溯。
小结
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方面,战争频仍,生产破坏,人民流离失所,饱受战乱之苦。另一方面,不同族群之间离散聚合、交错杂居,族群融合在规模、深度和影响上却是空前的。近370年30余个大小政权兴替,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胡”族群大规模南下中原,中华文明实现了长城边缘地区与中原农耕地区的一体化整合,巩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基本格局并塑造了“华夷一统”的政治传统。
经过此一长时期的族群融合,周边族群融汇于中原的内聚性更加强烈,族群碰撞、交流与融合的程度更为剧烈,北方汉人与胡人逐渐融合,百越以及西南部的居民与南下汉人的文化与血缘交融也在深化。匈奴、鲜卑、羯、氐这些曾经在历史上叱咤风云的族称,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逐渐消失了,但这些族群及其文化早已融入中华民族之中,彰显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形成特点。这样的大交融,不是一方同化另一方,而是双向涵化与多方互化。魏晋南北朝时期正是各族群相互涵化,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