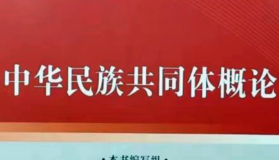-
1 授课视频
-
2 章节测验
秦汉时期,伴随着“书同文”政策的推行,百家思想汇流于儒,华夏文化认同得以奠基。中原文化向周边地区广泛传播,对各地文化交融发展起到了主导作用。周边族群的文化、艺术、习俗、生活方式也传入中原,塑造了秦汉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在这一复杂的历史进程中,大一统王朝不是简单地“以一化多”,而是集区域和族群的多元特征于“一体”,再以“一体”去融汇“多元”,进一步拓展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发展格局。
秦代是汉字发展成熟的关键期。古文字经过长期发展演变,到战国时期,由于诸侯国各自为政,“文字异形”现象比较严重。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下令“书同文字”,统一全国的语言文字,规范字形、用字、用语体系。
以秦系文字取代六国文字,是“书同文”政策最重要,也是最见成效的方面。秦系文字以小篆为正体。李斯作《仓颉篇》,赵高作《爱历篇》,胡毋敬作《博学篇》,合称“三仓”。“三仓”以小篆书写,作为推广标准文字的范本颁行全国,对当时的普通民众和基层官吏起到了文字启蒙与知识普及的作用。这些字书在秦汉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多有发现。
秦朝还有一种书体,称为隶书(秦隶),笔画方折平直,比小篆简化,书写更为简便。相传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程邈搜集民间书体,删繁就简,创三千隶字,以利书写。但隶书并非秦统一后产生,至少在战国晚期就已经广为使用,睡虎地秦简就是以隶书写就的。因为秦“官狱多事”,政务繁忙,用秦篆书写公文极不方便,隶书就流行开来,最终成为日常通用的书体。
除了统一字形之外,“书同文”的内涵还包括规范用字、规范名物称谓及避讳等,为秦代官府行政工作提供统一的标准。从里耶秦简“更名方”可以看到,秦统一后对全国官方文书中使用的字词都作出了详细规定。汉代的标准语“洛语”,承袭先秦的雅言,称“正音”“雅言”。“洛语”的使用没有地域限制,也称“通语”。在当时,推广“通语”被上升到法律的高度。
“书同文”的文教政策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一种通用的语言文字,使汉字走向统一、规范和定型,不仅便于制度法令的传布与推行,而且促进了不同地域的文化交流。在岭南,今广西贵港罗泊湾汉墓出土器物的文字与各地发现的秦文字风格一致,说明秦统一岭南后,统一的文字得到了广泛的推行。在北方,因匈奴无文字,与汉朝通信均用汉字和汉字书信格式。在东北,汉字是高句丽人的通用文字,留存至今的《好太王碑》等均用汉字书写。在西域,自西域都护府设置后,地方政权在认同自己和汉朝政府之间的隶属关系的基础上,自愿听从汉廷的指令,汉语遂成为通行于各族群间的官方通用语。新疆尼雅遗址发现汉简《仓颉篇》,充分说明两汉时期,西域已经使用中原的通用文字抄写范本。
总之,后世常常用“书同文”来形容天下统一、社会大治,就在于秦汉时期的这一文教政策推动并彰显了大一统政治建构,对形成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产生了深远影响。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初置博士官,传诸子百家之学。而后为统一思想和学术,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颁令焚书,禁绝私学。汉初,社会生产得以恢复,统治秩序逐渐巩固,遂成“文景之治”。但是,随着经济渐趋繁荣,新的社会问题开始出现,诸侯势力威胁中央,富商豪强兼并农民土地,匈奴不断进犯。如何统一思想,做到规范一致、政令畅通、官民和谐,成为统治者无法回避的问题。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确立了儒家思想的官方意识形态地位,为大一统政治实践奠定了坚实的意识形态基础。
董仲舒将阴阳家形而上的宇宙观与儒家政治哲学相结合,从理论上论证了大一统政治社会制度的合法性,解决了汉王朝的道统问题。他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如果“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人君就无以持一统,因此,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建元五年(前136),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设五经博士,尊崇儒家经典,优礼延揽儒生数百人。但实际上,汉武帝的政策并非简单地独尊儒术,而是儒法兼用,并融汇了道家、墨家、阴阳家等多家思想,各家思想在儒学框架内实现会通。
此后,西汉太学均以儒家经典为教授内容,察举制的官员选拔也以儒家思想为标准,所选官员主要出自儒生。皇权与儒家官僚体制逐渐形成相互支持并相互制约的共生关系,从制度上保障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以及后世儒家士大夫阶层持续存在并发展的可能性。四方之民积极向化,儒学对凝聚中华文化认同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
东周列国文化可划分为七个文化圈,分别为中原文化圈、北方文化圈、齐鲁文化圈、楚文化圈、吴越文化圈、巴蜀滇文化圈、秦文化圈。随着秦汉大一统王朝的建立和巩固,这些文化圈交融汇聚,逐渐形成了具有统一风貌的汉文化的基本样态。
关中地区是秦汉王朝的政治文化中心,因特殊的陵邑政策和多次移民运动而表现出“五方杂厝,风俗不纯”的特殊文化风格。从秦朝至西汉中期,相继有数十万移民陆续迁入此地,周秦文化传统得以部分继承。但由于移民的大量涌入,特别是西汉初年“秦中新破,少民”,而由东方移民“益实”,这一地区的文化构成已大为改观,一个新关中文化圈实际已经形成。班固《西都赋》提到长安及诸陵邑形势,有“英俊之域”“冠盖如云”等赞誉,说明此地广聚天下“英俊”,集会四方“豪杰”,早已打破传统地域文化界限。他们从汉代各个地区(包括各边疆族群)流动而来,造成了帝陵附近人口的增殖及人才的汇合,形成一个特殊的区域文化。
楚地特有的民俗风情和艺术风格对秦汉文化的塑造和形成有重要作用。秦末反秦运动的主力多为楚人,项羽、刘邦等人均有关于喜好“楚歌”“楚舞”的记载,以屈原等人作品为代表的楚辞,对汉赋、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战国晚期至秦汉的宫殿建筑一反从前的多重院落式风格,出现高台建筑和巨型建筑组群,追求气势雄浑、崇高博大、“非壮丽无以重威”的效果,而这正是楚宫建筑的传统,号称“天下第一台”的楚国章华台就是典型代表。秦代漆器的龙凤纹样、咸阳秦宫遗址的壁画和瓦当、秦始皇陵出土的铜车马和秦俑等,均带有楚地的风韵。
齐鲁文化影响秦汉历史文化进程最突出的表现是儒学向西传布,并成为主流意识形态。齐鲁儒生中多有代表,如秦始皇时期,数十位五经博士均为齐鲁人,汉武帝时则有丞相公孙弘等人。自西汉昭、宣时期到西汉末年,丞相多为掾史文吏和经学之士,出身齐鲁者占比约三分之一。《汉书·儒林传》中单独立目的有二十七人,齐鲁籍的有十二人。
滨海地区因其特殊的经济优势,在当时文化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由于“擅海滨鱼盐之利”,滨海地区往往经济繁荣。从《管子·海王》中可见“海王之国”的政治理想。燕、齐、吴、越等滨海地区的早期商贸活动和航海实践也使秦汉文化中包含了海洋文化元素。目前所见汉代铁官、盐官遗存文物,位于滨海地区的甚多。除《汉书·儒林传》中籍贯可考的众多儒学名士外,西汉一代名医淳于意、东汉造纸专家左伯、学术大师郑玄等人也都来自滨海地区。
区域文化的长期交融不断增进秦汉文化的共同性。如山西、河南、湖北、内蒙古、四川等地原本多见的秦式墓葬,至西汉初年已基本不复存在。在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里仍然可以看到各地文化风情的差异,全国被划分为“山西”“山东”“江南”“龙门、碣石北”四个经济文化区;但到了西汉晚期至东汉,黄河流域已经可以大致归并为关东(山东)、关西(山西)两个基本文化区。东汉以后,区域文化融合进程进一步加快。汉人扬雄《方言》中的某些地方语言词汇,到了晋人郭璞《方言注》的时代,已经成为各地通语。许多关西关东方言当时已经混化。这些都表明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进一步形成。
不仅如此,秦汉时期的国家祭祀与民间信仰也开始逐步整合。秦汉帝王巡行的重要目的之一是祭祀天地、山川、鬼神。《史记·封禅书》中有秦始皇“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的记载。所谓“八神”,原本是齐文化的崇拜对象,包括天、地、兵、阴、阳、日、月、四时之神等。秦始皇在先秦各国山川祭祀习俗的基础上,整合秦国关中的七大名山加上关东的五大名山,建构出一个相对固定的山川祭祀体系。西汉以降,朝廷基本承袭了秦时祭祀制度,汉武帝确定的“五岳”体系,到汉宣帝时“自是五岳、四渎皆有常礼”、标志着五岳之序最终明确下来。长江的祭祠规格升为一岁四祠,仅次于黄河(一岁五祠)。汉朝对南方长江水域祭祀系统的认同,与秦汉时期对南方广大区域的开发、人口流动和族群交融密切相关。“五岳四渎”的祭祀体系最初并不固定,与各地的祭祀圈都有重合,如河神为秦、晋、齐人共祭,汉(沔)水为楚、秦人共祭,但随着秦汉大一统的发展,这些独立的祭祀圈最终被整合成覆盖全国的大祭祀体系。
秦汉时期,得益于政治大一统带来的便利,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持续互动,中原与边疆的文化艺术交流达到了新的高度。中原地区的思想、文化、艺术不断向边疆族群传播;同时,边疆乃至更远的异域文化也为中原文化注入了新鲜元素。各区域文化都跨出了自己的地理局限,彼此借鉴互融,共同塑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作为中原王朝的正统思想,儒家思想由中原向边疆传播,对边疆族群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发现的汉墓壁画中绘有圣贤、豪杰、孝子、贤妻、良母的故事图,其中“金日碑拜母像”壁画描述匈奴休屠王太子金日碑向母像跪拜的场面,很有典型意义,壁画上的金日碑还穿着汉服。匈奴习俗本是贵壮贱老,金日碑是匈奴人,却受到汉人孝悌文化观念的影响,他的子孙也均以忠孝显名。
在西域,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图5-6)采用白、背、绿、赤、黄五色经丝,代表了汉代织锦技术的最高水平,反映了汉人的阴阳五行思想在西域的流传。“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上有在新疆地区发现的最早的“中国”二字,距今两千多年。“中国”最初是一个地域概念,泛指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最早明确记载“中国”二字的是西周初期的青铜器“何尊”铭文,铭文中有“宅兹中国”字样,指以洛阳盆地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专家考证认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是由蜀锦匠人专门为汉朝皇家织造的,最终却出现在新疆地区的汉代墓葬中,表明边疆和汉王朝之间往来密切。该遗址还发现了八枚精绝、且末等地贵族用汉隶书写的互致问候的书简,其中一枚正面写“奉谨以琅玕一致问”,背面写“春君幸毋相忘”,反映当时汉字是西域与中原人士之间交流的主要媒介。在蒙古高原匈奴单于庭龙城遗址中出土了“天子单于”汉字瓦当,这充分说明了汉代时匈奴使用“天子”等中华文化的观念建构其政治核心概念。楼兰古城平台墓地出土的连弧柿蒂纹“长宜子孙”铜镜、“家常富贵”铜镜、星云纹铜镜,以及尼雅遗址出土的“君宜高官”铜镜、龙虎纹铜镜等,其样式与西汉中晚期和东汉时期中原地区常见的样式一致。如在西南夷地区,云贵高原出土的汉代铜钟,是在中原乐钟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属中国古代乐钟体系的地方类型,但很多方面又打上了本地文化的烙印。在青海羌人区上孙家寨发掘的西汉至东汉中期墓葬群,保留了羌人特有的埋葬习俗,但墓葬形制和陪葬陶器种类基本与中原地区一致。匈奴分裂后,南匈奴一改前期单人葬式,墓葬加入了许多汉人丧葬文化因素,出现家族式多人合葬墓,随葬器物中有大量的汉式陶器。
中原的音乐对边地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在西域,细君公主在乌孙,经常抚琴长歌,创作了脍炙人口的《黄鹄歌》。汉宣帝时,解忧公主之女弟史,与丈夫龟兹王绛宾一起去长安“学鼓琴”,受赐“歌吹数十人”,归国后“撞钟鼓,如汉家仪”,这是西域主动学习和传播中原音乐的明确历史记录。龟兹石窟早期壁画中出现了排箫、阮咸等中原乐器,当与此段历史有关。元帝竟宁元年(前33)春,呼韩邪单于朝汉,汉赠其衣、锦、帛、絮,以及竽、瑟、卧箜篌等乐器。在西南地区,迁往巴蜀的豪族带去的中原礼乐使得巴蜀之地“箫鼓歌吹,击钟肆悬”。
与此同时,边疆地区的文化与艺术对中原也产生了重大影响。西汉中期,佛教传入西域,此后逐渐流行于民间。永平七年(64),汉明帝遣使赴西域访求佛法,使者在大月氏国迎请天竺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以及佛像经卷至洛阳。两位高僧居于白马寺,组织翻译了《四十二章经》等。桓、灵二帝时,西域僧、居士接踵来到中原,翻译大量佛经,佛教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深刻影响了中华文明在后世的发展。
两汉时期,西域、西戎、西南夷等周边地区的音乐舞蹈等艺术作品大量传入中原,受到各阶层欢迎。自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后,来自西域的胡乐就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原,琵琶、竖箜篌、胡笳、羌笛等乐器传入中原,如今都是中国常见的乐器,成为中华民乐的重要组成部分。秦汉时期的音乐考古发现了来自古代两河流域和波斯的丝弦乐器图像,出土了箜篌的实物。《急就篇》注:“空侯,马上所弹也”,可理解为其最初源起和普遍使用与草原民族文化有密切的关系。
秦汉时期,于图乐、龟兹乐、印度和西域的佛教音乐等都加入西乐东渐的行列。武帝时,受胡乐《摩诃兜勒》启发,李延年造新声二十八解,成为朝廷的武乐。当时每每举行盛大演出,就会有西戎乐曲“狄辊”,以及西南夷传入的“巴渝舞”等。龟兹乐舞是发源于中国古代西域的一种舞曲。音乐家苏祗婆推动了龟兹调式在中原的发展,龟兹“五旦七调”乐律,冲击了宫廷僵化的乐制,为中国传统音乐注入了新的活力。龟兹乐中的“般涉调”在中原长期流行,在民间很有影响。班固《东都赋》叙述明帝款待四夷使者,除表演汉朝乐舞外,还有“僚休兜离”的四夷乐舞加入。东汉灵帝时期,诸多以“胡”为名的文化因素已经在社会中广泛流行。“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可见当年胡汉交融、载歌载舞的盛况。
总之,在秦汉时期,各区域性文化都大大超出了自己的原生地域,传播至更为遥远的地方。游牧文化就从北方扩展到中原甚至更南的区域,如曾在北方代地长期生活的薄太后,其陵墓外藏坑就出土大量金银饰品,上有马、熊等动物形象,还有颇具草原风情的纹饰;江西南昌海昏侯汉墓所出双狼猎猪纹石嵌饰为本地制作,纹饰亦借鉴了北方草原地区的动物厮杀纹。南越国遗址所出随葬品,就体现出多种区域性文化元素的杂糅,在越文化的基础上,不仅吸收中原政治文化,还包括了楚文化甚至草原文化。如该地出土的36件青铜鼎,就可分为汉式鼎、楚式鼎、越式鼎三种类型,各具特色,共同构成南越王政治地位的象征;还有惟妙惟肖的“虎噬羊”牌饰也采用了战国以来北方草原地区民众喜爱的艺术主题,同样受到南越地区统治者的欢迎。端午节祭祀屈原的活动起初仅在楚地一隅发生,后传至王朝各地。端午吃粽子纪念屈原的习俗相沿至今,成为海内外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