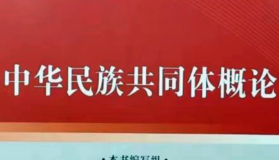-
1 授课视频
-
2 章节测验
秦汉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族群间的社会交往交流机会大为增加,中国历史进入更广泛深入的社会大融合阶段。“编户齐民”制度为全国人口管理与国家统一提供了制度保障,“行同伦”的整合策略增强了社会认同,“徙民实边”促进了社会流动,“天下一体”“天下一家”的观念成为社会主流意识。
秦汉社会生活的重塑源自社会基层组织的重组,“编户齐民”制度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编户齐民”主要是通过登记户籍的方式掌握人口信息。这一制度可溯源到周朝的人口登记制度、春秋时楚国和晋国建立的户籍制度,在商鞅变法中正式定名实施。“编户齐民”在秦统一后推广到全国,在汉代趋于成熟和定型。编入户籍的民户主要是广大农民,也包括无爵位的地主和小官吏。官府依据户籍来制土处民、征收贡赋、规定禄食、兴发力役、组织军旅。
通过“户”及其相应的组织建制,秦汉王朝建立了有效的纵向控制体系,国家对社会基层的治理效能大为提升,即便是来到中原的胡人也受这一制度制约。从里耶秦简可以看到,秦中央政府要求各县都登记并上报辖域内诸“蛮”的户籍信息,湖南沅陵虎溪山汉墓出土的《计簿》就记录了西汉文帝时期沅陵侯国的“蛮夷”人口数。不管是俘虏、聚族内附的居民、擅长乐舞百戏的乐师,还是为汉官服务的奴仆,都成为编户民。还有一些胡人被征召入伍,“胡骑”与“越骑”是守卫王朝秩序和安全的重要力量。
编户齐民的实质是对春秋战国以来社会结构的重组。它彻底改变了以往以宗族集团作为基本社会单位的政治模式,转而以家户作为国家治理和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打破了过去的血缘关系,通过地缘与政治达成社会治理,有利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此后,编户齐民制度成为中国古代政治的基础性制度,也构成“百代皆行秦政制”的重要内容。
秦统一后,除了推进编户齐民等制度建设外,还非常重视规范社会风俗,推动“行同伦”,用统一的伦理纲常规范各地民众行为,从而达到“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之效。
秦统治者以立法形式纠肃民风,郡县各级长官都有考察和整肃民间习俗、督治风俗教化的职责。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书写的会稽刻石铭文,批评了民间盛行的不良风气,以皇帝名义严令禁止淫逸之事。睡虎地秦简《语书》是秦的南郡守“腾”下达给所辖各县的政令,其中明确提到“圣王作为法度,以矫端民心,去其邪避(僻),除其恶俗”,谆谆教诲各县官员应积极敦化“乡俗”,可见秦王朝对风俗教化的重视,始终不断敦促各级官吏贯彻落实。在县下各乡,还设有专门执掌教化的乡官,称“三老”,这一建制为后代承袭。
西汉时期,随着儒学被确立为国家意识形态,朝廷也试图通过齐整风俗来实现国家整合。其中,派遣循吏到边疆任官,不仅能为边疆地区带去先进的农业技术,还普及中原伦理文化,是对边疆社会实施教化、推动民众移风易俗的重要手段,如著名的“文翁化蜀”。汉景帝末年,文翁任蜀郡太守,栽培当地小吏,使其赴长安学习,学成归蜀后,或安排他们担任重要职务,或通过察举向朝廷推荐,有人因此官至太守、刺史。文翁还在成都兴建学宫,从学的年轻人可免除徭役,学成后,根据能力高低授予不同的官职。文翁还经常让学子跟随自己观摩处理政务:蜀郡之俗为之大变,文教大盛。
在西南,东汉框帝时,胼舸郡(今贵州黄平、贵定二县间)采用中原礼俗教育民众,以中原文化融合凝聚各“蛮夷”部落。在南方,光武帝时,桂阳郡(今湖南郴州)太守卫飒兴修学校,传布儒家伦理及婚丧礼仪,当地社会风貌大变。九真郡(今越南清化)旧以射猎为业,无嫁娶之规,太守任延铸农具,授农耕之法,并定婚配礼法。当地民众感激太守,多给子孙起名为“任”。治郡循吏受到各地百姓拥戴,百姓多为其建祠祭祀,影响深远。在官民各方努力下,中原与边疆的伦理风俗交流融合,大一统社会共同性逐渐凝聚。
秦汉大一统第一次将内部具有差异性的广土众民塑造为一个社会性的统一体,并吸引和推动周边族群加入这个统一体。
首先,是中原地区内部的人口大迁徙。秦统一前后,为加强对六国故地的控制,实行“出其人”“移秦民万家实之”的政策。六国居民开始大规模搬离原住地,其中一部分贵族迁入秦国本土,如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一部分豪侠迁往巴蜀,“秦惠文、始皇克定六国,辄徙其豪侠于蜀”;更多的民众则在六国之间迁徙,如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三十五年(前212)“徙三万家丽(骊)邑,五万家云阳”;等等。上述中原内部移民总数达到20余万户,规模在百万人以上。出土秦简上的“新地吏”“新黔首”等称谓,证明了当时各地的人口流动。同时,这类移民并非临时性质,睡虎地秦简《封诊式》有“迁子”案例,明确规定迁“蜀边县”的“终身毋得去”。
汉初,将六国旧贵族迁往关中地区,如齐国诸田,楚国昭氏、屈氏、景氏等大族,燕、赵、韩、魏诸国的宗室后人及关东各地的豪强名家;同时,汉朝新设置陵邑(高祖长陵、惠帝安陵、文帝霸陵、景帝阳陵、武帝茂陵等),前后迁移10万余人进入关中,从而增强了关中地区的实力,客观上促进了中原各区域的人口交融和文化交流。两汉时期的田延年、田千秋、第五伦等名臣,祖上都来自这些迁徙入关的群体。
其次,中原到边疆也有大量人口流动。秦汉推行“徙民实边”政策,由内地向边疆地区迁移农业人口。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蒙恬收复“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以南地区),之后从中原迁出一批“犯人”及其家属戍守边地。同年,秦始皇还迁徙50万人戍守岭南,与越人杂居。秦始皇三十六年(前211),秦向河套至阴山一带的北河、榆中移民3万户。汉朝向边疆转移人口的规模有增无减。汉文帝时,募民为戍卒,徙居塞下屯田。汉武帝先后徙10万人居朔方,徙70余万人至新秦中,发卒60万在上郡、朔方、西河等郡屯田戍边。取得河西走廊后,元狩二年(前121),武帝在浑邪王故地置酒泉郡,移民实之。
两汉时期,还有大量的中原人口自发向塞外迁徙。其中,流入匈奴的汉人总数10余万,包括逃亡的官员及奴婢、战俘等。这些汉人在为匈奴增加劳动力的同时,也带去了中原文化和技术。如武帝、昭帝时期的卫律,投降匈奴后,在当地着胡服,用胡俗待客,同时向匈奴单于献穿井筑城、治楼藏谷之计。
最后,周边族群向边郡或中原流动。如光武帝建武十一年(35),羌人归顺,东汉朝廷曾多次将大批降附的羌人迁往天水、陇西、扶风三郡;明帝永平元年(58),将羌人降众七千多人迁置三辅(长安及附近的关中之地);和帝永元十三年(101),将羌人降众六千多人迁往汉阳、安定、陇西等郡。在南方,朝廷将部分东瓯和闽越人迁往江淮,这些移民从此融汇于中原人口之中。
更值得一提的是,两汉之际和东汉末年分别出现了两次向南部地区,尤其是江南的移民潮。
两汉之际战乱,大量中原人“避难江南”。通过比较元始二年(2)与永和五年(140)的户口数字,可以看到江南地区户口数增长140.50%,人口数增长112.13%,而同时期全国户口数与人口数均为负增长。
东汉末年,受天灾、战乱影响,中原人口再度大规模南迁。一时英才皆聚于南方,《三国志·魏书》称“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当时不少黄河流域居民为避难,竟远迁至“交州”(今广东、广西及越南北部、中部)。
北方“流民”南迁与江南地区的开发是同步的。有学者指出,东汉以后,政府经营的重点转移到了南方地区,史著中反映江南生产、赋税情况的记载也明显增加。人口的流入不仅促进了江南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江南的开发,而且因生产环境和通婚环境的改变而有利于江南人口素质的提高。同时移民也是文化的载体,移民流向江南也带着北方文化流向江南,所以,移民的过程也是中华文化融合和扩展的过程。
随着越来越多的周边族群与汉人杂居共处,民间族际通婚亦成为常态,既有周边族群迁居内陆与汉人通婚,也有汉人迁往周边族群聚居区与当地人通婚。秦朝时,民间的族际通婚已到一定规模,政府不得不制定法律予以规范。如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秦律规定,若父母皆为部族人,其子称“真”;父为部族人,母为秦人,子称“夏子”。
在汉朝出使西域的使者中,有不少人娶过“胡妻”“胡妇”。张骞被匈奴羁押时,身边有胡妻,即使逃归中原其胡妻也一路随行。苏武也有匈奴配偶。李陵、李广利降匈奴后,皆娶单于之女为妻。汉人与胡人通婚所生后代被称为“秦胡”。汉顺帝时,马子硕因任官留居陇西,娶羌女,生子马腾,马腾及其子马超就是典型的“秦胡”。东汉名将段频手下有秦胡步骑五万余人。族群间各种形式的通婚,客观上使不同族群从血脉上连成更加不可分割的共同体。
经过长期的迁徙流动、通婚聚居和多方互化,不同族群的生活方式趋同,血脉联结加深,族群界限渐泯。将黄帝作为共祖,将不同族群都视为“天下一家”中的一分子,成为族群交融加深的重要反映。这鲜明地体现于《史记》的编写思路和历史观中。基于天下大一统的实现,司马迁撰写《史记》时梳理出一条以黄帝为华夏族群共同始祖的谱系。这一谱系不仅有华夏圣王“血统”脉络,还包括地处“蛮夷”之邦的吴、越、秦、楚,甚至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由此开创了华夷同祖的族源叙事模式。更重要的是,司马迁还为匈奴、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大宛立传,将其纳入“国史”视野,彰显“华夷共祖”“四海一家”的大一统思想。这一做法后来也为《汉书》所继承,成为中华民族内在多元却不失一体的标志。
秦汉时期,中国历史上人口规模最为庞大的“汉人”群体开始出现。虽然“汉人”作为确切概念用于自称和他称的具体时间还有待细考,但确凿无疑的是,汉人共同的文化心理与价值追求在这一时期已初步形成。
在族源构成上,汉人前身是春秋战国时期在族群大融合中形成的华夏共同体,融汇了包括炎黄、“东夷”、“苗蛮”、越人、戎、狄、羌等在内的多个古代族群。经历四百余年秦汉大一统,华夏共同体融入了更多周边族群。他们长期生活于统一的王朝,形成了明确的大一统政治文化认同,演化成了具有鲜明社会文化特征的“汉人”群体。
在文化心理上,因为族源和生存环境多样,汉人除了农耕文化之外,还吸收了游牧、狩猎、山地、海洋等多样文化元素,交融形成以农耕文化为主体和枢纽、汇聚兼容多种文化样态的汉文化,确立了古代中国最主要的伦理秩序和社会规范。这使得汉文化在保持共同性、统一性的同时,始终保持极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从而能够不断与时俱进。
在价值追求上,汉人在形成过程中发展出了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诸子百家思想,进而构造了大一统观念与制度,推动其成为中华民族漫长历史中的基本价值追求和制度实践。秦汉以来,不论是“混一海内”的统一王朝还是政权并立的分裂乱世,大一统都成为中华大地各族群、各政治体的共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