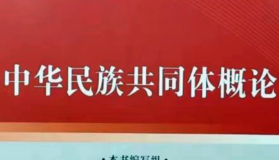-
1 授课视频
-
2 章节测验
自周代开始,虽已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但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权威式微,各诸侯国互相攻伐,旧的统治等级秩序与政治统一格局逐步瓦解。乱世之中,饱受战乱分离之苦的广大民众内心最深切的渴求就是和平、稳定与统一,诸子百家纷纷提出整合寰宇、一统天下的主张。比如,《论语·颜渊》提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孟子·梁惠王上》提出天下“定于—”,《荀子·儒效》提出“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非十二子》提出“一天下,财万物,长养人民,兼利天下”。秦国顺应时势,积极变法,最终完成了天下一统,建立了中国历史上首个中央集权大一统王朝。其后,汉承秦制,进一步巩固了大一统的政治共同体。
秦朝建立后,秦王赢政兼采传说中“三皇五帝”尊号,确立了“皇帝”称号,自称“始皇帝”,制定了一整套朝仪、典章和文书制度,以彰显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皇权至高无上的权威。其后,皇帝之下的中央官僚体系也逐步完善,形成三公九卿制,分工执行中央政令。这一套中央政治体制深刻影响了后世王朝的政权组织形式。
秦朝在全国境内推行郡县制。郡县制起源于春秋时期(郡源于秦国、县源于楚国),到战国时期商鞅变法时,秦国开始废分封,普遍推行县制。秦国统一六国后,为有效管理空前广袤的国土,在全国普遍设郡,每郡有守、尉和监各一;郡下辖县,郡守、县令、县长都由皇帝直接任命。《史记》记载秦设三十六郡,而出土文献大大扩充了已知的秦郡数量,如里耶秦简记载了洞庭郡和苍梧郡,岳施秦简记载了江湖郡、河间郡、恒山郡、衡山郡、庐江郡、清河郡、四川郡等。秦县更是达到了一千多个。新设郡县被称为“新地”,由秦故地官员前去治理,同时推行徙民实边、行役戍边的政策。在边疆族群聚居地区,则设“道”以管理,道、县为同级别的地方行政机构,都受郡的管辖。
郡、县(道)是中央政府实施直接治理的地方行政单位,通过垂直集权的郡县制,秦朝将中央的法、律、令推行至全国各地,实现了高度的政治统合,中央集权制度从此确立。在中央集权郡县制的制度运转体系里,无论民众以前属于哪个邦国、哪个族群、哪种文化,都成为秦朝的“编户齐民”,都在同一体制下生活,这就大大弱化了族群界限和地域区隔,而强化了其政治共同性。这对巩固疆域、稳定政局、促进交融起到重要作用,有力塑造了高度统一的大一统政治共同体。
汉朝在建立之初采取郡县与封国并行的体制。汉初五十余郡,有三十多郡属于诸侯国,基本都在齐楚吴等国故地;中央直辖的只有十余郡,大多在秦故地。汉初的封国不同于西周的封国,下辖的不再是贵族的采邑而是郡县,所以有“郡县之制,无改于秦”一说。不过,封国与郡县并行的双轨制的确弱化了中央对边地的控制。与此同时,边疆还出现了南越、东越、匈奴等政权,西南夷诸君长也纷纷自立。
当汉朝统治趋于稳固时,朝廷着手加强对诸侯王国的控制。汉景帝行“削藩”之策,平定七国之乱。汉武帝颁布推恩令,进一步分散封国力量,设刺史监察郡国,加强朝廷对郡国的管理,强化中央集权。汉武帝还积极经略边疆,先后统合迁徙南越、东越、西南夷,将匈奴逐往漠北。宣帝神爵二年(前60),设立西域都护府,全面掌控西域。最新考古证实,汉武帝时期,古滇国国王降汉,汉武帝在该地设郡,封滇国国王为滇王(图5-1),建立以郡县制为基础的行政管理体系,对该地区行使治权。至此,汉朝郡县统治区域得到极大扩展,在东北、西北、西部、西南和南部边界都设立新郡,郡守管辖的土地与匈奴、羌人等族群聚居的土地交错,各族群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在这片土地上更为广泛地展开。
秦汉建立的中央集权郡县制,奠定了大一统的制度基础。这一制度的运行并非仅靠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动,如果没有中下层官吏的认同与执行,没有追求统一、安定社会局面的主流民意的认可和支持,这一庞大的制度体系不可能如此迅速建立并历经秦汉两代而基本定型,且影响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央地治理传统。里耶秦简就充分展现了在“新地”洞庭郡迁陵县,秦吏勤勤恳恳组织人民开垦荒地和探明山川物产、开发国土、登记民户、绘制地图、上报到朝廷归档阅存等治理细节。1975年底,在湖北省云梦县发掘了睡虎地秦简。根据其中记载可知,睡虎地M11号秦墓墓主是一位基层的小吏——“喜”,其遗体周围放置着秦王朝的法律文书、案例等简牍史料。同墓还出土了《编年纪》,依年代顺序记载了秦国的国家大事与“喜”的个人事迹,一个普通小吏以如此方式将自身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
可见,秦朝大一统国家体系的建构和运转,离不开千千万万个“喜”这样的基层小吏、战士和平民百姓。正是他们怀着自发的忠诚与情感,才为秦汉开创大一统政治传统提供了内在历史动力。
秦汉建立中央集权大一统王朝的过程,是多元一体超大规模政治共同体形成的过程。比如,秦灭六国可以视为政治上完成统一,但六国的制度文化在秦汉王朝融会贯通、日臻完善。如县制,最早由楚国开创,晋国继之,又为秦及之后王朝长期沿用;秦朝立郡县,项羽复分封,而汉高祖采取郡国并行,则是秦楚杂用;叔孙通以齐鲁之地的儒家礼仪为汉王朝制定礼乐典仪,董仲舒将齐儒之学融入“汉道”;源于齐国的黄老之学和经济之术,源于燕赵的军事制度,源于韩魏的纵横刑名,也都融入秦汉统治制度,最终形成稳定的大一统制度体系并垂范后世。不仅政治层面如此,社会层面的族群交融、文化层面的多元合一,都体现出多元和一体的有机统一,这一精神被后来的历代统一多民族王朝所传承发扬。
多元一体政治共同体的建构伴随着官吏的广泛流动。郡县制下,天下一家,官员的选拔不受地域和族群限制。早在秦统一六国之前,任将相的外来客卿就甚多。西汉时,姓名、籍贯可考的京兆尹有近40人,籍贯在关中之外者占绝大多数,如渤海(汉朝渤海郡,辖今河北沧州、衡水,山东德州一带)人隽不疑、代郡(今河北蔚县)人范守、蜀郡(今四川西部地区,治所在今成都)郫人何武、涿郡(今河北涿州)高阳人王伯、东海(今山东郯城)兰陵人毋将隆、巴郡(今四川东部地区)阆中人徐诵、会稽(今钱塘江以南的浙北地区)吴人陆恭等,来自五湖四海。江苏连云港尹湾汉墓出土的简牍记载了西汉东海郡各县、侯国官员的履历,其中有人来自梁国蒙县(今河南商丘),曾任象郡象林县(今越南广南会安一带)候长,因功劳迁为建陵侯国家丞。可见当时基层官吏亦有极强的流动性。内附族群也可入朝为官,如匈奴休屠王之子金日碑,入汉之后,因才干勇略获得武帝赏识,最终成为武帝的托孤大臣,其后代成为显赫世族,为巩固西汉政权、维护民族团结作出重要贡献,彰显了大一统政治体系的包容性与多元性。
秦汉王朝还通过设属邦或属国,置持节领护及行羁縻、怀柔等多种举措治理边郡,建立藩属体系,将周边匈奴、乌桓、鲜卑、羌及西域各国不同程度地纳入大一统王朝的政治秩序。
属邦之制在战国时期的秦国即已出现。秦兵器铭文有“属邦”一词,睡虎地秦简中也有《秦律十八种·属邦》。“属邦”负责管理归附的“臣邦”和有“蛮夷”聚居的“道”,兼具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的双重特征。其中,《秦律十八种·属邦》就规定,道官输送隶臣妾和因家人犯罪而被收捕的人,必须写明已领口粮的具体日期,是否领取了衣物、是否婚配,符合规定条件的即按照法律供给衣食。这一方面说明秦朝已经在“蛮夷”聚居地区设置了“道”这一政权机构及其官吏(“道官”)。另一方面,也表明“蛮夷”中的普通罪犯与秦人罪犯待遇相同,秦人罪犯并无优待之处。秦统一后,属邦主要在陇西地区,辖有县、道,管辖界内“蛮夷”和秦人。始皇三十三年(前214)之后,秦将新并入的“蛮夷之地”全部划归郡下之道,由国家派官吏管理,采取变通措施推行编户化,基本实现了郡县一元化,同时也体现了政治一体下治理策略的多元性和包容性。
两汉时,“属邦”因讳刘邦之名改称“属国”。汉初国力未盛,统治者无力营边。文景时,中央设置“典属国”一职,专门负责处理归顺“蛮夷”事务。汉武帝平定四裔,远征匈奴,边地归附人口激增。元狩三年(前120),以匈奴浑邪王入降为契机,汉武帝在北部边塞设立属国,由都尉统领,以安置浑邪王部落。武宣时,汉朝先后在西北边疆设置安定、天水、西河、上郡、五原、张掖和金城七个属国,以安置降附的匈奴、羌人等。此后,设置属国成为汉代处理降附地的常用举措。东汉光武帝时,朝廷虽大量裁撤郡都尉和关都尉,但仍保留边郡的属国都尉,属国的治理方式也逐渐向一般郡县靠拢。
对于不具备设置属国和边郡条件的边疆族群,如匈奴、乌桓、鲜卑等,朝廷则酌情派遣临时性的“持节领护”统筹管理,如使匈奴中郎将、护羌校尉、护乌桓校尉等,分别处理匈奴、羌与乌桓事务,统理中原王朝与北方、西北边疆各族群的往来。对于西域诸国,则设西域都护府加以管理。通过不同的政治联系和治理方式,汉官吏与当地统治者交流频繁,带领各族人民修治沟渠、广置屯田、发展生产,共同创造了当地的和平与繁荣。
除设官置吏等制度建设外,秦汉王朝还采取和亲、纳质、册封等策略羁縻周边族群。
“和亲”是将皇族女性嫁给对方,以改善双方关系的一种政治结盟方式。两汉时期,汉匈和亲次数最多,最初多是在军事压力下被迫而为,后来多是匈奴主动求娶。汉元帝竟宁元年(前33),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嫁呼韩邪单于,为汉匈双方带来了长期的和平与兴旺。1954年与1981年在内蒙古包头等地的汉末墓葬中发现了内有“单于和亲”“单于天降”“四夷尽服”等文字的瓦当,就是这一时期汉匈关系和洽的实证。西域诸国也常与汉王室和亲通婚,细君、解忧两位公主嫁至乌孙,为乌孙与汉朝的友好关系作出了卓越贡献。
“纳质”指边疆族群与中原政权间派遣王子“入侍为质”和“纳质为臣”的制度。汉武帝时,西域楼兰、大宛、尉犁、危须、抒弥、乌孙等国纷纷“纳质”。“纳质”虽然有不平等因素,但客观上加强了边疆族群与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联系。质子们学习汉朝典章制度,参加朝廷礼仪活动,耳濡目染华夏文化,思想情感上也向华夏凝聚。
册封周边君长,赐予王号,也是重要的羁縻措施。东汉初期,光武帝恢复原西汉藩属的高句丽王、白马氐王侯君长的称号,又各封乌桓、鲜卑等族首领为侯王君长,获得周边族群的拥戴和认同。《后汉书·东夷列传》载:“自中兴之后,四夷来宾,虽时有乖畔(叛),而使驿不绝。”此后,东汉统治者大体遵循光武帝之策,继续强化与四夷的友好关系,中原与边疆保持了较长时间的稳定交往。
秦汉时期,以长城为分界线,呈现出农耕、游牧社会持续不断交往交流交融的壮观景象。
匈奴是当时最重要的北方族群,他们生活在蒙古高原,以游牧为生,逐水草迁徙。秦时,匈奴各部落形成联盟,匈奴地区已建有一些城堡,有少量的农业生产,有些部落已开始使用铁器。汉初,冒顿单于以其“控弦之士”三十余万,东败东胡,北服丁零,西逐大月氏,使“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其统治区域东起东胡故地,横跨蒙古高原,向西与氐羌相接,向南延伸到河套乃至今晋北、陕北一带,统一了北方草原。
强大起来的匈奴,屡犯西汉边郡,对西汉政权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元朔二年(前127),匈奴入犯,汉遣卫青出击,夺回河套一带,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直接威胁,随后设置朔方郡(今内蒙古鄂尔多斯西部及巴彦淖尔西南部),徙十万人于朔方。汉得朔方后,匈奴连续进犯,卫青数度迎击。元狩二年(前121),霍去病自陇西出兵,过焉支山(今甘肃山丹东南),西入匈奴境内千余里,缴获匈奴休屠王的祭天金人。同年夏,霍去病越过居延海,南下祁连山,大败匈奴。同年秋,匈奴浑邪王率众归降,汉分徙其众于西北边塞之外,因其俗而治。后又陆续设立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管理河西走廊地区。元狩四年(前119),卫青、霍去病率兵与匈奴决战漠北,卫青北至宾颜山赵信城而还,单于率残部向西北败退,从此“漠南无王庭”。霍去病军出塞两千余里,至狼居胥山,临瀚海而还,败匈奴左部左屠者王。此役之后,汉军占领朔方以西至张掖、居延间的大片土地,汉廷又调发60万人移入上郡、朔方、西河等地。
匈奴向西远徙以后,内部分裂,出现五单于并立局面。宣帝甘露元年(前53),呼韩邪单于归汉,引众南徙于阴山附近,后与汉恢复和亲,结束了百余年来汉匈争战局面。
东汉时,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南匈奴遣使称藩。光武帝将南匈奴安置在五原、朔方、云中、定襄、雁门等地,居于汉与北匈奴之间。此后,南匈奴被北匈奴打败,汉朝又令单于徙居西河,派遣使匈奴中郎将常年驻军单于王庭,设置官署吏员,负责管理归附的匈奴人。从此汉匈杂居成为常态,内附的南匈奴逐步习得了中原农耕的生活方式。东汉延光三年(124),新降匈奴复叛,胁迫呼尤徽一起造反。呼尤徽说:“我老矣,受汉家恩,宁死不能相随!”北匈奴被鲜卑与汉击败后西迁,最远的迁至现在的欧洲,不断与其他族群交融,而匈奴作为一个古代的族称最终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这一时期的北方游牧族群还有乌桓,亦作“乌丸”“古丸”“乌延”等,属东胡系统。汉初,匈奴击破东胡,乌桓役于匈奴。漠北决战后匈奴败退,乌桓内附于汉,汉朝迁乌桓人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等郡,置护乌桓校尉进行管理。东汉光武帝时,辽西乌桓归附,光武帝复置护乌桓校尉于上谷郡宁城,同时管理鲜卑人。明帝时,设度辽将军,置度辽营,屯于五原郡,安抚内附的鲜卑、乌桓人。从这时起,乌桓人与汉人开始了长期的错居杂处,相互交融。
在东北,接受中原和东北各族群文化的影响,高句丽势力壮大。汉元帝建昭二年(前37),高句丽始祖王朱蒙建政,以纥升骨城(今辽宁桓仁五女山城)为都城;平帝元始三年(3),高句丽第二代王琉璃明王迁都国内城(今吉林集安),同时筑尉那岩城(丸都山城)。此后420多年间,集安地区长期是高句丽政权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秦汉时期的西域主要指今甘肃省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地带。当时在塔里木盆地南北边缘绿洲分布着楼兰、焉者、龟兹、疏勒、且末、于闻、莎车等几十个绿洲小国;天山以北还有乌孙游牧政权;帕米尔高原以西有大宛、大月氏、大夏等国。匈奴强盛时,西域诸国多受匈奴控制。汉武帝时,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与西域多国建立联系,开辟丝绸之路,史称“凿空”。其中,车师国国都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西北),东向敦煌,南通楼兰、部善,西达焉耆,西南连乌孙,东北接匈奴,扼丝绸之路的要冲。西汉与匈奴“五争车师”,前89年,车师开始归附于汉,汉朝控制区域得以扩展,但尚不稳定。
前72—前71年,西汉、乌孙、丁零和乌桓联军大败匈奴。前60年,匈奴日逐王先贤掸率众降汉,西汉遂设西域都护府,治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北),掌管西域诸国,前后任命西域都护18人。西域都护府的设立,打破了西域各地小国林立、互不往来的隔离状态,造就了在中央政府的统一管理之下西域各地相互交流日益增多的局面,增进了西域诸城邦国、各民族间的相互了解与信任,增强了西域各地各民族对中央政权的认同,对于大一统国家和中华民族的形成有着重大意义。
西域诸国君长接受汉朝册封,当地佩戴汉朝印绶的官员达370余人,西域被纳入汉王朝管辖范围。新疆阿克苏地区曾出土西汉西域都护李崇私印,以及西汉政府颁给边疆羌人首领的“汉归义羌长”铜印等,均为西汉管辖西域的重要物证。新疆民丰县尼雅遗迹出土的木牍封泥上印有“部善都尉”;新疆新和县排先拜巴扎乡古代遗址发现一枚卧驼钮,新和县兰合曼古城发现一枚卧狮钮,两枚印章印文均为“常宜之印”。“常宜”应是汉代吉语“常宜子孙”的缩写。这都是汉王朝对西域实行经营和加强管理的历史见证。东汉最著名的西域都护班超,苦心经营西域三十年,“得远夷之和,同异俗之心”9。后因年迈,汉章帝召他回朝,消息一传出,疏勒全国上下恐慌,有些人不顾仪态,放声大哭,抱住班超所骑的马腿不肯放。疏勒都尉担心龟兹再来,绝望地拔刀自杀了,希望以死来挽留班超。这足以说明以班超为代表的汉朝官员对西域的有效管理,增强了西域对中原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莎车曾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西汉于前60年设置西域都护府后,莎车国便隶属于中央王朝管辖。莎车国归属汉朝后,大约在汉元帝时期(前48—前33),莎车王的儿子延作为质子久居长安。回到西域继承王位后,他积极推行汉朝中央政府的政令,依照汉朝典章制度来治理地方,促进了莎车国的快速发展。他常教导儿子们:应世世代代忠于汉朝,不能背叛。莎车王延去世后,汉朝追赠他为“忠武王”,并任命延的儿子康继承莎车王位。遵循父亲的教导,康继续领导西域各族进行反抗匈奴的斗争。西汉灭亡时,西域大乱,莎车王康尽力收容和保护原西域都护府所属的一千多名没能撤走的汉朝官吏、士兵和他们的家属,使之免遭匈奴残害。莎车王延、康的事迹,是当时西域诸国忠诚于汉朝的一个缩影。这种忠诚爱国的历史传承与多元文化的深层交流,奠定了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坚实基础。
西北、西南地区散居的羌人部落与中原王朝战和不定。羌人原居于黄河的湟水、赐支河流域,《后汉书·西羌传》中记载有一百多个羌人部落。至东汉,支系繁多的羌人已广布在秦陇以南的广大地区,包括今甘肃、青海、四川西部、西藏和新疆昆仑山区。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西羌联合匈奴围攻袍罕(今甘肃临夏),汉朝派兵破西羌,设置护羌校尉,管理西羌事务;东汉长期沿袭。护羌校尉不仅发挥了政治抚绥的作用,而且深入当地社会,带领羌人屯田农耕,使河西地区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这一时期,部分羌人部落还远徙入西藏地区,传播了汉朝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与生活在青藏高原的本地人群融合,大大促进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使当地人口有了较大增长。
岭南和东南沿海地区活跃着百越部落。其中,南越部落主要分布在今我国广东、广西及越南北部等地。秦始皇开五岭,置南海郡(治所在今广东广州)、桂林郡(治所在今广西桂平)、象郡(治所在今广西崇左)三郡,徙谪戍民50万人以经营之。秦亡后,南海尉赵佗据其地自立为王,向南拓展疆域至今越南北部和中部,之后得到汉高祖加封,南越成为汉藩属国(图5-2)。汉武帝时,在南越分设九郡,徙部分居民于江淮,移汉人杂居其地,此后当地不同族群逐渐融合。闽越主要分布在今福建地区,秦统一后置闽中郡(治所在今福建福州)。秦亡后,闽越旧酋长无诸占旧地,获汉高祖加封为闽越王。汉武帝灭闽越,徙其众于江淮间,与汉人杂居融合。除南越、闽越外,长江以南还分布着众多百越族系。正是在秦汉时期,国家力量进入岭南地区,中国的南方疆域大致成形。
秦汉时期,在东北地区以至朝鲜半岛北部、中部,生活着汉、夫余、高句丽、滋貊、沃沮等族群。汉武帝元朔元年(前128),朝鲜半岛溅君南闾等,因不满卫氏朝鲜王右渠的控制,率28万人口到辽东归附汉朝,武帝一度在辽东塞外置苍海郡。元封二年(前109),汉武帝以半岛南部族群诉朝鲜阻碍其与汉朝通商为名,从水陆两面发兵5万攻灭卫氏政权,并在其地设置乐浪郡、玄菟郡、真番郡、临屯郡。这四郡之下又设县,郡县长官由汉朝中央派遣汉人担任。在汉朝管理之下,大量汉人官吏、富商大贾与农民前往任职、经商与垦荒,中原文化得到广泛传播,特别是乐浪郡呈现出一派汉文化景象,形成了考古学所称的“乐浪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