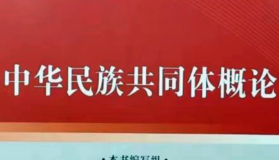-
1 授课视频
-
2 章节测验
春秋战国是一个群雄并峙、战争不已的动乱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族群大融合的时代。五百多年里,大国鲸吞小国、强国兼并弱国从未停止,连年的兼并战争中,先后涌现出“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促成了区域性的政治统合和族群融合,造就了一批对中华民族历史进程影响至深的“大夷”,也极大地拓展了中华民族的核心区。在频繁而深入的交流融合中,“诸夏”凝聚为“华夏”,与“四夷”等族群共同融汇成华夏共同体,如江河汇入湖海一样再也无法分割。随着“天下一家”观念的深入人心以及对“天下一统”的追求,列国林立的局面最终被统一多民族王朝所取代。
西周灭亡后,诸侯崛起,周王朝名存实亡。在强烈的统一王朝观念作用下,实力强劲的诸侯开始了一系列探索,试图弥合分裂的政治局势,建立起新的天下秩序。
春秋早期,北方戎狄大规模南下,与诸夏列国发生了一系列冲突与战争,甚至灭掉了邢国与卫国这两个重要的姬姓封国。齐桓公以此为契机,打出“周天子”的名号,高举共同对抗“戎狄”的旗帜,统合天下秩序,领导天下诸侯。因此,后世将齐桓公称霸的策略总结为“尊王攘夷”。这一策略很大程度上被此后的春秋霸主所继承。从短期来看,这一策略起到了凝聚认同的作用,诸夏列国共同面对一个强有力的“他者”,彼此之间差异弱化,加强了相互之间的交融和认同;但从长期来看,无论是“尊王”还是“攘夷”,都是诸侯在周王朝衰微的情况下尽力维持天下秩序的一种手段,而非主要目的。实际上,霸主们既没有真正“尊王”,因为周朝仍处于持续衰落中;也没有真正“攘夷”,因为齐、晋等国虽与北狄的部分支系爆发过较为激烈的战争,但其规模与强度在春秋时期不算突出。诸夏列国与“东夷”诸国长期和平共处、深度融合,与“南蛮”大邦楚国也在大部分时间里维持了和平交往,北方戎狄的许多部族也与诸夏列国保持着友好关系。而在春秋霸主中,除了齐国和晋国,其余的楚、秦、吴、越均在不同程度上一度被中原列国视为“戎狄”。然而,一方面,楚、秦、吴、越积极学习中原文化,在文化和政治形态上有了质的跨越;另一方面,中原诸夏列国并未将之视作仇敌,而是积极调整战略,与之充分合纵连横。当“霸主”都曾出身于“蛮夷戎狄”,而列国甚至周天子也在事实上认可其地位时,春秋霸主“尊王攘夷”也不具备实质意义。
春秋后期,“华夏”的观念开始出现,并逐渐取代了“诸夏”。“诸夏”是一个复数概念,先有了一个个“有夏”之邦,再有这个集体的统称。个体边界是明确的,一般就是一个邦族,因此“诸夏”作为一个集体的边界也是相对明确的。而从“诸夏”“诸华”到“华夏”,不仅是从复数概念变成了单数概念,也从若干邦族的集合体变成了一致认同的共同体,这意味着内部个体界限的逐渐消弭,如同多条河流汇聚成一片江海。
但是,华夏共同体并没有只停留在“诸夏”的边界,而是继续融汇更多族群。北狄的大规模南下并未造成华夷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反而促进了戎狄与诸夏人群的大规模融合。杂居是族群大规模、深层次融合的重要因素。由于自然环境变化等原因,春秋时期“蛮夷戎狄”深入中原与诸夏列国混居。春秋前期还颇为常见的华夷交战,到后来就转变为华夷之间的交错融合。到春秋战国之际,中原的族群分界已经相当模糊,无论是原来的“诸夏”,还是“蛮夷戎狄”,基本都融入华夏共同体。
春秋时期的列国兼并,也是推动族群融合的一大原因。春秋霸主都是通过兼并小国而成的。据文献记载,楚国、晋国均灭国数十,秦国灭国十二,齐国、吴国、越国也吞并了若干邦族。这些大国的兼并行为,一方面是政治上的区域统合,另一方面也是区域性的族群融合。楚国统合了江汉流域的族群,晋国统合了黄河以北的族群,秦国统合了关中平原和河湟地区的族群,齐国统合了山东半岛北部的族群,吴、越统合了淮水下游至太湖、钱塘江流域的族群。随着各国内部集权和县制推行,区域内各族群遂归属于同一政治实体。
当历史进入战国时期,天下分裂已久,甚至文字已经分为晋、楚、秦、齐、燕五个系统,彼此差别较大。但长期以来各族群强烈认同天下的政权应当集于一统,“分”终究要归于“合”,这已经成为中国历史理所应当、势所必然的基本逻辑。所以,当梁惠王问孟子“天下恶乎定”时,孟子明确地回答他“定于一”。虽然当时诸子百家政治见解各异,但有一条共同的底线,即建立“统一秩序”。儒家强调“定于一”;法家强调“车同轨、书同文”;墨家强调“尚同”与“执天下为一”;即便主张“无为而治”的道家,也反复探讨“取天下”和“天下王”的奥秘,主张“万物虽多,其治一也”。“天下一统”是包括儒、法、墨、道等诸子百家各门各派的共同主张,也是处于战乱中的天下各族的共同心愿。最终完成天下归一的并非诸夏列国,而是“大夷”秦国。
西汉思想家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将所谓“蛮夷戎狄”分为两类:“小夷”和“大夷”。“小夷”指的是不具国家形态、未聚合成邦国的赤狄、白狄、犬戎等,“大夷”则是充分吸纳华夏文化、已形成邦国且国力相当强大的楚国、秦国、吴国、越国等。楚、秦、吴、越长期被中原列国视为“蛮夷”“虎狼”,但无论是政治统合,还是族群交融,这些“大夷”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春秋时期,戎狄与诸夏列国杂处的情形非常普遍。狄人中的赤狄与白狄两大分支纵横中原,西至晋国、东至齐鲁的列国多与之交战,同时也不断融合。在“天下之中”的伊洛平原上,也生活着扬巨、泉皋、伊洛之戎和陆浑之戎。近年来考古发掘的河南伊川徐阳墓地,多数学者认为就是陆浑戎的墓葬。”诸夏列国与这些戎狄之间,有和平交往,也有兼并战争,但都使得交往交流程度不断深入,最终走向融合。当时亦有很多重要政治人物因各种原因来到别族之地生活,并在杂居中完全融入。
如楚国贵族苗贲皇,本是楚国公室分支若敖氏的族人,其父还担任过楚国令尹,后来因政治斗争失败而来到晋国,成为晋国的著名贤臣。另一位楚国贵族屈巫臣,因为得罪了当时在楚国掌权的令尹子重和司马子反,投奔了晋国,为晋国策划了扶持吴国以制衡楚国的战略,成为晋楚争葡形势改变的转折点。苗贲皇和屈巫臣为晋国效力的故事,就是成语“楚材晋用”的写照。而屈巫臣的儿子屈狐庸,则被派遣常驻吴国担任“行人”。40年后,屈狐庸已经成为彻底的吴国人,作为吴王的使者与晋国沟通。晋国大夫伯宗,被晋国的权臣家族邵氏杀害,其子伯州犁被迫迁往楚国,成为楚国显赫的贵族。后来,伯州犁之子邵宛又被楚国的奸臣费无极陷害,自杀身亡,其子伯蓄被迫迁往吴国,成为掌握吴国政权的太宰。
战国时期,华夏人群开始与北方草原族群杂居交融,也对“流沙以西”和巴蜀以南的人群逐渐有了进一步了解。譬如,战国中期赵国的赵武灵王攻占了原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南),利用这里广阔丰美的草原养马练兵,而兵源既有华夏边地的善骑之民,也有招揽收编的胡人骑兵。华夏人群在和胡人接触后,充分认识到“胡服”的便利性,于是改穿草原游牧族群的上衣下裤和胡衣胡帽,这就是著名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上古中原先民对“天下”西界的认知长期停留在河西走廊一带,再向西则夹杂了具有神话色彩的地域想象,这种情况到战国时期有了根本性的改变。《逸周书》《山海经》等典籍中记载了生活在“西域”的各族群之名,如大夏、莎车、竖沙、居繇、月氏。这些都是那个时期生活在新疆到中亚地区的族群,如“大夏”就是“吐火罗”的音译,说明华夏人群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和新疆地区的人群进行直接交往。
华夏人群与巴蜀以南也就是今云南地区人群的直接交往是由楚人推动的。战国后期,楚国将军庄踽受楚王派遣,沿长江而上,经略黔中、巴蜀等地,进而向南进入云南。庄踽及其部众在滇池一带开辟了数千里肥沃的土地。由于秦国攻占巴蜀,断绝了归楚之路,庄踽及其部众就留在滇地,和原居于此的人民一起开发这片土地。庄踊积极融入当地人群,接受当地文化,改穿滇地的服装,成为滇地人民的首领。从考古学上看,战国晚期滇地的青铜文化有一次飞跃式的发展,很可能与庄踽入滇带来了先进的制度文化和青铜冶炼技术有关。
随着各族群间的血缘融合更为深入,许多重要的历史人物都诞生在跨族群婚姻的家庭中。如晋文公与孔子。晋文公重耳是晋献公和狐姬所生,他一直与自己母族狐氏狄人关系密切,其舅狐偃是一直陪伴在他身边的股肱之臣。晋文公在流亡的19年间,有12年生活在狄人部族中。他还娶了另一支戎狄腐咎如的女子季隗为妻,生下了晋襄公。就是这位出身于族群融合家庭中的晋文公,日后带领晋国成为天下霸主,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具有深刻影响。
孔子的父族是宋国国君后裔,而宋国国君又出自殷商王室,所以孔子常以“殷人”自居。春秋初年,孔子的先祖迁徙到了鲁国都城曲阜,在这个周礼最兴盛的邦国生活了数代。其父叔梁纥娶了颜氏女,生下孔子。而颜氏据传说是东夷之邦邾国的公族后裔。孔子出生于其父亲担任长官的邹邑,这里曾是邾国的旧都。他的身上流淌着商王族和东夷人的血液,生于东夷旧地,长于周礼之邦。身兼多种族群文化身份的孔子,成为儒家的创始者,是古代中华文明最重要的代表性人物。似晋文公和孔子这样的跨族群家庭后代,在春秋时期十分常见。
春秋晚期,东南方的吴国崛起。原本诸夏列国都将吴国视为“蛮夷”,但随着吴国的强大,列国纷纷与吴国联姻,不少姬姓国也打破“同姓不婚”的礼制与吴国联姻。如鲁昭公就曾迎娶吴国国君的大女儿为妻,蔡昭侯则将自己的大女儿嫁给了吴王(在陪嫁青铜器蔡侯申盘的铭文中记载了此事,图4-8)。
周朝建立后,随着疆域的扩展和各族群的大规模迁徙,“汉字”文化圈也进一步扩展。文字所承载的文化对“西戎”“北狄”“东夷”“南蛮”产生了深远影响,推动了各族群间的文化交融。
春秋后期,有一位名叫“驹支”的戎人首领,曾明确表示,虽然“诸戎”与华夏之间多不能进行直接的语言沟通,但他本人深谙华夏文化和诗书典籍,是一位能够在政治活动中“赋诗言志”的博雅君子。
战国时期的中山王是白狄的分支鲜虞的后裔。20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河北省平山县发现了中山国的都城灵寿故城以及中山王墓。该墓出土了“中山三器”(图4-9),三器的铭文集中体现了中山王对华夏文化的高度接受。其铭文书法隽永,文辞典雅,很多语句与《论语》《诗经》《礼记》《周礼》《左传》等儒家经典颇为接近。如铜鼎铭文“寡人闻之,与其溺于人也,宁溺于渊”与儒家典籍《大戴礼记·武王践阵》中“与其溺于人也,宁溺于渊”的词句基本一致。方壶铭文“夫古之圣王,务在得贤,其次得民。故辞礼敬则贤人至,蹇爱深则贤人亲”体现出儒家“民本”“仁政”思想。这与传世文献中记载这一时期的中山国“专行仁义,贵儒学,贱壮士,不教人战”(《太平寰宇记·定州》)相呼应。由此可见,这位北狄出身的中山王是熟读经典、推崇儒学的,足见中山国的上层贵族早已接受了汉字,并且受到了华夏文化的深远影响。
东夷诸国本身就是非诸夏族群中文化较为发达的一支,东夷郯国国君郯子就是孔子的老师。大概在孔子30岁的时候,郯子到鲁国朝拜。鲁国的大夫叔孙昭子问起“少峰氏鸟名官”之事,郯子就对鲁国的贵族讲起了黄帝、炎帝、共工、太睥、少啤等族群的职官名称由来,以及少醵氏以鸟名为官称的详细情况。孔子听到之后,感慨道“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拜郯子为师。
早期楚国是“南蛮”的代表,常常被中原列国贬称为“荆蛮”。早在西周时期,楚国贵族就已经广泛地使用汉字了。如传世的“楚公家钟”“楚公家戈”“楚公逆钟”“楚公逆馎”等,都是西周时期楚国国君的青铜器,其形制与铭文格式都与中原诸夏列国的青铜器大同小异。到了春秋时期,楚国与诸夏列国的文化交流更为密切。尤其是春秋晚期的周景王之子王子朝带着周王朝所藏的典籍出奔到楚国后,楚国迎来了文化大发展时期。中原礼乐文化与楚地本土文化,孕育出绚烂多彩又颇具特色的楚文化,催生了先秦文学的高峰《楚辞》以及大文学家屈原、宋玉。楚地原本若即若离地处在华夏文化圈的边缘,此后即成为华夏文化圈的核心组成部分,其南方的百越、滇地也逐渐受到华夏文化的影响。这是先秦时期中华民族核心区的一次重要扩展。
相较于楚国人群,地处东南方的吴越人群与诸夏列国的文化差异在早期更为显著。在《说苑》所载的《越人歌》和《越绝书》所载的《维甲令》中,都保留了春秋战国时期用汉字记录的百越人的部分语音。根据当代语言学家的研究,古越语与现今的壮侗语族有密切的关系。但百越是较早学习使用中原“雅言”的地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吴越贵族使用的文字就是汉字,并且对汉字的字形进行了艺术化改造,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鸟虫书”。大量吴越青铜器上都有以“鸟虫书”铸刻的铭文,如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的国宝“越王勾践剑”(图4-10)。“鸟虫书”字形繁复优美,极具艺术价值而又不失汉字构形的理据,是古吴越人对汉字文化创新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
春秋中后期,吴越与诸夏列国才开始有所接触,短短数十年后,吴国就出现了一位以“晓诗书、通礼乐”折服了中原列国的人物——王子季札。季札曾出使中原列国,与当时许多著名的士子,如叔孙豹、晏婴、子产、叔向等结下深厚的友谊,留下一系列充满智慧的对话。季札在鲁国遍观周乐,聆听《诗经》中的国风、大雅、小雅和颂,还欣赏了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等不同时期的音乐。对这些乐舞,季札都做了精妙的点评,堪称中国音乐史上第一篇系统的乐评。后人赞誉季札为“穆穆延陵子,灼灼光诸华”。
经过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各族群开始酝酿出更深层次的文化共性,形成了共同的祖先认同。在商代和西周时期,中国大地上生活的各个族群有各自不同的祖先神。据甲骨卜辞,殷人祭祀的始祖是“高祖要”(有学者认为其就是“帝喾”)。《诗经·大雅·生民》记载,周人的始祖是后稷。《左传》和《国语》中记载了很多邦族的祖先,譬如郯国的祖先是少峰,任、宿、须句、颛臾等风姓邦族的祖先是太峰,六国和蓼国的祖先是皋陶,姜姓的祖先是太岳(亦称“四岳”)。楚国是祝融的后裔所建,陈国是颛顼的后裔所建,秦国是伯翳的后裔所建。
到春秋时期,黄帝的传说已经出现,但当时黄帝还不是各族群的“共同祖先”,而只是姬姓人群的始祖。孔子的老师郯子将黄帝、炎帝、共工、大峰、少峰并列,说明在当时的观念中,黄帝还只是各族群众多始祖中的一位。
进入战国时期,原本纷繁并列的众多祖先传说开始出现融合的迹象,黄帝走向“共祖”的地位。较早的史料记载,姬姓的始祖是后稷,姜姓的始祖是太岳,彼此并无联系;后来,姬姓的始祖上溯到黄帝,姜姓的始祖上溯到炎帝,而黄帝、炎帝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弟,这就从血缘上将二者的祖先紧密联系起来了。
在《世本》记载中,原本与黄帝并列的祖先神帝喾和颛顼,也变成了黄帝的曾孙和孙子。《大戴礼记》中的《五帝德》和《帝系》两篇,则建构了自黄帝以下完整的祖先传说体系,这一体系后来被司马迁的《史记》继承发扬。原本以帝喾和颛顼为始祖的邦族,此时自然也统统归属于黄帝世系之下,将黄帝作为自己的始祖。譬如晚清出土的战国青铜器“陈侯因齐敦”(图4-11),是田氏代齐后的齐威王所作,他仍称自己是“陈侯”,说明他认同自己是陈国后裔;但在追述自己的祖先时并未提到颛顼,而是直接上溯到了“高祖黄帝”。
类似的现象,也发生在秦国与楚国。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国的祖先伯翳是颛顼的后代;据《大戴礼记·帝系》记载,楚国的先祖重黎是老童之子,而老童是颛顼之子。据载颛顼是黄帝之孙,所以说秦国、楚国之人自然也都是黄帝的后裔了。
汉朝以后,东夷的祖先神少峰(少昊)与太腺(太昊)也不同程度地融入了黄帝传说的体系中。据许多文献记载,黄帝与少瞭之间是父子关系,有说“黄帝者,少昊之子”的,也有说“少昊,黄帝之子”的。太峰则与伏羲合二为一,成为黄帝之前的一位远祖。
在中国古代历史中,黄帝后裔的群体规模不断扩大。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和《史记·匈奴列传》的记载,本不说汉语的越人和匈奴人被视作“禹之苗裔”和“夏后氏之苗裔”,而夏禹是黄帝的后代,黄帝也就被视作越人与匈奴人的始祖。此后的史家也延续了这种叙事体系,譬如《魏书·序纪》记载鲜卑人是黄帝之子昌意少子的后代;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将“西南夷”纳入黄帝世系之下,源生于西南山地人群的祖先神,也进入了华夏文明的神话传说体系。可见历史上各族文化绝非单向输出,周边族群对华夏文明的影响也相当深刻。
黄帝是各族共同祖先这一观念的形成,是春秋战国时期各族群不断交流融合的结果。将黄帝认同为“共祖”,虽不能反映全部真实的历史,但确实可以反映春秋战国时期各族群不断凝聚成一个更大共同体的主观意愿。当原本分立的各族群因不断交流融合而形成共同体时,彼此之间的区别就退居其次了。既然大家都认同彼此属于同一群体,就会反过来重构自己的祖先传说,形成世人皆认可的共同祖先。
因此,有研究者认为,通过修改本身的族源历史,各族群相互结合,并由共同的族号来宣示新的族群范围,形成族群的自我意识。就中华民族而言,这一过程大致发生在西周、春秋时期。此时黄河、长江中下游各人群间,出现共同的族号(华、夏、华夏或中国)以及共同的祖源(黄帝)。
小结
夏商周上承五帝时代,下启秦汉王朝,是古代中华文明由萌发走向兴盛的关键阶段,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孕育阶段。在近两千年的漫长历史进程中,中原及其周边地区逐渐发展出诸多族群归属于一个国家的政治格局,“天下一家”成为各族群普遍接受的观念。各族群在不断杂居与通婚中打破了旧有的血缘边界,实现了深度融合和共同发展。汉字文化圈不断扩展,各族群在交流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了共同的祖先认同。周朝修建了纵横天下的道路体系,进一步将天下各地的族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跨地区的物品资源流通也加强了各族群间的经济联系。中华大地上的先民们“最终熔铸为一个人数众多的文化、经济、政治共同体”,确立了华夏共同体的基本框架。
华夏共同体在长期动荡战乱的春秋战国时期趋于成熟,但政治上的分裂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华夏共同体的进一步融合和扩展。秦、楚、齐、燕等列国之人心中的强烈地域意识不容忽视,更遥远的北方匈奴、南方百越、西域诸国、西南滇人等仍被视为“他者”。华夏共同体内部的更深层交融和以更开放的姿态拥抱更多周边族群文化,则需要在大一统王朝建立的时候才能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