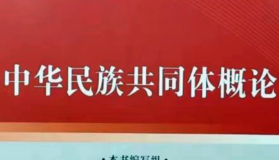-
1 授课视频
-
2 章节测验
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习近平
历史上第一个世袭王朝,建立于约前2070年,标志着中原及其周边地区形成了诸多族群归属于一个王朝的政治格局。约前1600年,东方的商人崛起,建立商朝。至前11世纪,西部的周人兴起,代商而建立周朝,定都丰镐(今陕西西安),史称“西周”。前771年,西周灭亡,随后周平王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史称“东周”。东周大致分为春秋(前770—前476)和战国(前475—前221)两段,是历史上群雄争霸追求一统的动荡时期,也是族群大迁徙大交融的重要时期。
最迟在夏中晚期,中原地区就已经发展出空前繁荣的经济生活与文明形态。经由夏商周三代不断治理与巩固,中原地区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在这一核心区,分布着诸多不同族源的邦国,自称为“夏”或“华”,形成了具有共同文化认同的“诸夏”。“四夷”人群(包括“三苗”)有的居住于核心区域的周边地带,有的在核心区域内与诸夏人群混居,受到华夏文化的浸润与影响。
夏商周三代,王朝疆域逐步扩大。夏朝统治的范围主要限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商朝已扩大到河南大部、河北中南部、山西南部以及山东西南部。西周时,已北至燕山南北,南到江汉流域,东至山东半岛,西达甘肃天水。随着疆域的扩大、族群的增多,商朝和西周都实行分封制和灵活开放的族群治理政策,各族群间的交往交流不断加深。
西周初年出现了华夷交战与“华夷之辨”,但没有改变“诸夏”邦国之间、“诸夏”与“四夷”之间边界弱化的趋势。春秋后期,“华夏”的观念开始出现,并逐渐取代“诸夏”。相比于多个邦国集合体的“诸夏”,“华夏”强调一个人数众多、边界开放的文化、社会、经济、政治共同体,认同华夏文化的“诸夏”“四夷”皆处于其中。随着族群交融与思想交汇的深化,华夏共同体日趋发展、稳固与成熟。
春秋战国时期,分裂带来的战乱让“统一”越发成为各邦族的共同追求,使得“天下”作为贯通政治秩序、经济结构、社会形态、精神世界的整体性体系得以确立,“天下一家”成为世人普遍接受的观念。崛起于“四夷”之地但继承华夏文化的强大邦国,如楚、秦、吴、越,在促进文化交流与族群融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最终,曾被视为“大夷”的秦国实现了天下一统。
正是在夏商周时期,华夏共同体出现并发展;各族群在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上不断加强、凝聚,越来越多的族群与文化进入共同体,为秦汉大一统王朝奠定基础,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确立了初始格局与演化路径。
夏商时期是中华文明的早期发展阶段,也是早期国家初创的时期。中华文明核心区在这一时期初步形成,被“天下”各族群认可为“共主”的中央王朝出现并逐渐稳固,族群交流范围主要集中于中原及周边地区,文化层面的交流范围则远超王朝疆域,汉字文化圈初具雏形。
夏(约前2070—约前1600)直接统治的疆域大致是山西省南部、河南省西部一带。夏朝处于早期国家初创阶段,比较完整地保留了氏族组织结构。文献中所见的夏朝邦国,基本都是以“氏”为称,如有扈氏、斟鄂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辛氏、冥氏、斟戈氏、防风氏、有穷氏、豢龙氏等。这说明当时“族”是构成邦国的基本单位,一邦就是一族。这些邦族最初建立的合法性及日常管理规则并非来源于夏。而夏朝相对强大的军事实力和文化辐射力,形成了周边邦族对其“中央”地位的认可,但这种等级从属关系较为松散。
夏早期政权异动频繁。根据古史传说,大禹通过治理水患确立了“天下共主”的地位,但其子启则是通过与伯益部族的战争才夺得王位。后来有扈氏反对启,爆发了甘之战。至启子太康为政时,有穷氏首领后羿(又叫“夷羿”)夺取夏政权。后来有穷氏又被寒浞取代。历经数代争斗,夏王室后裔少康最终夺回王权,夏朝的统治才得以稳定。
夏朝中后期(约前1800—约前1600),中原地区突破了地域局限,对周边区域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影响,创造了空前璀璨的文明。河南偃师的二里头遗址被认为极有可能是夏朝后期的都城,二里头文化的典型器物“牙璋”扩散并影响到东亚大部分地区,北至陕北地区,南至岭南珠江流域,东到山东半岛,西到四川盆地,标志着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核心区已在中原形成。
这一时期,生活在东亚大陆东部的人群已与生活在今新疆地区的人群有所交往,并发生血缘融合。21世纪初,于新疆罗布泊地区发掘的小河墓地(距今约4000—约3400),其时代与夏朝大体相当。古DNA检测证实,小河墓地人群的母系遗传构成已有东亚人群的遗传成分。
到夏朝晚期,与东夷有密切联系的商部落逐渐兴起,他们通过战争推翻夏朝,建立了商朝。商朝的疆域仍以中原为核心,但直接治理的“王畿”范围已涵盖今河南省中部、北部的大部分地区,较夏朝治理范围有所扩大。同时,商朝还在距离“王畿”较远的地区建立了若干军事据点,实现对更广袤疆域的有效掌控。例如东下冯商城(今山西夏县)、垣曲商城(今山西垣曲)、盘龙城商城(今湖北武汉),均在商朝早期就已建立,其目的是安定夏朝遗民、西方族群和南方族群。商朝的政治辐射至河南大部、河北中南部、山西南部以及山东西南部,其与周边族群交往交流的范围不断拓展。西南已达四川盆地,对古蜀文化影响至深。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的大量玉器,在类型、形制上与中原的玉器有诸多共性;三星堆青铜尊(酒器)、青铜燥(酒器)的造型,基本仿照了中原青铜器的同类器型。西北则触及新疆地区,殷墟妇好墓中就发现了由新疆和田玉料制成的玉器(图4-1)。
商朝后期,商人结束了频繁迁都,都城稳定于殷(今河南安阳)。以国都为核心的“王畿”地区被称为“商”,也称作“大邑商”,是商人的统治区与核心聚居区,商朝的各级贵族多居于此。“王畿”之外是“四土”,包括东土、西土、南土、北土。那些名义上臣服于商朝的邦族分布于“四土”,如东土的人方、林方、危方,西土的羌方、羞方、召方,南土的雇、息、虎方,北土的土方、孤竹等。“王畿”与“四土”,又被称为“内服”与“外服”,对应着不同的管理方式和职官体系,它的雏形可能在夏朝就已出现,到晚商时期发展成为较为完备的制度,体现了商朝族群治理的智慧。
商朝对“内服”实行直接统治,对“外服”的邦族则一般不干预其内部事务。臣服于商朝的邦族要履行一定的义务,如定期向商朝纳贡,商王征战时要派兵参战;商王也可以到“外服”邦国的土地上田猎。总体来看,各邦族与商王室的联系仍然不够紧密,其忠诚度主要取决于与商王室关系的亲疏程度。到商朝晚期,“天下”还未形成一个完全将各邦族囊括在内且稳定有序的政治实体。
文字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载体,也是历史上中华民族内部各族群间文化交流的主要媒介。商朝各族群交流融合的广度和深度,较之夏朝已进一步提升,其重要的标志之一就是文字的广泛传播与应用。虽然先秦时期各族群语言并不相通,但文字的使用打破了语言的界限。汉字的萌生可能很早,目前所知最早的成体系的汉字材料是发现于安阳殷墟的商朝后期甲骨文,这是一种刻写在龟甲或动物骨头上的文字,主要记载当时占卜的内容。在商朝晚期,甲骨文的使用范围已大大超出中原,西方的陕西周原、东方的山东大辛庄均发现了甲骨文字。1959年,湖南宁乡出土了一件商朝晚期铸有“大禾”铭文的人面纹方鼎(图4-2),这里不在当时商朝的政治影响范围内,但文字仍在此使用。
青铜器的大规模使用也加强了商朝与周边族群的经济、政治、文化联系。商朝是中国青铜文明的高峰,对青铜矿料有极大需求。青铜的合金成分主要是铜和锡,中原地区缺乏大规模、高品质的铜、锡矿产,而南方的长江流域则分布着较为丰富的此类资源。因此,商人在长江、汉江交汇处建立城市,以此控制南方的铜、锡资源,并在中原与长江中游之间建立起转运此类矿料的通道。部分方国接受了商朝以青铜器为代表的礼乐政治文化,如大辛庄、苏埠屯、新干大洋洲、三星堆等遗址都出土商式青铜器。可见,青铜文明的发展极大地扩展了族群间直接交往交流的范围,有效地将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诸族群联系起来。
族群间的文化交流从来不是单向的。殷墟妇好墓中发现了大量体现周边文化元素的文物,包括具有草原文化元素的青铜器、承载海洋文化元素的海贝,以及和田玉料等。同时,先秦时期并非只有中原语言文化影响了周边族群,周边族群也给中原文字文化增添了若干新词,其中一些已成为汉语中的基本词汇。如“贝”“牙”“狗”等可能是来源于苗瑶语、侗台语等语言的词汇,已经成为汉语中不可分割的要素,体现了“润物细无声”这一历史上中华民族内部各族群文化交流交融的常态。
商朝虽不再像夏朝邦国那样以“氏”为称,而改为以“方”为称,却仍未改变聚族为邦、一族一邦的社会结构。其各族群地域意识加强,但尚不具备族群间大规模交融的条件,未形成深入社会基本单位的族群交融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