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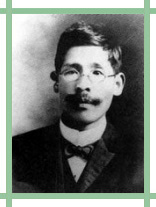
藤野先生是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候的一位老师。
有研究者注意到,《藤野先生》这篇文章的手稿题目经过了一番涂改,涂改前的题目是《吾师藤野》。无论是“先生”还是“吾师”都强调了藤野的教师身份。
鲁迅还曾经写过其他几位师父:第一位师父是个世俗气息浓厚的和尚,他是可亲可爱龙师傅;三味书屋中有一位方正、质朴、博学寿镜吾老先生,这是鲁迅的启蒙老师;还有一位是大名鼎鼎的语言文字学家章太炎先生,鲁迅临终还写文章追念这位老师。
但在这些老师中,鲁迅给予最高评价的是藤野先生。在《藤野先生》一文中这样说道:“但不知怎的,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 一个“最”字写出藤野先生在鲁迅心目中无人能比的地位。
由此,我们迫切地想知道:藤野先生到底怎样伟大呢?与赫赫有名的章太炎先生相比,藤野先生是一位默默无闻的平凡教师,并没有什么惊世骇俗的学术成就,正如鲁迅所说,“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知道”。鲁迅曾经用文字速写记下了藤野先生第一次来上课的情形。“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不仅其貌不扬,而且不修边幅,甚至闹出一个笑话。由于“穿衣服太模糊了,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冬天是一件就外套,寒颤颤的,有一回上火车去,致使管车的疑心他是扒(二声)手,叫车里的客人大家小心些。”鲁迅也曾经亲自见到他“有一次上讲堂没有带领结。” 生活中,藤野先生的外表是朴素甚至寒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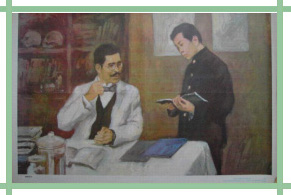
那么是否,他对鲁迅有格外的关照呢?
有一个周六,他使助手来叫鲁迅去研究室。研究室中,藤野先生坐在人骨和许多单独的头骨中间,正做着骨学的研究。他问鲁迅:“我的讲义你能抄下来么”,之后,藤野先生真的收下鲁迅的讲义,亲自审阅修改。并约定每一个星期都要如此。当鲁迅打开藤野先生返还的讲义,内心的感受十分复杂。鲁迅一连用了三个词:“吃了一惊”“不安”“感激”,原来鲁迅交上去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修订了讲义内容的脱漏,连日文文法的错误也一一订正。就这样,一直继续到藤野先生教完了他所担任的所有功课。藤野先生对鲁迅的功课认真负责,是一位非常敬业的老师。
还有一次,藤野先生把鲁迅叫进研究室,当面指出鲁迅所绘制的解剖图不够严谨,血管被擅自移了位置。这样画虽然美观,但是与实物不相符合。他随即叮嘱鲁迅要严格“按照黑板上那样画”,因为“解剖图不是美术,我们没办法改换他。”这朴素的话语中包含着高屋建瓴的指导:做学问就应该遵循实事求是、严谨求是的原则。
藤野先生对鲁迅不仅有学科专业上的辅导,还有文化风俗上的关心。
在解剖实习进行了一周之后,藤野先生叫鲁迅到研究室去,用极有抑扬的声调说道:“我因为听说中国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担心,怕你不肯解剖尸体,现在总算放心了,没有这回事。”藤野先生的这份担心,首先就表明他用心细致,关照到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心理。后来,看到鲁迅顺利实施解剖,便放心并高兴起来,可见学生的进步就是藤野先生的快乐之源。

藤野先生曾经询问鲁迅中国女人的裹脚致畸的情形。裹脚是怎么裹法?足骨变成怎样的畸形?待到鲁迅回答完毕,还一边叹息着,“总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两问一叹,很具有藤野先生的风范,一面是细致追问、希望亲自考察,严谨且敬业;一面是悲叹中国女人的不幸,国际主义的关怀,令人感到温暖、人性。在藤野先生眼中,旧中国还有许多落后愚昧的文化,他热心帮助鲁迅,不倦地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
不是为了母国而是为了中国,不是为了一己之私而是为了科学学术的发扬光大。科学是具有超越性和普遍性的,在这里,藤野先生身上呈现出的超越了民族、国界的光辉,这其实就是科学的光辉。

藤野先生在日本昭和13年《文学向导》刊物上发表过一篇回忆鲁迅的文章。
文章反复提及记忆之模糊,有四五次之多,可见藤野先生对鲁迅并非印象特别深刻,或是寄予怎样的厚望。文章写道:“因为是多年前的旧事了,所以记忆不是很清楚。”“周君也到我家里来玩过,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了。”“如果我过世的妻子还在世的话,或许还可以回忆起一些事情。”“周君临别时来我家道别,不过我忘记这次最后会面的具体时间了。据说周君直到去世一直把我的照片挂在寓所的墙上,我感到很高兴。可是我已经记不清是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形式把这张照片赠送给周君的了。”
关于令鲁迅大受感动的著名的修订讲义一事,藤野先生也提起了,“当时我主讲人体解剖学。周君上课时虽然非常认真地记笔记,可是从他入学时还不能充分地听、说日语的情况来看,学习上大概很吃力。于是我讲完课后就留下来,看看周君的笔记,把周君漏记、记错的地方添改过来。”
可见,修订讲义、文法是确有其事。但对于鲁迅的高度评价,藤野先生却感到大为惊讶。
“我虽然被周君尊为惟一的恩师,但我所做的只不过是给他添改了一些笔记。因此被周君尊为惟一的恩师,我自己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在藤野先生平淡的叙事看来,他只是履行了教师的本分,这一切并没有非同一般的意义。而鲁迅则把这一切搬上了神坛,为藤野先生佩戴了崇高的光环。
这种落差让我们有点失望。失望之余,我们还要追问:为什么师生之间普通的事务,在鲁迅主观世界里能产生了那么强烈效应呢?
藤野先生在文中给出了线索:“如果是在东京,周君大概会有很多留学生同胞,可是在仙台,因为只有周君一个中国人,想必他一定很寂寞。”
这就让我们注意到《藤野先生》一文,开头五段的闲笔其实并非闲笔,而是对于鲁迅处境的非常重要的提示。
说道鲁迅的处境,恐怕还要从鲁迅的故土一路说起。祖父下狱,父亲亡故,经历了从小康之家坠入困顿,鲁迅在故乡绍兴饱尝了世人的冷眼。在遭到族人的排挤、流言中伤之后,他带着八元川资走异乡、逃异地,来到南京新式学堂求学,辗转几所学堂,末了,于学问上还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不相见”。怀着这样的失望、惆怅、迷茫、无助,鲁迅来到日本留学。
藤野先生就指出,周君的同胞大多在东京留学。只有鲁迅一个人在仙台,因此,他是寂寞的。与同胞在地理空间的隔绝,是否是他精神寂寞的原因呢?

鲁迅在开头这样描述东京的留学生:“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象绯(fēi)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鲁迅由发型入手,对这些封建遗少的扭捏作态,进行了无情、幽默的嘲讽。在生活做派上,鲁迅与他们也是格格不入的。这些清国留学生的住处,地板常常咚咚地响得震天。那是他们在学跳舞。到东京来,难道就是为了跳舞玩乐吗?这种吃喝玩乐的做派,鲁迅是非常鄙夷的。清国留学生的圈子,他无论如何也融入不进去。鲁迅的确如藤野先生所说,是孤独与寂寞的,但这种孤独寂寞并非由地理空间造成,而是精神上的距离。
于是鲁迅不愿留在东京,他在文中说: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因此鲁迅在弘文学院结业后来到了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在仙台虽然受到特别的礼遇,但鲁迅对生活仍旧不太适应。先是受到蚊蝇的骚扰后来又要勉为其难喝下芋梗汤。
鲁迅在仙台,远离了他所鄙夷的清国留学生同胞,但并没有远离是非与歧视。根据藤野先生的回忆:“周君来日本的时候正好是日清战争以后。尽管日清战争已过去多年,不幸的是那时社会上还有日本人把中国人骂为‘梳辫子的和尚’,说中国人坏话的风气。所以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也有这么一伙人以白眼看待周君,把它当成异己。”
最典型的的一件事是“漏题风波”。鲁迅在仙台,虽然努力,但因为到日本时间不久,日文还不扎实,因此学习吃力,成绩平平,成绩刚刚合格,用鲁迅的话说:“不过是没有落第罢了”,然而这样的成绩却还是引发了猜忌、招致了侮辱。一是学生会的同学来翻检我的讲义,一是鲁迅受到一封以“你悔改吧”为开头的责难匿名信。两件事情都是日本同学怀疑鲁迅那将将及格的成绩是作弊所得,是得到了藤野先生的漏题暗示。虽然经过调查,流言被熄灭,但鲁迅却对日本人的流氓逻辑愤怒不已:“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60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这公然的民族歧视令鲁迅无法容忍。
藤野先生是在鲁迅身心的困境中出现的:故乡绍兴是那样的世态炎凉,南京的求学之路是那样曲折无望,日本的留学生活又让人感到孤立、屈辱。藤野先生对鲁迅的不经意的关心,就像黑暗中的一丝光亮一般,显得特别辉煌耀眼,因此在鲁迅心中激起层层波澜。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的时候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 可见,鲁迅最初是怀着治病救人、报效国家、传播新思想的崇高愿望,奔赴日本的。在故乡绍兴,父亲被庸医延误病情,奇怪的药引和败鼓皮丸都不能医治他的水肿,丧父之痛使鲁迅清醒地意识到中国医学科学的落后。鲁迅就希望将最先进的现代医学带回故土。
但“幻灯片事件”却改变了鲁迅原本的志向。这件事情非常有名,鲁迅在《藤野先生》《呐喊自序》《阿Q正传》俄译本序,三篇文章中都讲到事情的经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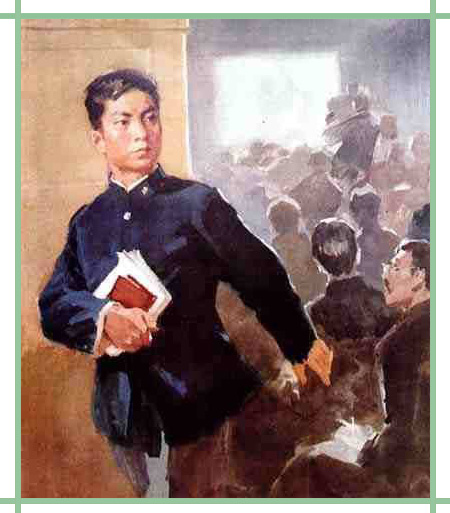
在上霉菌学课的间隙,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教师照例放些风景或时事的幻灯片给学生看。其时,正当日俄战争,有关战事的画片自然较多,大多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面:他们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强壮的体格,而显示出麻木的神情。
往常,每当看到日军胜利的画面,日本同学照例就欢呼鼓掌,这一次也不例外,大喊“万岁!”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鲁迅说:“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何尝不醉酒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
鲁迅在讲完幻灯片的来龙去脉,指出了这个事件对他的影响,他说:“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变化了。”“变化”二字在《呐喊自序》中有更为详细的内心剖白。“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要紧事,凡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务,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为了改造国民性。鲁迅弃医从文,自此走上文艺创作之路,意在通过艺术形象启蒙国人。对看客恶习的批判,贯穿鲁迅创作的始终。在小说《示众》中,在散文诗《野草·复仇》中都有丑陋的看客围观的场面。在杂文《娜拉走后怎样》中,鲁迅更直言不讳地指出:“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到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hú sù)他们就看到了滑稽剧。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办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
直到今天,网络上仍有大量热衷围观的看客,被戏称为“吃瓜群众”。“看客”不是某一个时代的产物,而是与中国人灵魂、骨髓紧紧联系的产物。可见,鲁迅以敏锐的眼光,超越时代的准确性,捕捉到国民性的根本。这就是经典永恒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