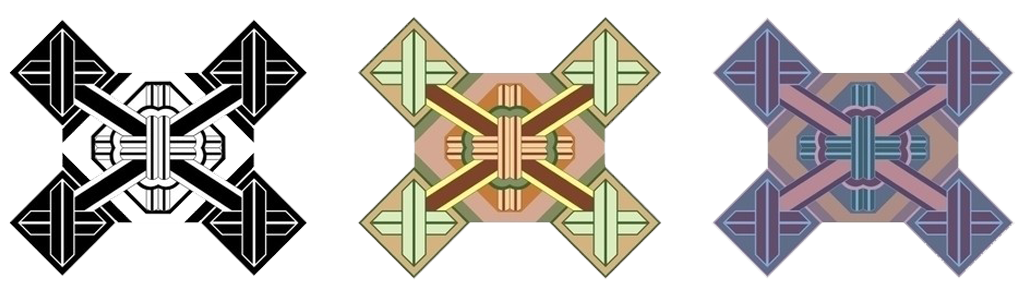
徽商的兴盛主要表现:
![]()
活动范围广
明嘉靖万历年间,徽商足迹几遍全国,不但南北二京、各省都会及其他大小城镇,甚至“诡而海岛、罕而沙漠”万历《休宁县志》,都是徽商活跃的场所,特别是在长江流域,有“无徽不成镇”的说法,经营行业多。徽商只要有利可图,几乎“无货不居”。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工农业产品的日趋商品化,经营盐、典、茶、木等商品的贸易带来巨额利润,成为最主要的行业。
![]()
资本特别雄厚
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清乾隆时,在扬州的徽州盐商汪廷璋就是“富至千万”的大商人了。《扬州画舫录》清朝在其财力最充沛的乾隆四十六年,国库存银尚不及淮商资本之多。两淮盐商之富,竟使皇帝为之动容。乾隆帝南巡时,就曾惊叹“:富哉商乎,朕不及也”。
![]()
投资产业发展
明清时期,已有一些徽州商人将其积累起来的商业资本投向生产领域,开始向早期资产者转化。这种现象虽然不多见,但它却代表着商业资本的新动向,具有深远的意义。徽商数以千百万计的巨额资本,除了捐官、助饷,讨好朝廷与官府,确保自身的地位以外,一部分用于奢侈性的消费,还有相当一部分用于反哺徽州本土。徽商的隆兴,与徽州宗族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积累了巨额商业利润的徽商在家乡建祠堂、修坟墓、叙族谱、购置族产和族田,维系宗族势力。
徽商被人称誉为“儒商”,“贾而好儒”是徽商的一大特色。徽商很注意在家乡对于教育的投资,建义学,助修学院,对族内弟子进行培养。长成后能进入仕途则有了官府后台,不能从政则经商也有了较高的文化素质,以致徽州“东南邹鲁”所具有的“十家之村,不废诵读”嘉靖《婺源县志》’特色延绵不断,至今尚有很大的影响。徽商经济对徽州本土的反馈,对于徽州宗法社会的维系、徽州人才的培养、村镇的建设、乃至徽文化的发展,无疑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在相当程度上,徽商成为徽州整个社会的依靠,是他们支撑起那片山野的天空,当然也支撑起徽州的教育。徽商“肥家润身”之外的教育投资,主要在下面三个方面:
![]()
延师课子弟
徽州为“程朱桑梓之邦”,乡风的熏染,使徽州人“贾而如俗”,在以官为本位的封建社会,读书有显而易见的功利性。发达的商人把读书看作一种政治投资,不惜千金一掷,延名师,买典籍,教育子弟。如狱县商人鲍柏庭“世居狱东新馆·”一家初以贫,奉养未能隆。后以业浙磋,家颇饶裕”,而后“其教子也以义方,延名师买书籍,不惜多金。尝日:‘富而教不可缓,徒积资财何益乎”。对于族内子弟的教育,徽商同样舍得花钱。救县商人余文义设里“义塾以教族之知学者,祁门商人胡天禄捐里田产使“塾教有赖,学成有资”。休宁《茗州吴氏家典》明确规定:“族内子弟有器宇不凡,资案聪慈而无力从师者,得收而教之,或对之家塾,或助以膏火”。狱县潭渡黄氏《家训》也载:“子姓十五以上,资质疑敏,苦志谈书者,众加奖劝,盆佐其笔札裔火之费,另设义学,以教宗党贫乏子弟”。
![]()
捐资修建学校
明清时徽州除了少数几个官办府学、县学,先后建有60多所书院,400多所社学以及无数的塾学。这些学校的建置和运行经费大多来自商人和官徐(其中许多官僚出身商人之家,如汪道昆、胡宗宪,或其家有人经商)。乾隆初年担任两淮总商的徽州盐商汪应庚看到江甘学宫岁久倾倒,“捐五万余金函为重建,同时还以立千余金制祭礼乐器,又以一万三千余金殉腆田一千五百亩,悉归诸学,以待岁修及助乡试资斧”。黔县舒大信“修东山道院,置屋十余楹为族人读书地。邑人议建书院,大信存2400金助之,。翻看《徽州教育纪》,这类例子不胜数举。明清两朝,按国家的统一规定,各周立社学。少数社学的费用出自官方,大部分出自乡族捐助。在其他地区由于经费和管理不善,社会往往难以长期维持下去,但在徽州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究竟原因,正因为徽州各乡各族多商人,他们给了社学源源不断的财力支持,使得各地的社学能够广泛而持久地存在。
![]()
修建宗祠和“忠孝节烈,牌坊"
徽州的宗祠、牌坊难以确切估计,但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建筑之精美、气势之雄伟为别处少有。这项投资看似与教育无关,实则不然。宗祠、牌坊在封建社会不仅具有建筑学上的意义,还具有伦理学和教育学的意义。作为一种棍家伦理的物化象征,它们在道德教育中发挥了范本的作用,徽商在这些方面有一笔不小的开支。如黟县《朱氏祠志》记载隆庆三年正月(1569)修理宗祠正厅门屋就用了“递年生息并贸产,共银一千一百四十三两五钱,许氏家族的一次理主大礼,花费商贾捐款1191元8钱多。


徽商除了上面在本地的种种行为外,他们在客乡也有意或无意地影响着徽州的教育。同治年间,欺商曾以12300余络的巨资在南京创建试馆,作为士子乡试住宿之所。徽商“必据都会”,都会为文化及政治中心,人文荟萃之所。胡适认为徽州子弟多俊秀,是因为受到了占风气之气的都市文化的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