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韵学—概述
汉语音韵学是研究汉语语音系统的科学。它包括古音学、今音学、等韵学等学科。音韵学也称声韵学,它是研究古代汉语各个历史时期声、韵、调系统及其发展规律的一门传统学问,是古代汉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研究方法上,传统音韵学主要使用的是系联法、类推法、统计法和比较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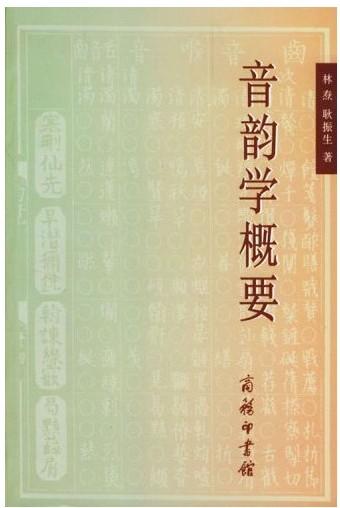 音韵学和语音学不同:语音学是对语音的客观描写,有时还利用各种实验方法,来征明语音的生理现象和物理现象;音韵学则是把语音作为一个系统来观察,它研究各种语音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语音学既然把语音当作生理现象或物理现象来研究,因此有所谓普通语音学,讲述发音器官的作用、各种语音的构成,那是适用于全人类的,只是每一个民族的具体语言还有自己的一些语音特点罢了。至于音韵学,则不可能有“普通音韵学”,因为音韵总是属于一种具体语言的,它具有很显著的民族特点,甲语言的语音系统决不可能跟乙语言的语音系统相同。
音韵学和语音学不同:语音学是对语音的客观描写,有时还利用各种实验方法,来征明语音的生理现象和物理现象;音韵学则是把语音作为一个系统来观察,它研究各种语音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语音学既然把语音当作生理现象或物理现象来研究,因此有所谓普通语音学,讲述发音器官的作用、各种语音的构成,那是适用于全人类的,只是每一个民族的具体语言还有自己的一些语音特点罢了。至于音韵学,则不可能有“普通音韵学”,因为音韵总是属于一种具体语言的,它具有很显著的民族特点,甲语言的语音系统决不可能跟乙语言的语音系统相同。
但是,音韵学又是跟语音学有密切关系的。不能想象,一个人不懂发音的道理而能把音韵学研究好。因此,我们又可以说,语音学是音韵学的基础。
汉语音韵学已经有了一千多年的传统,它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和术语。我们应该用现代的语音学的理论和术语去说明它。我们不能抛开古代的理论和术语不管,因为我们必须把音韵学这份文化遗产继承下来。
音韵学—研究内容
简介
音韵学古代被目为“绝学”,不免令常人望而生畏。一方面,因为汉语为表形语言,汉字与具体读音脱钩,使得解析字音殊为困难,又兼古代并无音标注释字音,学者多以文字描述发音的部位方法等等,隔靴搔痒,旁人看了自然云里雾里。另一方面,又因为音韵学家大多喜欢故弄玄虚,将一些本来很简单的概念硬是与阴阳五行,天地日月什么的搅和在一起,旁人就更加难以看懂。不过,今天我们有了现代语言学作为工具,那些原本玄妙无比的名词只需细加解析,便会昭如日月,人皆可见。我写这个小文的目的之一,也就是为了让不懂汉语音韵知识的人,能够从此对之有了一定的了解。当然,如果你有一定的语言学的功底,便可以更快,更容易的了解音韵学。音韵学的另一个名字叫做声韵学,顾名思义,就是研究声和韵的学问。当然,汉语情况特殊,除了声和韵之外,还有调。不过,古人并不了解调是一个独立的要素,而是把它放在韵里,所以没有把这门学问叫做声韵调学(听起来也挺别扭的)。现在,让我们来跨进音韵学的大门,第一步,自然是要了解它的研究对象:声,和韵。 声,或者叫声母,也叫子音,这些其实都是一个概念的多种说法。外语中似乎没有对应的说法。在汉语中,声母特指一个音节开头的音素。不过这个解释也并不是很全面,因为有零声母的说法。一种经常性的误解是把声母理解成为辅音,其实,辅音未必是声母(比如“音”这个字最后的一个辅音n),当然反过来,声母也未必是辅音,比如“音”这个字,"in",它开头并没有辅音音素,一般就称之为零声母(没有声母)。不过古人认为零声母也是一种声母,在后面要提到的三十六声母中,影母就是零声母。
韵的概念就更复杂了,音韵学中的韵和韵母也不是一个概念。当然,熟悉语言学的人知道韵母和元音的区别,这里还是提一下,韵母未必由元音组成。“男”nan,韵母是an,n这个音素是辅音,然而仍然是属于韵母的范畴。有时候韵母甚至可以完全是辅音,比如广州话“五”读ng,这个ng就是韵母。韵母在汉语中就是指一个音节除了开头的声母之外的所有音素的总和。但中国古代所说的韵,和韵母却又不是一个概念。韵的来源是格律诗的需要,可以在一起押韵的字就称为同韵的字。同韵的字未必同韵母,这是因为押韵的时候是只要韵腹和韵尾相同就可以押韵,韵头纵有差异,也可以不论,比如家jia就可以和瓜gua押韵,而两者的韵母自然不同(一个是ia,一个是ua)。反过来,同韵母的字又未必同韵,这是为什么呢?原来中国格律诗的押韵,光韵腹和韵尾相同尚且不够,关键的一条是声调还必须相同,这样不同声调的字就不可能同韵了。所以,我们在提到韵这个概念的时候,一般认为它是指包括韵腹和韵尾以及声调加在一起的一个概念。
三十六字母
现代汉语有24个声母,相比而言,唐朝时汉语的声母要多很多。宋朝时有人提出“三十六字母”的说法,字母这里就是声母的意思,至于为什么叫字母,这个和梵语有关。
对于拼音文字,表示声母是比较方便的,比如我们现在用汉语拼音就可以说:“家”是j母,“他”是t母等等。古人就没有这样的便利条件,因为汉语是没有单纯表示一个音素的字的(拟声字不算)。不过,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来表示声母,就是用一个这个声母开头的字来表示。好比我们可以这样说:“特叹同天”都是“特”母,“得东定地”都是“带”母。当然,这个字是可以随便选取的,只要声母确定就可以了。不过,“三十六字母”由于影响很大,后代学者在讲到声类时一般还是尽量按照“三十六字母”给出的声类代表字来描述。
“三十六字母”相传为唐朝僧人守温所创,故又称为“守温三十六字母”。不过根据现在的研究,“三十六字母”并不合于唐朝的声类,另外,守温的著述残卷也已经被发现,上面只记述了三十个字母,而且和“三十六字母”有很多的不同。因此“守温三十六字母”当出于后人的伪托。至于“三十六字母”究竟何人所创,至今未有定论。“三十六字母”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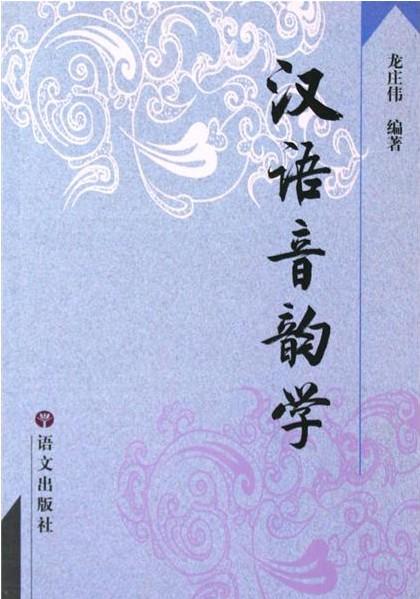 帮滂并明 非敷奉微
帮滂并明 非敷奉微
端透定泥 知彻澄娘
精清从心邪 照穿床审禅
见溪群疑
晓匣影喻
日来
请注意,这里把“三十六字母”分为六行并不是随意的。中国古代的音韵学者在提及声类时,一般将其分为五类,即唇,舌,齿,牙,喉。这大体说的是发音部位,不过,也有一些其它的音素在里面。为什么要分为五类呢?这个是因为音韵学家非要把它和五音商,宫,角,徵,羽什么的牵扯起来,此例一开,后来什么不搭界的东西都凑了上来,什么五行金木水火土,四方东西南北中,五脏肝脾心肺肾。这个也是音韵学令人敬而远之的元音之一。当然,我们今天掌握了现代语言学的知识,对于这些概念就可以有更清楚的了解,而不必纠缠于古人的文字游戏中了。
“三十六字母”的第一行“帮滂并明,非敷奉微”被称为是唇音,更细一些的划分是,“帮滂并明”是重唇音,“非敷奉微”是轻唇音。从现代语言学的说法来看,重唇音就是双唇音,轻唇音就是唇齿音。为什么叫轻重?大抵人类嘴唇结构是上唇较下唇突出,发唇齿音远较双唇音放松,因此,唇齿音“轻”,双唇音“重”。
第二行“端透定泥,知彻澄娘”称为舌音,和唇音一样,舌音也分为两类,“端透定泥”称为舌头音,“知彻澄娘”称为舌上音。实际上两者都是舌尖或舌面的塞音,不同之处是,前者是舌尖音,后者是舌面前音。
第三行“精清从心邪,照穿床审禅”称为齿音。齿音亦分为两类。“精清从心邪”称为齿头音,“照穿床审禅”称为正齿音。它们彼此间的关系类似于舌头音和舌上音,发音部位一个靠前,一个靠后。在现代语言学上,实际上舌音和齿音的发音部位没有什么不同,都是硬腭或齿龈和舌尖或舌面所发出的,不同的是,舌音都是塞音,而齿音都是塞擦音或擦音,将同一位置的塞音和塞擦音或擦音归为不同类也是古人的一贯做法。
第四行“见溪群疑”称为牙音,此名较为怪异,许多人搞不清楚牙音和齿音有何区别。其实这里牙指的时舌根处的大牙,就是臼齿。古人审音不细,将舌根音的发音部位误认为是臼齿,于是就有了这个不确切的名字。
第五行“影晓匣喻”称为喉音。但它们还需要具体分析。“晓匣”的发音位置其实与舌根音相同,但由于它们是擦音,故没有和是塞音的牙音放在一起。喻基本上是一个半元音,类似今天汉语的y声母。而影是声门擦音。这些发音位置歧异的声母,古人未加细审,皆归为一类,后人分析鉴别之,何其辛苦也?
第六行“日来”分别被称作半齿音和半舌音。这两个称呼多少有些误会的成份。原本两者分别被放在齿音(日)和舌音(来)里,但由于某些原因(下面就要提到),音韵学家将它们从各自的位置取出来,合成了一个新的音种,称为舌音齿。其实意思是从左边念是舌音,右边念是齿音。后人不明此理,以为两者和舌音齿音发音部位有所不同(不过确实也不同),便分别称之为半齿音和半舌音。不过将日来二母单独列出也是有其根据的。按照现代语言学的观点,日来二母属于无擦通音,音色接近元音,而与其他声母的情况不同。
清浊音
“三十六字母”各组内部声母的排列不是随意的。除齿音外,每种音都由四母组成。这四母的排列正好是按照全清,次清,全浊,次浊来排列的。齿音略有不同,因为齿音没有次浊,排列方式为全清,次清,全浊,全清,全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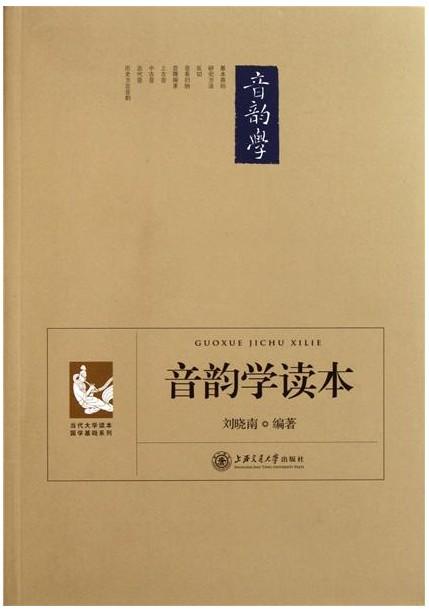 清浊也是汉语音韵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不过由于古代学者所用词语的紊乱,清浊的意思在许多场合并不相同。不过最常用的意思就是指所谓的带音或者不带音(声带振动与否)。不带音者为清,带音者为浊。汉语的声母按照前所述,分为全清,次清,全浊,次浊四类。从现代语言学的角度来讲,全清声母不带音,不送气,次清声母不带音,送气。全浊声母带音,送气与否无所谓。而次浊声母也不带音,但次浊声母为响音(包括鼻音,边音,闪音)和半元音,而与全浊声母为塞音,塞擦音以及擦音不同。 全次清浊这四个名称的来源大抵是来自韵图。韵图里将属于同一类的声母(比如同属唇音)放在一大格里,然后将一大格分为四(非齿音)或者五(齿音)小格,表示同一发音位置的不同声母。四个小格的声类排列是:“清,次清,浊,清浊”,五个小格的声类排列是:“清,次清,浊,清浊”。这里次清本来是第二个清声的意思。但后人不明此理,以为次清表示“清之次者”,就是不纯粹的清,于是将原本的“清”改叫“全清”,表示它时纯粹的清,其实今天我们都知道无论声母送气与否,清音就是清音,没有清得多一些或少一些的区别。当然,为了整齐,“浊”也就被改成了全浊,“清浊”被改成了“次浊”。其实“全浊”声母正好是“全清”或者“次清”声母的带音,三组声母彼此对应,而“次浊”与“次清”根本没有任何关系。“次浊”原来的称法“清浊”或者“不清不浊”都表现了“次浊”声母与清声母或者浊声母都不对应的关系。
清浊也是汉语音韵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不过由于古代学者所用词语的紊乱,清浊的意思在许多场合并不相同。不过最常用的意思就是指所谓的带音或者不带音(声带振动与否)。不带音者为清,带音者为浊。汉语的声母按照前所述,分为全清,次清,全浊,次浊四类。从现代语言学的角度来讲,全清声母不带音,不送气,次清声母不带音,送气。全浊声母带音,送气与否无所谓。而次浊声母也不带音,但次浊声母为响音(包括鼻音,边音,闪音)和半元音,而与全浊声母为塞音,塞擦音以及擦音不同。 全次清浊这四个名称的来源大抵是来自韵图。韵图里将属于同一类的声母(比如同属唇音)放在一大格里,然后将一大格分为四(非齿音)或者五(齿音)小格,表示同一发音位置的不同声母。四个小格的声类排列是:“清,次清,浊,清浊”,五个小格的声类排列是:“清,次清,浊,清浊”。这里次清本来是第二个清声的意思。但后人不明此理,以为次清表示“清之次者”,就是不纯粹的清,于是将原本的“清”改叫“全清”,表示它时纯粹的清,其实今天我们都知道无论声母送气与否,清音就是清音,没有清得多一些或少一些的区别。当然,为了整齐,“浊”也就被改成了全浊,“清浊”被改成了“次浊”。其实“全浊”声母正好是“全清”或者“次清”声母的带音,三组声母彼此对应,而“次浊”与“次清”根本没有任何关系。“次浊”原来的称法“清浊”或者“不清不浊”都表现了“次浊”声母与清声母或者浊声母都不对应的关系。
全浊和次浊声母在语音发展上明显有着很大的区别。我们说现代汉语中无浊音,是指无“全浊”声母,至于“次浊”声母有如“泥”、“来”、“明”等,现代汉语还是有的。另外,全浊上声字现代汉语大都变成了去声(“上”本来是上声字,所以称为“上”声,但由于“上”是邪母,为全浊声母,因此“上”变成了去声shàng。现在有人认为应该把上声读成“shǎng”,自是不明白语音发展规律所致),而次浊上声字则未变。全浊入声字,在现代汉语归入阳平,而次浊入声字则归入去声,可见全浊和次浊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声类。前面提到韵图中声母的排列,原本,舌音一栏是“端透定泥来”,齿音一栏是“照穿床审禅日”,各多了一个次浊,将原本整齐的格式打乱了,所以韵图的作者就将日来二母独立列为一格,与其他声母分开,这就是前面所述日来单列一类的元音。